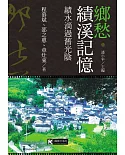推薦序1
攜夢繼續航行
殘缺的夢攜帶他的文字,或反過來說,他的文字攜帶殘缺的夢,在遠方的港口航行。因為殘缺,他繼續遠航,不捨晝夜。三十年來不懈的散文追求,搖蕩在無數起伏的歷史事件。在啟航之初,臺灣正要從封閉階段走向開放時期。那是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威權欲逝未逝,理想將至未至。衝撞的浪潮席捲每一個心靈,不是夢醒,便是夢碎,所有的騷動都指向一個預告:舊歷史就要過去,新時代將要到來。正是在謎底猶未揭開之前,林文義已決定選擇散文書寫,涉入混沌未明的水域。
他的文字讀來極為柔軟,卻暗藏一股堅定的意志。逆著社會潮流,他並未縱身於政治運動的怒濤,而是以散文形式構築一座城堡,冷眼觀察詭譎的風雲變幻。每一時期的文字,似乎都是一面鏡子,倒映著政治氣候的凝滯與流動。柔軟是一種書寫策略,足以使憤怒與抑鬱獲得沉澱,足以使複雜情緒達到濾淨殆盡。他的筆並未直接干涉權力,文字姿態也未造成敵對,然而,正是藉助於婉轉的節奏,使得大時代裡受到遺忘的感覺,受到遺漏的感情,都保存在冷靜的紀錄裡。
經過那麼長久的書寫,林文義散文可以視為珍貴的記憶。他保存的記憶不是驚天動地的事件,不是新聞記載的政治,而是三十年來不同時期的心情;那樣的心情不僅屬於他個人,也共同屬於穿越歷史隧道的整個世代。記憶的重量落在他的每冊散文,其中浮起的喟嘆,感傷,頌讚,歡愉,都必然回應著與他錯身而過的人與事。
《邊境之書》是他散文旅程的延伸,負載著較諸從前還要沉重的愁緒,這是受到政治傷害之後的系列散文。如果有一天歷史遭到遺忘,至少這冊散文還保留鮮明的見證。林文義是為夢而活的作者,但是對於時代的激流與暗潮卻保持纖細的觀察。他從未確切描摹過自己的夢,但是散文本身便足以道盡一切。他嚮往過一個可以信賴的政治,在那裡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對待,在那裡正義是能夠觸摸的價值。為了這樣的嚮往,他放棄旁觀的態度,曾經毅然介入粗糙的政治運動。作為食夢者,他訝然發現現實政治裡全然沒有夢的影子。不僅沒有夢,而且還受到刺傷。
傷害畢竟沒有終止,跨入新世紀的臺灣,承受的罪孽更為深重。當民主遭到出賣,理想遭到背叛,釀造出來的傷害波及這世代所有的心靈。這是一個不容淡然的年代,也是一個無處可逃的社會。民主災難襲來時,食夢者無夢可尋,食利者有利可圖,林文義的感傷就在於此。雁行折翼的苦澀,竟至如此難嚥。
邊境的暗示,存在於欲言又止之間。散文裡記載了多次旅行的心情,黯淡卻不消沉。邊境,既喻放逐,又喻回歸,依違於理想與幻滅的兩極。年輕時,他訴諸於靈感,訴諸於華麗。跨過中年之後,他的書寫不再乞靈於情緒,而是求諸於自我意志。每一個落在稿紙上的文字都有他不得不說的欲望。彷彿是規律地繳出週記,把無法藏於內心的語言公諸於世。因為是規律,每一篇散文都必須凝聚強悍的意志。
坐在遠方的港口,他瞭望的方向仍然準確對著臺灣。即使有忘懷的時刻,他還是無法忘情。所謂邊境,絕不意味遠離,也非若即若離,其實是全神投入。他不甘於脫離臺灣社會的庸俗與醜陋,也不怯於面對外在現實的瑣碎與繁華。在他的內心維持一個邊境,頻頻以深情回眸他所愛戀的土地。他的文字不能不以柔軟對應,句式越來越簡短,意象越來越清澈,非如此便無法對付越來越醜惡的政治。
與林文義相識近三十年,對他的文字藝術極為熟悉。在同輩散文家的行列裡,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那樣不懈地沉浸於書寫。宋澤萊曾經說,林文義是美麗島事件後的重要散文家。實情當不止於此,他應該是新世紀的重要寫手。他的散文不能只是當做文學看,其中還有歷史,也有政治。時代跌宕、轉折、反覆的任何波動,都在他的文字裡留下痕跡。混沌未明的水域,全然不能阻擋他的遠航。一位作家堅持十年的書寫,並不稀罕。堅持三十年、四十年的創作,必定是體內進駐了一個傲慢的靈魂。他將站在邊境,專注凝視這個社會。現實是這般殘缺,他必將攜夢繼續航行。
陳芳明
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政大台文所
推薦序2
葉派忠誠掌門人
這許多年以後,我還清晰記著,不知啥原因沒上學的下午,我的手伸向大哥的書架,找到《葉珊散文集》,那個忽然一瞬間的畫面。
瘦長的開本,質樸的封面,忘了是晨鐘還是文星版的。那一個下午,躺在泰順街住屋裡,我清楚地墜落到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裡。那一個世界,有一股說不出的寂寞,感覺卻是華麗的。那時,我以為自己是找到了一個祕密,找到就讀師大附中的大哥之所以擅長寫散文和情書的金鑰匙;以為還在少年維特懵懂階段的自己終於踏進愛情的新天地了。也許真如此吧。然而,多年以後,自己更清楚:當時那一剎那,是掉進了文學的世界了。
如果小說界有所謂的「張派」,那臺灣散文界也應有「葉派」。我不曉得有多少人像我一樣是因為這一本書的召喚,而闖入文學的世界裡。相信四年級生不少,五年級生恐怕也有一批。其中,林文義大哥是其中一位,而且,是成就極其可觀風格始終如一的難得作家,如果稱為最忠誠的葉派掌門人也不為過吧。而葉派,如同這本新作被引用散文評家張瑞芬教授對文義大哥的說法:「雄渾又憂鬱,陽剛卻唯美,結合了陰柔本體與對粗獷的嚮慕,如希臘神話中集陰陽二體於一身的半人馬……。」
一九七七年,已經更改筆名為楊牧的王先生,在新成立的洪範出版社,依然延用原筆名而增訂了新版的《葉珊散文集》。那一年,我自己正追趕高中以來荒廢的功課,拚命於大學聯考的窄門。終於購買而擁有自己的珍本,恐怕是到高雄上大學以後。因為阿米巴詩社,因為全國學生文學獎,因為苦苓和向陽,因為陽光小集,年輕的我開始遇見許多自己心嚮往的作家,其中,林文義大哥便是其中一位。
歲月會公平地處理人們自己驕傲的年少無知。那時初識文義大哥,身為大學生的自己,總覺得他是文壇上教人景仰的前輩了---雖然後來發覺才長七歲,用現在的說法:都是四年級的。而稱謂也就從文義大哥變成阿義仔,電話長談的,也不知不覺從年少的許多夢想,到中年以後無從逃逸的悲歡。
深夜裡翻閱文義的《邊境之書》,忽然又憶及文中提及的許多老友。當年這些年少輕狂的朋友,現在紛紛都偽裝成年輕中年而其實是年近過半白的朋友了。
這一群朋友經歷了一個歷史旅程,是過去世代沒有而未來世代也不會出現的。出生於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成長在七○年代的革命希望,投入八○年代的夢想建構,然後是九○年代最高峰,再跨入廿一世紀的挫敗和沮喪,以及,在眼前必須面對的反省。
這一個世代,就像一群伊底帕斯,年輕時憑依著自信和正義而弒父一般地貪欲革命,卻又遭眾神詛咒而自盲雙眼、流放於科羅諾斯。
阿義仔和我的許多藝文朋友一樣,用不願太快衰老而失去青春的方式,來拒抗這個眾神安排的宿命。因為這樣的堅持,即便是必然獨行在寂寞的草原,我想,阿義仔和許多朋友一樣,將這無所蔽護而隨時遭險的未來孤獨路程,視為自己求仁得仁的甘願吧。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何處是你的邊境?華麗以及蕭索,靜謐或者動亂,海角天涯,你以真情找尋最美的一顆星。」
這是《邊境之書》作者寫在扉頁做前言的句子。我再次抄一遍,因為,這本書不是只有林文義的生命故事,是這一世代同一輩的人的共同生命。
王浩威
後記
境與靜
美麗的蒼茫的後中年,儘見滿地荒蕪!幸而專志、嗜愛的文學書寫依然堅執持續,似乎生命裡還潛伏著不馴的理想主義,一向浪漫的抒情美學意識;是的,浪漫原出於至小孤寂卻不願認命於庸俗,抒情賦予以文學表達形式亦是相信在這紛擾、多端的人世間,試圖尋求、構築一片花與樹的夢土。
涉身詭譎、峻礪的江湖,看過人與人之間的虛實、應對、算計,真情與矯飾,其實是小說最真切的取裁;我亦不揣淺薄地試筆二三,不是曾有前人明諭:「小說比歷史還真實」嗎?虛構的情節往往真實就悄然侵入,寫小說的人極力抗拒,圍城般的生死戰役,幾無閃躲的浴血對峙,就因過於清楚而蒙受苦痛。拋盔棄甲的遁逃到詩的領地,聖鬥土學習轉化為種花植樹的園丁,靜靜生活,在最邊緣的角落。
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告解的形式?於是就在二○○九年,歷經政爭之亂、風災肆虐的時刻,彷彿尋求文學救贖般地,應邀撰寫兩個散文專欄,動盪的亂世,我卻秉持著「抒情為上」的意念,著力於每帖千字的持續書寫。
浮舟於海,回看島嶼,寧願保持一種疏離的等距;不免偶覺清寂,只有書寫的文字替代且舒慰我時而沉鬱,時而輕緩的內心,抒情風格竟然容許我藉以依託、傾訴。這才發現,昔時那一廂情願、率真愚騃之人早已遠去,如鏡碎影滅,若夢乍醒,回歸文學還我純淨初心。
一千字散文。格律般流動,筆與紙,晝與夜,猶若淨心抄經的過程,我必虔誠如古代的僧侶或教士,卻沒有任何信仰的規範、制約;這必得深深感謝編者的寬容與疼惜,雖說專欄幅員囿於千字,於我卻如無垠草原、大海,任我奔馬疾馳或潛泳,風起雲湧,海色山影,酒歌畫夢,得以壯闊,得以纖美,文學之聖殿果然幽深無盡,我這使徒,只能讚嘆且謙卑。
書分兩卷,前之:「邊境之書」逐月數帖原載於《中華副刊》,後之:「靜謐生活」則每週登在《人間福報》,合五十四帖。細心讀者自能辨識其中異同,意旨還是從抒情出發而止於塵世所感;書題:「邊境」亦如我人生向來的寧在邊緣,厭於眾聲喧譁的虛相,確切的渴求一種真實的靜謐,純然的美質涵養。
陳芳明先生的序文,才是此書最美好的完成。總讓我時而感念二十多年的文學情誼,他的典範與純淨伴隨著我們曾經堅信的島國之夢,雖似湮遠卻永不熄滅。多年以來,兼具作家與醫師身分的王浩威,則是我印象不忘在花蓮初識的秀異詩人;此後時而求教於多次生命遇逢困厄的課題,其溫暖真摯於我猶若暗夜燭光,撰序鼓舞自是意義非比尋常。
必須向誠摯邀約專欄的編者:中華副刊羊憶玫、人間福報蔡孟樺深致謝意。從《迷走尋路》到《邊境之書》。聯合文學年輕、銳氣的編輯同仁,總令我憶起從前在副刊工作的美麗歲月;郁雯自始是我文學旅行最好的伴侶,人生亦是,她猶若明鏡予我在朦昧中,得以映照、反思。
雖說「邊境」,卻是靜好的真情凝視。
林文義
二○一○年二月四日 臺北大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