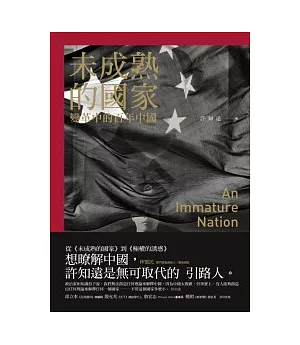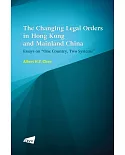代序
二十年和一百年——那些丟失的東西
一
俄國詩人葉夫圖申科和朋友K去看一部舊電影。其中一個鏡頭是猶太人在烏克蘭敖德薩遭受蹂躪的暴行,一群小鋪老板和刑事犯打著「殺死猶太人,拯救俄羅斯」的橫幅,手裡提著沾著猶太兒童們的血糊糊的頭髮的棍棒。
「難道你想變得跟這些人一樣?」葉夫圖申科轉頭問K,他知道K是個排猶主義者。
K躲開他,然後用冷冰冰的聲音回敬:「我們是辯證論者。不是所有過去的東西都要拋棄的……」
「他的眼睛裡流露著希特勒青年團員的凶光。他的皮夾克的翻領上閃爍著共青團的徽章」,葉夫圖申科後來寫道,「我驚愕地瞧著他,無法弄明白,我旁邊坐著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今,從那時起已經過去十年了,我才明白,史達林的主要問題根本不是他逮捕和槍殺了一些人……」
這個插曲發生在一九五○年代初的蘇聯,葉夫圖申科在史達林去世的十年後,回憶他的青年時代。除去有關K的爭吵,我還記得他對夜晚莫斯科情緒的描述:「街上走著些下班回家的,疲倦的人們,手裡提著麵包和盒裝的餃子。那些建設和戰爭的年代,那偉大的勝利和偉大的欺騙的年代,在他們的臉上留下了悲慘的影子。在他們的疲倦的眼神裡和壓彎的脊背上,存著一種不可理解什麼的意識。」
莫斯科正享受著全世界的讚嘆,它在最短暫的時間內建立起一個工業強國,擊敗了希特勒,擁有了核武器,誰能想到五十年前仍被視作歐洲最落後、野蠻的國家的俄羅斯,迅速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一半地區的領袖,製造了原子彈,第一個將衛星送上太空。莫斯科強大的宣傳機器,迷惑了外部世界,西方的主流知識份子相信,莫斯科找到了人類歷史更好的一條途徑;也麻痺內部人,多少俄羅斯人堅信不疑,史達林正是最英明的領袖,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成就。只有最敏感的頭腦,才會意識到這個國家面臨著深刻危機——是的,或許你有了一個表面強大的肌體,但靈魂卻是低劣的。
二
我和一個朋友談起這個故事。他今年四十五歲。二十年前他正在北京一所大學裡讀博士。他曾深深沉浸於那年夏天的熱烈氣氛,撰寫宣言、參加遊行。「我們都不成熟,也談不上多麼深刻的想法」,他對我說,「但都覺得自己和這個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希望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在他看來,一九八九年是一九一九年精神的延續,青年人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能力去改變這個國家的運行軌跡。
接下來的事件讓他們大吃一驚。驅散他們熱忱的是子彈和鋼盔。「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那個事件不是在於死了多少學生,而是我們整整一代人都放棄了。」他說。
另一個朋友和他年齡相仿。二十年前,他正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在他成長的七、八○年代,香港正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個徹底的殖民地正成長為現代城邦城市,覺醒的香港意識正逐漸取代既有難民心態。而他這一代對中國的情感也開始醞釀。他的父輩一代為了逃離大陸的饑荒、動亂,而寄居於香港,尋求安全與富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在他這一代心目中是貧窮、封閉、動蕩,是奮不顧身的偷渡客,是順著深圳河飄到海面上被五花大綁的屍體——他們死於武鬥。英國的殖民統治和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歷,使香港人習慣性地染上政治冷感,只埋頭掙錢就好。這種情緒在八十年代發生了轉變,中英和談象徵著政治權力的更替,它給香港人帶來了新的焦慮,也逼迫他們去了解和參與政治生活。英國的影響力在衰退,而中國的勢頭在上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贏得了很多香港人的好感,中國似乎正在擺脫昔日的噩夢。而一直到那年六月之前,香港對於中國的變化充滿了希望,人民已公開吐露自己的心聲,表達自己的主張,一個民主、繁榮的中國不正是未來香港最好的期望嗎?
我的這個朋友是位活躍份子,他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學則有著抗爭的傳統。而香港則再次成為海外華人表達他們的敬意和幫助的中轉站,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海外華人經常是推動中國內部改革的動力,是他們在海外的屈辱經歷,讓他們認定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他們熱心地支持康有為的保皇會、孫中山的同盟會,還有蔣介石的抗日行動……但很多時候,他們也被視作一個威脅到中央權威的異質力量。不同的人群對於強大的國家的認同大相逕庭,當一些人認為民主體制、多元價值是建立一個強大、穩定國家的基本條件時,另一些人將之視作危險的力量。當權者發現這裡經常容納異議份子,對於二十年前的北京來說,香港似乎再次充當了這樣的角色。
「就像是一個準備戀愛的少女,卻遭遇了對方的侮辱。」在一次酒後,我的朋友說。天安門的槍聲,驚走了他們對中國的純真幻想,他們想去愛這個國家,去幫助這個國家,卻發現他們的愛碰到了裝甲車。
三
二十年過去了,又一代人成長起來。表面上,他們的生活軌跡仍舊如常,北京的朋友畢了業,成為一所大學的教授。但是,在內心深處,他知道一些東西不復存在。他任教的大學比從前更富有,修建了更高大、豪華的建築,學生的數量也更多,他們似乎更年輕、更時尚、更無所不知,但是有些東西卻似乎消亡了。
而香港的朋友,做過新聞記者,也為香港政府服務過。香港則早已回歸,特首取代了港督,維多利亞公園的紀念活動仍在,但二十年的時間也足以沖洗掉很多。它的特首在面對議員關於天安門悲劇的質詢時,強調要多看中國這二十年取得的成就。
這二十年的成就的確驚人。二十年前的中國,風雨飄搖,政府與民眾的情緒空前的緊張,共產主義世界正在坍塌,中國被孤立,一些人預言這個國家馬上就要陷入崩潰。但如今,中國是最令人矚目的國家,它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在世界經濟衰退中,以更強有力的姿態出現,仿佛是世界運轉的新的模式。
但是,倘若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國,你會經歷一些與表面輝煌的數字和眩目的言辭不相同的東西。這是個光怪陸離的社會:貪腐無所不在,人們認定權力本就如此;大學像是巨大的商業公司和行政機關,思想與價值,變成最不重要的一環;人人都渴望同樣的成功,臉上掛滿了焦慮的神情;網際網路世界中,暴力、偏狹和愚蠢泛濫;人們言談粗鄙,除去實際利益,什麼也不相信……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說這是一個信念崩潰、道德淪喪、思想窒息的社會。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人們喪失了對未來美好的期待,也不相信社會還有別種可能,更對善良、正義、理想、尊嚴、勇氣,這些人類基本的情感採取漠視的態度,似乎除去淪為赤裸裸社會達爾文主義現實的俘虜,人生別無選擇。那些照耀我們的人性光芒,那些突破現實的美好情感,就算你不能說絕無僅有,也是稀少得可憐。
如今看來,一九八九與一九九二年這兩個年份,是一種詭異的結合。子彈和鋼盔,提醒了幾代人,不要試圖去參與政治生活、去挑戰現有權力,這一切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引來個人災難。而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是國家政權對全社會的一次收買——給予你掙錢和墮落的權利,但放棄你作為公民的其他權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獨立性。
現在,它大獲成功,我們的社會不正充斥著以另一種面貌出現的K嗎?在硬性的政治宣傳下的K,狹隘、殘酷、自以為是;而政治壓力和消費主義工作造就的K,是另一種類型的狹隘、殘酷和自以為是。他們都沒有靈魂。
四
一些人提醒我,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有或多或少類似的問題。或許歷史具有相似之處,我們卻不能因為昔日也有過、別的國家也有過,而放棄對此刻此地的警醒與批評,這種放棄才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代人真正墮落的標誌。我們也無法用物質成就來自我安慰,倘若人能夠放棄自己的精神性,那麼他生存的意義到底何在?粗俗經常戰勝高尚,強權也經常擠壓正義,物質則吞噬精神,但倘若我們因此喪失了對高尚、正義、精神的確信,這或許才是徹底的失敗。
物質豐沛、國家的強大、技術的進步,甚至民主制度,它們都不是我們努力的最終目標。我們的成就最終是以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來衡量的。
這個國家的歷史上充斥著濫用和踐踏她的人民的善良、純真、高尚、創造力的例證。但正因如此,堅持這種善良、純真、高尚與創造力,才變成最強大的武器。嘲諷、不屑、退縮、放棄的四處瀰漫,只是證明了當年的踐踏與濫用的大獲全勝……
二十年光陰,如白駒過隙。而百年中國的發展與變革,也轉瞬間被巨大的經濟成長所掩蓋和遺忘。那些丟失的東西在哪裡?那段被拋在腦後的歷史應該如何檢討、反省?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定性的軌跡嗎?而如果存在,它又將引導我們走向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