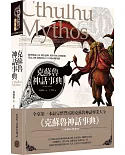導讀
永遠說不完的故事
傳說,對我而言,是永遠不會說完的故事,
在個人生命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領悟;
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會發生不同的意義、不同的結果。
所以十年前的《傳說》、二十年後的《新編傳說》,
新舊雜陳,也讓我看到自己與許多人心事的轉變。
一九八八年,我寫了一系列的神話故事,集結成為《傳說》。對於神話我始終沒有忘情,還有好多個故事想寫,於是又陸續寫了四篇,成為《新傳說》。
我喜歡神話傳說,總覺得每個民族的神話傳說裡都包含了很多、很深的東西。
和其他文學不一樣,神話、傳說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難免會「添油加醬」,每個說故事的人都變成傳說的創作者。
我們都聽過「嫦娥奔月」,但是每個人說的「嫦娥奔月」都會有一點不同。可能我敘述嫦娥奔月的故事時,會著重在嫦娥的寂寞、孤獨,所謂「碧海青天夜夜心」;換個人來說,可能就會著重在嫦娥和后羿的愛情。神話在口傳故事的發展過程,會不自主的帶進敘述者的性格取向,包括外在和內在的性格,使故事聽起來更加撲朔迷離。
燃燈佛的因緣
神話傳說雖然都是很老很老的故事,可是往往會因為某一個機緣、某一個人,發生新的意義。
在《新傳說》中,我寫善慧〈借花獻佛〉的故事,就是因為一個特殊機緣。「借花獻佛」這個成語耳熟能詳,這個成語是來自印度佛教經典,指的是福氣分享的過程。
故事描述一個聰明俊美的小沙彌,叫做善慧,(這個名字有很多種不同的翻譯,「善慧」是較常見的譯名),他四處求道,參加法會論辯。有一次,他贏了一場論辯,得到一些獎金,就帶著錢進城,聽見整個城市在傳說著:「燃燈佛要來了,燃燈佛要來了!」他很高興;對信仰者來說,一生中得以接觸燃燈佛是很難能可貴的機會,也是很大的功德福報。
燃燈佛是用自己的肉體去燃燈的佛,現在我們可以從很多佛教繪畫中看到他的姿態,用手指燃燒著燈火,用肉體燃燒,照亮整個世界。漢字的「燃燈」兩個字太美了,往往讓人忽略了它的本意有很強烈的肉體上的苦痛,與「割肉餵鷹」、「捨身飼虎」一樣,都意涵一個捨身的過程。
當善慧這麼一個天真無邪、聰明俊秀的小沙彌,看見城裡到處都是「歡迎燃燈佛」的字句,他心想,燃燈佛來了,應該去找些蓮花供養(用蓮花供養神佛菩薩,是印度人的習慣),可是他在城裡找了好久,一朵花都找不到。一問之下才知道,因為國王想要把供養燃燈佛的功德都歸於自己,早就把城裡花店的蓮花搜刮一空,就連河邊生長的野蓮,都派衛兵守著,一般人難以接近,所以大家都買不到花。
善慧覺得沮喪,好不容易有機會接近燃燈佛,卻沒有花可以供養。他垂頭喪氣地一個人在城裡東走西走,忽然看見巷弄裡閃過一個人影,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女孩,手裡還拿著七朵蓮花。
他趕緊追過去,攔住小女孩。小女孩看到有人出現,嚇了一跳,怕是碰上歹徒要跟她搶花。當她看清楚善慧俊美、和善的模樣,她才放心了。善慧把論辯贏來的金幣全掏出來,對小女孩說:「我想用全部的金幣買你手上的蓮花。」小女孩說:「不賣,我好不容易才得到這七朵花,這花是為了供養燃燈佛的。」小沙彌聽了悲喜參半,好不容易看到花卻不能買,又不能強人所難,因為小女孩拿花也是要供養燃燈佛。
善慧的表情很難過,好像要哭的感覺,小女孩看了也很過意不去,就答應要分給他五朵,留兩朵給自己,一起供養燃燈佛。說完,小女孩覺得小沙彌很漂亮,她有點臉紅、不好意思的說:「我知道你這輩子在修行,我也在修行,可是我希望在你修得正果、成佛之前,可以做你的妻子。」善慧就是後來的悉達多太子(釋迦牟尼佛),而這個小女孩即悉達多太子在成佛前人世的妻子。
相同故事不同結局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片片段段聽到借花獻佛的故事,可是前幾年在中部教書的時候,接觸到一個很久不見的朋友,才有了改寫故事的念頭。
我和這個朋友是在很偶然的機會下認識,當我還住在台北的時候,他曾經來幫我修過電器。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電器白痴」,一碰到電器問題,或是家裡停電就會完全不知所措。
當時我家裡突然停電,向朋友求救,朋友說:「哦,我剛好有個朋友住在你家附近,他是學電機的,他會幫你忙。」不久後,就有個人騎著摩托車來,按了門鈴,是一個在讀五專的小夥子,他檢查後發現是保險絲斷了。這好像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不應該麻煩人家,可是說真的,我也不知道保險絲要怎麼換,更不知道要怎麼打開那些東西。他看我不知所措的樣子,就笑出來了,他說,這是最小最小的電器故障,然後三兩下把保險絲換好,電燈亮了。
這時候他看到我桌上正在抄寫的佛經,他說:「有時候我也很想看,但就是不太容易懂。」
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機緣,我和這個年輕人認識,但後來就沒有聯絡,一直到我去中部教書時,接到他的電話,問我有沒有空?能否有機會來拜訪我。
我其實已經有點記不得他了,但還是邀請他到宿舍來。他變得有點瘦,應該是受了一些苦吧,因為不熟,我很難去聯想他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這個人改變得很大很大。
他很安靜不太講話,只是翻一翻我桌上的佛經,說他現在吃素、也常讀佛經,聊了一會兒,他突然問我知不知道借花獻佛的故事?
我大概講了一下這個故事,包括故事的結尾,就是燃燈佛終於進城了,大家都很想親近他,很多瘸子、瞎子也試圖要擠到前面去接近燃燈佛,想藉此減輕身體上的苦難。善慧擠在人群中,遠遠看到燃燈佛很華貴的儀容,赤足走進城,城門口有一個污穢泥濘的坑洞,燃燈佛沒有看到,一腳就要踩上去。善慧覺得燃燈佛的身分不應該踩在這麼髒污的東西上,立刻全身撲上去,用頭髮墊在燃燈佛的腳下。
佛經裡,將這個畫面描述得很美:善慧五體投地趴在地上,以頭髮鋪地,五朵蓮花飛起,落在燃燈佛頭上,兩朵在他的肩膀上,成為一個供養的符號。
故事說完,年輕人發了一會兒呆,說:「你有沒有想過其實燃燈佛不是這樣進城的?」
他告訴我,燃燈佛一直用四肢在燃燈,身體應該是殘缺的,可能是一個沒有手腳的肉球,在泥濘中扭動身軀,所有等待的民眾都不知道他就是燃燈佛,甚至故意推擠他。善慧看到他要掉進泥坑,就撲地用頭髮讓這顆肉球滾過;那時候的善慧已經忘掉燃燈佛,忘掉供養的蓮花,只是看到一個受苦的身體。
我很震驚,一個只有幾面之緣的青年,在當兵時刻,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有了這樣的疑問,特地前來把他的想法告訴我。當時我就決定,把我所瞭解的,和他所敘述的,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寫成了《新傳說》中的「借花獻佛」。
不是蒼涼,卻是蒼老
一個年輕人一定是因為什麼事情,才會讓他想去親近一些比較內省的經典,也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讓他有了新的燃燈佛的形象。我很好奇,卻沒有開口問他,因為我知道人性最底層的部分,不是好奇可以抵達;我也相信,當他坐在我的面前,對我說出燃燈佛的結尾時,他已經理清了很多心裡的困苦。
我們的社會是個很好奇的社會,因為年輕,卻把好奇發展成八卦雜誌的窺探。我想,好奇的極致應該是包容和悲憫,應該是出於關心,我們所好奇的不是他人為何事哀傷,而是他的哀傷,以及他要如何度過哀傷。重要的不是知道已發生的事件,而是人的心靈狀態。
如果這個年輕人再出現,我很想幫他畫一幅畫。從他第一次到我家修保險絲,到後來找我談佛經故事,他的改變很大很大,我一直記憶著那張臉,我想記憶著。不管是把他寫成〈借花獻佛〉的故事,或者為他畫一張像,我相信對世間許多人而言,都會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勵,至於那個讓他哀傷的事件則已經脫離了,不重要了。
我寫《新傳說》,同時也是在聆聽很多人的心事;一個古老的故事在很多人的心裡變成新的心事,重新演變,因為這位朋友的提醒,使我後來坐火車、公車時,看到殘缺的身體,總會覺得他就是燃燈佛,也覺得自己應該有善慧的心情,去擔待這些殘缺。
《新傳說》新增的四篇都比較接近這種感覺,和十年前的《傳說》很不一樣。十年前,我比較眷戀美,像〈莊子與蝴蝶〉、〈有關納西斯與ECHO〉都比較是個人的美的眷戀,新的四篇則是另一個層次,包括寫到嵇康在監獄裡面以鐵欄杆彈奏「廣陵散」,大概是中年的心情了吧,不是蒼涼,卻是蒼老了。
傳說,對我而言,是永遠不會說完的故事,在個人生命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領悟;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會發生不同的意義、不同的結果。所以十年前的《傳說》、十年後的《新傳說》,二十年後的《新編傳說》,新舊雜陳,也讓我看到自己與許多人心事的轉變。
開悟之前的迷障
我常常覺得神話是一種原型,可以不斷地賦與新的形式、新的詮釋,直到現在走在街頭上,不管是重慶南路、西門町,還是可以看見傳說仍然在發生,我生活周遭的朋友們,也都活在神話和傳說當中---即使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如借花獻佛,都可以找到許多人的原型;有人是善慧,有人是小女孩,有人是燃燈怫,有人是那位我沒有描寫到的國王。
國王其實也是一個有趣的角色,他那麼愛功德,所以搜括了城裡所有的蓮花。我不忍心去批判他,只覺得在生命裡每個人都用不同的方法在修行,也許他用的方法很容易被嘲笑,大家會說他是貪婪的、自私的,可是,這不也說明了一個包括我自己在內,大家都可能有的共同缺點?
貪婪我也有啊,我可能不貪名不貪利嗎?對美的東西,我又特別貪。對美的貪當然也是貪,也是一種貪念,自己不太容易發現就是了。
書出版之後,我才發現對這個角色的忽略,好像潛意識裡就排斥他,不想寫他。我想,如果有一天再改寫「借花獻佛」,這個國王會變成一個重要的描述對象,我對他沒有那麼不喜歡了,覺得他的貪不過是在開悟之前不同的迷障罷了。
過去我寫傳說,會有一個主角,但後來覺得,傳說不是屬於主角,每一個角色都是不能分割的「同體」,是牽連不斷的因緣糾纏。每一個人物在故事裡扮演的角色,都有某種開示的意義。善慧可能開示了我的某些部分,國王可能開示了我的某些部分,小女孩也開示了我的某些部分。
我認識一位替我減輕脊椎病痛的推拿師父,他得了一種很嚴重的病,失去視覺,在「看得見」到「看不見」的轉換過程裡,他非常非常痛苦。我想體會他的感覺,所以我嘗試閉上眼睛,很久很久,去感受失去視覺的驚慌。
驚慌過後,在我開始承認了「看不見」的事實時,我的另一隻眼睛張開了,可能在耳朵的聽覺裡張開,可能在鼻子的嗅覺裡張開,可能是在指尖的觸覺裡張開了。這個經驗使我知道沒有真正的盲人,很多東西反而是在眼睛看不見的時候才能「看見」,就好像在每一個神話傳說裡流轉的心靈經驗。
承載著人們的心事
當我重讀十年前所寫的傳說,和十年後新增的四篇故事時,我發現個人對美的執著,在《新傳說》裡放開來了,所寫出來的「苦」也不一樣。
譬如在〈有關納西斯與ECHO〉這則十年前所寫的傳說中, ECHO的苦是自閉的苦,她在愛情裡受了傷,退縮到山洞裡,我形容她皮膚上的苔蘚從腋窩長到鼻翼,甚至是嘴角,是一個非常形象化的憂鬱。我想,自己當時應該也有這樣的想法,在不快樂的時候會想要退到一個沒有陽光的角落,讓自己發霉,我稱它是一種「自閉式的憂鬱」。
可是後來寫到〈借花獻佛〉時,苦卻換了一種形式;燃燈佛的身體變成一顆肉球,在陽光下滾動,也不怕滾過泥濘。從沒有陽光的角落到有陽光的路,彷彿是一種痊癒的過程,我感覺自己在改變。
我相信那位修電器的朋友也看見我的改變,佛經裡的傳說在我和他身上互相交錯,重新創造。我還記得那一個下午,我們坐在學校宿舍的榻榻米上,陽光斜射進來,窗外開了一些桃花,桌上放著幾本佛經和手寫的東西;我們盤坐著,他聽我說完故事,說出自己的詮釋。那個對話的形式與空間,是好幾世才能找到的一個奇特的機緣吧。
愈來愈覺得,創作不是一個人在寫,身旁的每一個人都在跟我一起寫新傳說。我甚至幻想有一天,不需要文字書寫,用一種口語的連接方法,你講一段,我講一段,共同創造一個故事。
這就是神話的開始,如一艘船承載許多人的心事,從上游到下游隨波逐流而去。
自我凝視的納西斯
在《新傳說》中,我許多的學生最喜歡的一篇文章就是〈有關納西斯與ECHO〉,尤其我描寫納西斯的身體變成水仙的根莖,手指變成白色鬚根,在水中吸收水分,輕盈的小水泡在身體流轉,頭髮變成水仙的葉瓣,他們覺得這個描述過程美極了。
我卻覺得哀傷。
佛洛依德從納西斯的故事中分析出所謂的「自戀情結」,又叫做「水仙花情結」,我相信這是每個人都有的情結,每個人絕對都有非常非常眷愛自己的部分。一個人若說他討厭自己、憎恨自己,他的出發點恐怕都是來自於對自己的眷戀,只是轉變成不同形式罷了。
希臘神話的原典很有趣,它在講述納西斯的故事時,不是把重點放在納西斯的長相,(後來很多改寫的書籍都會強調他非常俊美漂亮),他只是一個老是在水裡看自己的男孩,或者說,他只是一個在水中看自己的「人」──我們甚至可以把性別拿掉。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看,一個喜歡在鏡子裡凝視自己的人,在倒影中看自己的人,一個喜歡思考自己的人,都可能有納西斯情結。在神話原型裡,納西斯代表的就是對自己的著迷。
我相信每個人在這世界第一個愛上的人都是自己。我們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愛情,其實都是在找一個內在的、不被瞭解的自己。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找錯了,有時候又好像找對了,那是因為我們對自己並不是那麼清楚;有時候你覺得瞭解自己,有時候你又不懂。
以我自己來說,到現在為止,讀了很多書,有一定年紀,經歷過許多事,也有相當的成熟度了,對自己仍是處於一知半解的狀況。
最近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他發現我內在有一個很不安全的東西,我說:「會嗎?」我最常聽到別人說我很明亮,說我很陽光,我自己也覺得在朋友中是開朗的個性。可是當這個朋友說,他讀了我的東西,發現在華美的背後總有一個很不安全的東西,好像這個華美隨時會消失,我開始凝視自己。
我回想起大約在十歲以前,的確有很多夢境是一直在逃,一直在躲;不知道為什麼而逃,躲的對象也一直沒有看清楚,躲的地方可能是一個很深的水井,可能是一個很深的櫃子,我一直往裡鑽。
我的本質裡的確是有一塊強烈的不安全感,我會親近宗教,也許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宗教常常在提醒我們所有華美背後的廢墟形式,也就是成、住、壞、空,和我的不安全本質互相感應。
朋友的話讓我變成對水中自我凝視的納西斯,我想,每個人都有一潭非常清澈的水,等待你去凝視自己,與自己對話,那是人的第一個情結。
面對巨大的孤獨感
這種凝視無疑是孤獨的,納西斯孤獨,ECHO也孤獨;但兩個人的孤獨有很大的不同;ECHO可能愛人,她愛納西斯,她的孤獨是不被瞭解的哀傷,但納西斯不可能愛人,他只是沉迷於水中的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最巨大也最純粹的孤獨。
我覺得納西斯的神話愈來愈迷人,尤其是在都市裡,在現代高科技的文明裡,每一個人都很像納西斯。這一代人的納西斯情結又比上一代嚴重很多,因為他們成長過程裡的自我,是不容易被干擾的,所以他們都非常喜歡凝視鏡子裡的自己,都喜歡在網路上去尋找自己。
當然,他們也特別孤獨。
前幾天有個雙魚座的男孩打電話給我,說他心情不好,因為他「好幾個」女朋友「剛好」那天晚上都找不到。我覺得這句話很有趣。當時我想的是,他好怕寂寞喔,他平常有好幾個女朋友,這個沒空就找另一個,可是當她們都不在時,他就無法自處了。
電話中,我跟他說了《紅樓夢》的故事,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這種「只找一個人,她不在,我就誰也不找」的思念和執著,可能才是「不寂寞」的開始。如果甲不在就找乙,乙不在就找丙,到最後必然是寂寞的,因為他不是在找對象,他只是在面對自己巨大的孤獨感。
很多人在談「性無能」,可是我發現「愛無能」也許更嚴重。現代人不太能夠愛,也怕去愛,這是一個更大的荒涼吧。
愛在飽滿的狀況裡,性不可能是無能的。這句話裡面當然有我自己很特別的對「性」的解讀,我不認為人的性器官只是狹隘的生殖器,我覺得全身都是性器官,我可以在撫摸一個人的頭髮時,感覺到性的飽滿,因為我的出發點是愛,愛飽滿才會性飽滿。如果性簡化成只有器官的刺激、亢奮,那麼這個人勢必是寂寞的,再多的藥物都無法治療。
從這個角度去想,我覺得納西斯勢必要變成一株草,他的世界就那麼小,他的意義只有在水邊的凝視,他是愛無能。
躲進自己的封閉世界
納西斯只能在水邊凝視自己,和ECHO永遠變成山洞裡的回聲,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但ECHO至少愛過,她會受傷,她會痛,納西斯沒有傷,沒有痛,他的冰清玉潔是因為一切事情都沒有開始過。
我發現,少年情懷都會喜歡納西斯,不太甘心自己是ECHO,這裡面當然隱喻了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狀態;他們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有ECHO的部分,因為覺得丟臉、不好意思。
可是,對我而言,這是兩種無法比較的生命形式。
如果我從另一個角度來寫ECHO,我會覺得,其實她在潛意識裡面,並不要納西斯愛她。
愛情很奇怪,你有一部分希望對方愛你,可是另一部分又很希望不被愛,那種躲在自己孤獨裡的哀傷,可能成為另一種形態的「享受」---我用這兩個字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我的確發現,自己和朋友在失掉愛情時的心情感受,不見得比戀愛差,那裡面有很奇怪的思念、牽掛、眷戀、糾纏。
失去和得到是兩種可以互換的東西;當愛人遠離的時候,我在很遠的地方思念他,寫信給他,是一種失,也是一種得。反而兩個人在一起時,會覺得幻滅,可能會吵架、會衝突,得裡面又有一種失。
ECHO就是如此,她的狀態好像是為了一種自閉中的完美,獨自在山洞裡反覆品嚐和咀嚼自己的哀傷,她不想再走出來了。而她不走出來,反而加深了那個世界的人對她的迷戀。
馬圭斯小說《百年孤寂》中,有個女孩始終坐在角落,沒有任何原因,當大家在聊天時,她一個人面對牆角吃泥土。那個符號很強烈!你不能說那不是一種滿足,但那是一般人無法瞭解的滿足。
我們的文化從六○年代以降,在流行的女性文學和連續劇中,這種接近自傷性、自閉性的愛的形式,是非常多的。似乎從瓊瑤所寫的《窗外》這部小說開始,就是這種基調,女性在沒有受傷前就假設自己受傷了,躲進自己的封閉世界,品味愛情的美麗。
我的女學生中也有很多這種例子,我當然會鼓勵她們,要走出來,天涯何處無芳草。可是,我發現她們「耽溺」哀傷---我用「耽溺」這兩個字,好像很不敬,但這種狀態未嘗不是一種美學,甚至也有一種自我完成的高貴,我很難去解釋,我認為那就是一種ECHO情結。
《紅樓夢》裡的黛玉也有這種耽溺哀傷的ECHO情結,你會發現寶玉對她的愛比大觀園裡其他女子都多得多,可是對她而言,那並不重要,她就是一直要還眼淚,她一直讓自己退縮到一個毀滅性的悲劇裡,焚稿斷癡情,這種狀態只有從神話原型裡才能得到解釋。
我想,神話原型不能從世俗來解釋,不是好或不好,而是在講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在每個人身上都有可能存在,只是強度不同;每個人身上都有納西斯的部分,也有ECHO的部分,當然也可能有莎樂美的部分---莎樂美在神話原型裡代表著另一種形式的毀滅。
讀懂了自己的內在
我相信,佛洛依德用神話原型來解釋「情結」,有他的道理。「情結」是一種解不開的結,我們一生在面對這個結時,都試圖用理性、理智去拆解,可是事實上,情結的結愈解愈緊。
佛洛依德之所以了不起,是他發現心理學與神話有這麼近似的狀態,神話原型和心理學的情結,同樣難解。所以佛洛依德本身並不關心治療,他在乎的是分析過程;治療是把結解開,可是他隱約覺得這個結是解不開的,我相信他自己也有一個結,他因為這個結而知道其實情結是解不開的東西。
莎樂美的神話最能說明這種無解的狀態。
十九世紀末王爾德等文學家、藝術家都非常熱愛闡述莎樂美的故事,因為這時候人們剛剛開始要面對人不可解的宿命性。在此之前,人們用實證主義、啟蒙運動去解釋人性狀態,可是像莎樂美這麼一則在聖經裡也找得到的傳說,完全沒有道理可循。
神話中,莎樂美是一個美得不得了的女孩子,媽媽是國王的寵妾,而這個國王是個淫慾到極點,簡直像動物一樣整天吃喝玩樂玩女人。他看到莎樂美時嚇一跳,彷彿在那一瞬間他的慾望卑微到極點,莎樂美的美不容褻瀆;他太容易玩弄一個女人,可是他完全無法掌控莎樂美的美麗。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美麗的莎樂美卻一直牽掛著在約旦河替人受洗的施洗約翰。
在宗教傳說中,施洗約翰和耶穌一樣都是沒有經過受孕過程生下的孩子。天使出現告訴瑪莉亞,她懷了上帝之子,她不相信,天使就叫她去見堂姊安娜,她也懷孕了,堂姊懷的就是施洗約翰。耶穌和施洗約翰來自同一個家族,可是各自長大,沒有見過面,他們都是神話裡宿命的人物。
有一天,在約翰面前出現了一個美麗的青年,那個人就是耶穌,約翰嚇了一大跳。青年說:「我是來受洗的」,約翰驚訝的回答:「在天國裡你比我大。」耶穌說:「我的時間還沒有到,你先執行你的任務。」這就是一個宿命的對話,接著耶穌脫掉衣服,赤裸的站在約旦河中,約翰雙手捧著河水,自他頭上淋下去,據說在那一霎,天整個開了,有鴿子飛下來。
這個描述非常奇特,後來很多文學家、畫家都為這個場景著迷,可是沒有人知道裡面有什麼宿命,有什麼需要解開的情結,只看到兩個站在水中的美麗青年。
之後,耶穌走了,他們一生只見過這一次面。
耶穌走後,施洗約翰愈來愈暴躁,他開始咒罵很多人淫慾、貪婪,要修改懺悔罪過,否則不能進天國。當他看到莎樂美時,他咒罵得更凶。他被莎樂美的美震動了,那種美是他修行過程中最大的敵人,所以他對她做出最嚴厲的咒罵和批判。
莎樂美從來沒有愛上任何人,也沒有動情過,除了施洗約翰,當她聽到約翰的咒罵時,她知道這個修行者是自己永遠得不到的人。
這兩個人互相吸引,卻互相得不到對方,變成一種很激烈的拉扯。
有一天,莎樂美對那個一直想要染指她、經常像隻動物般卑微討好她的國王說:「你不是一直想看我跳舞嗎?」國王一聽欣喜若狂,莎樂美終於對他有反應了,他說:「好,你只要願意跳舞,任何你想要的東西,我都可以給你。」
此時,莎樂美跳了一支歷史上很有名的死亡之舞。很多音樂家為這支舞寫了很美的曲子,大家都在幻想一位十六歲的少女、以完美的身軀跳出的舞
到底會有多美,可是沒有人真正看見過。
她跳完之後,國王問她要什麼,她說:「我要施洗約翰的頭。」國王聽完也臉色發白,他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個,但他還是命令人把修行者的頭砍了,盛在一個銀盤裡,獻給莎樂美。
莎樂美就靜靜捧著那顆血流不停的頭,親了施洗約翰的嘴唇。
這個神話之所以變成情結,是因為它完全無解,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可是當你在讀的時候,完全被震撼了。
神話原型最後都沒有答案,只有回到故事本身的隱喻,而故事之所以流傳,就是我們藉由這些隱喻,讀懂了自己內在不被看見的部分,殘酷也好,慾望也好,得不到的復仇也好,死亡之中的極致激情也好。
有太多人寫莎樂美,畫莎樂美,我也在《新傳說》中,重新做了自己的改寫,這一篇也是全書中最沒有答案的故事,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答案。
從神話鏡子看到自己
耶穌和約翰的愛、約翰和莎樂美的愛、莎樂美和國王的愛,國王和莎樂美媽媽之間的關係,都是糾纏不清的。我在寫的時候,覺得約翰和耶穌見面的那一幕非常重要,因為我無法忘記在美術館裡看到的那些畫,那一次的見面很驚人,連天都開了。而莎樂美最後和約翰人頭的吻,好像變成一種印記,一種見證,那是一個混合了華麗、美、殘酷、死亡、罪惡的畫面,這些元素平常都是分開的,可是在這一刻全混合了。
十九世紀末的文人會那麼喜歡這則故事,我想與歐洲當時頹廢派在檢討美與罪惡有關,美與罪惡也可以說是情與慾的關係,就是在情極深時,慾望同時也最高漲。我相信這三個人之間有極純粹的情,可是他們都分裂了,所以故事有最驚人的發展。
這個故事還會流傳下去,因為它愈來愈有現代感。我看過八○、九○年代的一部電影《酒店》,講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故事,幾乎就是約翰、耶穌和莎樂美的原型重現,看到最後你還是不知道他們各自愛著誰。
我相信我的學生中,也有莎樂美的原型。我常常聽學生說,他不知道和某人是友誼還是愛情,我就會回答他,其實本來就不那麼清楚。
過去的人會說不上床的就是友誼,上床的就是愛情,或者同性之間是友誼,異性之間是愛情,可是這種簡單的畫分,在莎樂美的傳說中不成立,到現代也已經不適用。今天我跟年輕學生在一起,根本沒有辦法判斷誰跟誰是戀人,誰跟誰是朋友,非常複雜,他們自己也常搞不清楚;往往就在曖昧之間,產生另一種情慾的糾纏。
至於情慾糾纏可解、不可解,從理智上來說是不可解,愈解愈緊,但是從人性最內在的情感本質來說,我覺得是可解的。我的意思是說,哲學解不開神話,但文學可以,因為文學就是尊重故事原型。當佛洛依德把神話故事分析一次,你就覺得結解開了。
其實解開情結的關鍵不是答案,而是聽故事的過程,當你從神話這面鏡子的反射中看到自己的原型,你就能讀懂自己,對宿命也比較不容易慌張了。
《新編傳說》或許還有與眾人對話的空間。
一九八九年蔣勳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