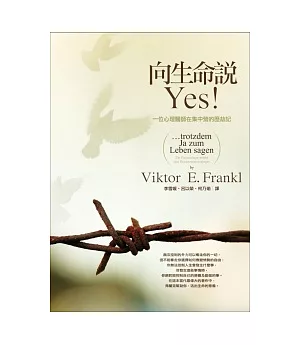德文版序
支持維克多.弗蘭克
正如維也納城堡劇院與城堡並無多少關聯,在我們現今的認知中,維也納的宮廷霍夫堡也和皇室宮廷毫無關係了。
維也納霍夫堡早已被新的世紀平民化、共和化,如今已成為國家文物的典藏處、大學系所部門、各協會的辦事處,甚至是私人公寓。它不僅是會議的舉辦場所,更擁有許多可做為展覽會、音樂會及演講之用的廳院。
一九七六年秋,在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獲獎後一年,鑑於維克多.弗蘭克的個人終身成就,每年於此盛大舉辦的奧地利圖書展評審亦特別頒授《多瑙國家獎》(Donauland-Preis),典禮就在霍夫堡一間金碧輝煌、燦爛奪目的大廳內隆重舉行。
從過去的歷史角度看來,當晚的頒獎典禮突顯了兩個特殊意義。
雖然在集中營這樣極度黯淡絕望的處境下,維克多.弗蘭克仍然找到一絲面對未來的希望與慰藉。「我想像著自己站在一個寬敞明亮而溫暖華麗的大廳講台上,面對一群興致高昂的聽眾演講,題目為《集中營的心理治療經驗》,並正好談到我才剛經歷過這一切。」
三十多年後,他就站在這寬敞明亮而溫暖華麗的大廳裡,不疾不徐地講述著。不僅是他如先知預言般的治療想像力,就連他的理論也成功獲得印證:他之所以能親身經歷這實至名歸的夜晚,正是因為他當年在心靈上預先體驗了頒獎那一夜的心境。
然而,對霍夫堡而言,那一刻所代表的意義已遠遠超越了個人的藩籬。
在奧國皇室還占據霍夫堡的期間,他們對周遭所有藝術與精神方面的璀璨發展完全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尤其皇室官方的維也納仍存著駝鳥心態,對即將邁入二十世紀的世界劇變漠不關心、無動於衷,一貫麻木地過著自我封閉的生活。雖然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已察覺到周圍世界的新興覺醒,卻也對一棟新建築物表達出個人的強烈反感;那棟美輪美奐的新建築物位於聖米歇爾廣場上,由阿道夫.魯斯(Adolf Loos)所設計,從他宮廷窗邊也可以望見。
隨著時代的演進,我們的世界學會了觀察那些奧國皇帝不願正視的事物;尤其自從維也納不再是皇帝專屬的城市之後,世界開始發現維也納是個深層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首都。如此說來,維也納霍夫堡算是藉此彌補了對維克多.弗蘭克的虧欠。可惜的是,做為宮廷專屬的霍夫堡卻未能給予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其他人應有的尊崇。
誠然維克多.弗蘭克所遭受的漠視已獲得某種程度平反,但對他個人而言,雙重的名譽補償卻來得太遲,因為此地不僅只有皇帝一人會貶低歧視偉大的思想家。
不過,這在三十年前終於出現充滿希望的開端。一九四六年,在一個地下小劇場裡的一次討論會上,一個默默無名的人現身舞台,就在我面前,他的個頭很小,和我們當時所有人一樣營養不良。他侃侃而談,在場的聆聽者都能感覺到那一刻的重大意義。他還引用了當時即將出版的一本書中的概念:「來自醫師的心靈治療」。
就在當晚那一刻,維克多.弗蘭克又完全回歸到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中了。
也從那晚起,我與他成為摯友,在他身邊看著他在戰爭甫結束的年代裡展開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當時的一切似乎都充滿了覺醒的新氣象,但隨後而來的年代思潮卻不若眾人原先的期盼。
就這樣,維克多.弗蘭克成為講師,其後升任教授,又成為某神經暨精神病醫院的主管,繼續他在一九三八年因殘酷不幸而被迫中斷的事業生涯。他生前德高望重、享譽國際……然而一如許多其他人,維也納也對他百般刁難,本書收錄的故事即可證明。這些心路歷程在歷經三十個年頭後,輾轉重回當初被記錄下來的故土,然而特別的是,它的旅途終點站卻是一家慕尼黑出版社,而非維也納的出版社。
這份有關集中營的歷劫報導先是由一家維也納出版社發行,初版(三千冊)全數售罄,不料再版卻成為滯銷品。數十年後,美國率先發行英文版,先後竟發行了五十餘版,多次榮獲「年度好書」獎,並打破兩百萬冊的銷售紀錄,譯本幾乎遍佈各種想像得到的文字。不容諱言,弗蘭克在維也納確實是著名學者,並未受到冷落且備受推崇,但維也納人卻令他有一股無法暢所欲言的箝制感。
由於我在戰爭甫結束的幾年內與他往來密切,因而膽敢在此坦言支持他──並非是支持一位醫生、心理學家、哲學家或學者,而是支持一個會繼續屹立不搖於社會的特殊人格、一位本應屬於維也納的良師、支持一日為我師,終身為我父的人。個人有太多該感謝他的地方,如今他的某些思想已成為我思想中的一部分,他的某些術語也成為我的辭彙寶藏。多虧從他身上習得的觀點與概念,我才得以免去諸多尷尬的窘境。
誠然,單是心中的感念亦可以信函的方式來表達。不過既然他的兩部個人著作終於在此合而為一,以德語文字呈現在讀者面前,如果不嫌太遲,更應選擇不尋常的方式來表達。
維克多.弗蘭克畢生遵循他所傳授的學理。從人間煉獄歷劫歸來,回到他的故鄉,雖然失去了摯愛的雙親、兄弟與妻子,失去了一切,他卻完全沒有報復的衝動,只有極少數的集中營生還者和流亡國外者方能如他一般大度。他隨即恢復從前一貫的模樣:維也納醫生。自始至終都駁斥「集體罪過」的理論【1】,他總是強調非人性規則中一再出現的正面例外,也從他個人及某些同伴身上的遭遇中看到善良的一面,並藉此克服了惡劣百倍的魔鬼。他「重新修補別人已經敗壞的事物」。雖然同胞曾百般羞辱他、折磨他,他卻將集中營的囚衣化成醫師的白袍,以醫療牧師的身分幫助他們。
很難想像世上會有比這個「非亞利安人」更有基督的慈悲心腸了,而且他並非基督徒。他宣揚實踐生命的意義,即便處在瀕臨死亡的邊界,其信念也無所動搖。
他的著作遍及世界各角落,但由於當時的隔離封鎖,除了奧地利以外,幾乎傳不到任何一位德語讀者的手中。初版的原書名在時代變遷的影響下成了副標題,因為時至今日,希特勒與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的集中營已成歷史,它們只是其他眾多新地獄中的一例罷了;同時,維克多.弗蘭克戰勝集中營夢魘的經驗,如今也能應用在其他許多質疑生命意義的情況,並非僅止於德國集中營的例子而已。
這個新書名是源自維克多.弗蘭克在維也納社區大學的一系列演講,之後彙集成冊發表,在此有必要稍加解釋。
話說隆納貝達博士(Dr. Friedrich L?hner-Beda)原是維也納文學家,以撰寫批判時代的詩句起家成名,曾在一次大戰期間發表過愛國詩作,後成為輕歌劇編劇家,尤其經常與作曲家雷哈爾(Franz Leh?r)合作《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微笑之國》﹝Das Land des
L?chelns﹞。他從保皇黨人士搖身一變,成為熱情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一九三八年被關入集中營後死於營內,並在布亨瓦德寫下著名的《布亨瓦德曲》歌詞。該曲由另一名維也納囚犯譜成,乃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紀錄,開頭段落以通俗的進行曲節奏呼籲受難者保持冷靜,鼓勵他們相信解放終將來臨。歌詞中有這麼一句:「雖然如此,我們仍要向生命說『YES!』。」
而這個仍要說「YES!」的信念,也是「形上學會議」【2】所要傳達的訊息,該作品第一次以作者之名,並在此透過書本的形式呈現。
當時這個訊息歷經了集中營的磨難,且構想仍相當模糊,因而沉澱多時。獲釋後一年,它從意識的深層逐漸浮現,維克多.弗蘭克在數小時內一口氣便寫下這部戲劇作品,彷彿是經由口述讓人筆錄下來似的。
數日後,他向幾位友人朗誦這部想像的戲劇作品,當時我也在場。個人必須在此強調,並非要做比較文學研究或橫向連結,批判後來其他類似的戲劇形式,但我自始至終都認為這篇在文學上也相當出色的文字,是一部極為特殊的「人性記錄」(document humain),而且令我不由得想將披著天使外衣的納粹黨衛軍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大審判官【3】兩相比較。
弗蘭克當時也將這篇文字介紹給因斯布魯克的友人圈,其中藝文雜誌《Brenner》發行人路德維希.封.菲克爾(Ludwig von
Ficker)因而結識了弗蘭克,這位特拉克爾與克勞斯【4】的至交,既重要且值得敬仰,當下便請弗蘭克惠賜手稿一份,於一九四八年刊登在雜誌中。唯有知曉菲克爾地位者,才明白這位當代同儕的推崇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弗蘭克特地為《Brenner》雜誌取了一個筆名蓋伯瑞.里昂(Gabriel Lion),結合了父親的名字與母親原有的姓氏。
雖然我曾為將劇本搬上舞台而四處奔走,嘗試至少以廣播劇的形式演出,可惜始終未能如願。如今本書重新再版,更熱切期盼該劇能搬上舞台!【5】
弗蘭克由於在故鄉受到的苦難以及因而被耽誤的人生,終於在近年獲得些許補償,不但於全球五大洲受邀演講,多次獲頒榮譽博士頭銜,並在維也納成立協會,如今他桃李、聽眾與崇拜者滿天下,活出生命的意義,他的影響力無限,也受到全世界的肯定。
不過他卻透過後面的篇章內容,賜予我們更多寶藏。藉由辯證的張力,將一段真實的生命歷程與一齣戲劇作品,化成一則符合時代思潮的全新寓言,一則關於人性軟弱與堅強,和來自上帝苦難根源的寓言。
漢斯.維格爾(Hans Weigel)
一九七七年六月於瑪莉亞-恩澤斯多夫(Maria Enzersdorf)
推薦序一
從地獄也可長出小花
南方朔
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暴行是罪惡,所以必須追究,它也是文明走到了瘋狂的叉路,因而必須警惕和反省,而同時,它也是人性缺陷所造成的煉獄,讓人受苦與死亡,因此人類必須更加努力來促成人性的復歸。
而做為納粹集中營浩劫餘生的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
1905~1997),他的這部經典著作—《向生命說Yes!》,以及他所開創的「意義治療法」,所致力的就是最重要的人性復歸這個面向。他在本書第三部「樺樹林同步劇」裡說到:「生命不能僅如糞土,我想讓它開花結果。」他想讓地獄裡也開出小花的宏願,本書就是最好的見證。在二十世紀的思想人物裡,弗蘭克為世所重,即在於他那獨特的開闊胸襟以及極為正面的思考方式。
而要介紹這本著作,最有提綱挈領效果的即是第三部「樺樹林同步劇」。這個劇本是在說史賓諾莎、蘇格拉底,以及康德這三位古代哲學家,從天上下凡到樺樹林的集中營。他們的用意是要以他們的思想來拯救人類的苦難。但是三大哲學家糾纏於種種概念裡,對人間的受苦完全無能為力,因此蘇格拉底遂說:「我們必須退場」,最好解救受苦的責任由劇中主角佛朗茲說出;「在每個當下,都必須重新下決定。」;「雖然也許是我想像出來的任務,但究竟是不是想像,這個問題只能在行動中,透過我們的行為來決定。」在劇本中,佛朗茲其實就是弗蘭克自己!
「樺樹林同步劇」,乃是頗有存在主義風格的劇本。眾所週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萌芽的存在主義,經過納粹暴行的洗禮後,已走到強調神聖個人面對人類存在情境惡劣化時,如何抵抗及再起這個方向,從人性論的角度而言,個人已等於退到了最後的防線。它也是人的責任這個核心價值的新起點,就整個時代意義而言,納粹暴行這種極端存在情境的出現,它等於已使得一切抽象可愛的古典哲學全都被打進了垃圾筒,人必須從最具體、最直接,但也最恐怖的日常經驗裡去實現自己。
「樺樹林同步劇」這個劇本就是上述道理的實現,面對集中營暴行,哲學家觀念式的談論方法已無任何意義,只有集中營裡囚徒自己的經驗。無論是善是惡,或是善惡之間的灰色,才是唯一的真實。只有在這種經驗裡,去做正向思考,而不是簡單的指控與報復,人類或許能找到得救的起源。存在哲學家沙特曾說:「別人是我的地獄」,弗蘭克則企圖在納粹這種極限臨界的情境裡去找到人類未來的可能性,因為只有如此,人的受苦始可能具有意義。人必須讓自己所受的苦是值得的,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超越受苦,讓受苦成為出發的起點。
因此,「樺樹林同步劇」可以說已概括了弗蘭克的存在哲學及人性哲學。它是弗蘭克思想最濃縮的版本。而當人們了解這點之後,再回頭去讀本書的第一部:他的集中營歷劫的記錄,就會對他為什麼不對集中營做集體式的指控,而是非常細膩的對日常生活的細節加以描述有所體悟。
因為,對集中營的罪行做出集體式或概括式的指控,由於它的指控是如此的恐怖與巨大,反而會讓人們產生一種殘酷超現實的印象,也會顯得不是那麼真切,它也會使人們真正掌握住整個罪惡的人心機制。相對的,當透過集中營日常生活的記載,它看起來沒有那麼壯闊,但受苦、殘酷,人類心靈與行為的善良面與邪惡面才會以更深刻的面向呈現。集中營是個人類社會的最極端型態,正因為它是最極端,它所顯露的光明與黑暗也就最突出。
因此,弗蘭克筆下的集中營和許多其他劫餘者的記載有很大的不同。他沒有太多劫餘後的忿怒,反而是多出了一份悲憫。集中營裡人們顯露出了苟存的競爭僥倖心理也有苦中作樂等隨死亡的那種犬儒麻痹,以及殘存的善良和悲哀。他沒有一竿子打翻一條船那樣的把受苦神聖化,而是悲憫自己,悲憫別人,悲憫整個世界。由於他是心理學家,他所看到的集中營景象遂比其他人深刻了許多。或許正因這樣的心情與關懷,遂讓他看到了從地獄裡也會開出花朵來的可能性—它就是本書的第二部分所說的意義療法。
所謂的「意義療法」,本質上乃是心理治療的一種傾向和一種範疇論的課題,它不以佛洛伊德的快樂原則或阿德勒的追求卓越的原則作為人類意志的動力,反而是將意義的找尋這個更宏觀的範疇做為意志的根本。而所謂的「意象」,根據他的集中營經驗,他其實已把「意義」的定義濃縮到了諸如愛、受苦、尊嚴、責任,對人類存在困境尋找新的自由等這些面向,因為意義療法在本質上碰觸到了人類最終極的核心價值,因此過去遂有人稱他為「最後的人道主義」。人類只有在愛、責任、自由、尊嚴這些縱使集中營的暴力都無法消滅的地方,始有可能重建意義以及人類不應被毀滅的終極合理性,因而它在心理諮商時當然也就難度較高,但人類其實不能否認,弗蘭克在這個價值渾沌的時候,終究還是想出了一個更正面的心理活動模式,這也是他對這個世界所做的最大貢獻。一九七○年代,全球盛行對愛和生命意義這些問題做出探討,都是他的思想的延伸!
一九七○年代台灣對弗蘭克的思想曾有過一陣熱狂。而今時移境遷,重讀他的著作,當會發現他所留下的,縱使到了今日,仍有極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智慧不會老的見證。
(本文作者為知名文化評論人)
推薦序二
觀其文,知其人—弗蘭克醫師的生命意義
張利中
人文是人的話語,在研讀人的話語之前,最好先認識、知道其人。維克多.弗蘭克(Victor Farnkl)是維也納的一位精神科醫師,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受苦的猶太人,我們可以先從猶太人的受苦談起。
猶太人自詡是上帝的選民,在經歷了出埃及等一段段苦難與流離的歷史之後,於西元前一千年間,在巴勒斯坦這條通渠大道上建立了猶太王國,在眾多帝國的環伺之下,注定了這個民族受苦的命運。於西元第一世紀的羅馬統治開始,猶太人經歷了將近兩千年「無國、無土」的大流散歲月。四處移居與受人逼迫的猶太人,始終秉持著對於一神上帝的信仰,維持其民族意識與生存。猶太隔離區(ghetto)在歐洲其來有自,絕對不是在納粹德國底下的新鮮事物;而集中營的火舌煙灰則是猶太人受苦的極致。弗蘭克便是在經歷了人間最大浩劫之餘,說出了有關猶太人此一受苦經驗,說出了「人」如何能夠在終極的苦難之中,依然堅毅地而有尊嚴地活下去的見證。所以閱讀本書,真的不應該脫離了此一受苦意識,將這本《向生命說Yes!》僅僅視為一本傳授心理治療「技藝」的手冊。而更應該是看待上帝的選民,如何在經歷浩劫災難之後,來切身地告訴我們,受苦是什麼?人如何能夠超越「苦難」,而也正是在受苦之中,意義能夠幫助超越一切!
筆者以及國內的一些學者及研究生,每兩年會前往加拿大參與「國際生命意義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ersonal Meaning)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的精神領袖就是弗蘭克先生。會中的一個特殊安排是邀集弗蘭克晚年的學生或是他的家人、子孫,來親身分享他們與弗蘭克相處的經驗。
其中有一個故事說到:有一天弗蘭克於維也納,走在往市政廳方向的街上,遠遠望去,在他之前有一個人的身影酷似佛洛伊德,隨著那個身影,十五分鐘後,終於在市政廳前,弗蘭克追上也確定那位走在他之前的人物是佛洛伊德。弗蘭克也因而調侃地說道:「在我一生之中,只有也只有那十五分鐘的時間,我是佛洛伊德的追隨者。」確實,弗蘭克所提倡的「高度心理學」與傳統精神分析心理學所提倡的「深度心理學」是極為不同的。在集中營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受制於「基本需求」或者是「性趨力」的支配;就是有人會為了尊嚴、同情、審美與宗教體驗,而捨棄了極為稀少珍貴的麵包、熱湯,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而起身與蓋保工頭對抗!人在集中營內,有可能變得冷漠,有可能變得麻木不仁,但是人性的光輝依舊存在。儘管是面對如此乖離的命運,弗蘭克本人就在幾次緊要的關頭上,選擇對其職責與照顧的同袍不離不棄,反而帶著他遠離了險境。我想弗蘭克要說的是,在最壞的情境中,在惡極的團隊裡,都還會有人堅持人性,堅持精神的存有,且發揮良善。在堅持人性與精神存有之中,而任由命運擺佈,也就是對於命運做出了超越的行動。
在樺樹林的同步劇中,蘇格拉底、史賓諾莎與康德三位哲學家的登場,為的是要說明人生有「超越的」,以及「更大的」意義架構存在。在永恆之中,人的存有極為短暫;在神的創造之中,人的「生命圖像」有其界限,哲學家要人思考更廣大的意義範疇。劇中讓人受苦的黨衛軍,竟然是黑天使的化身。這一切的受苦都應該被視為考驗,考驗著劇中受苦的兩位兄弟。母親的亡魂不捨其孩子的受苦,而哲學家卻奢言「這是考驗」,「痛楚又算是什麼?」(若是叔本華也在場,還會喜孜孜地說:「我早就告訴過你!」)。這些哲思,換來的是母親的喝叱:「這話私下說說還可以,但不准您向一位母親說這樣的話。諸位,這種話,不能告訴世上的任何一位母親……」。
換言之,哲學家忙於分辨受苦的意義,母親則是以「當事人」的身份發出警語—定義「苦難」的本質是一回事,而面對他人的受苦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本書英文序作者哈洛德.庫希納(Harold
Kushner)在其《當好人遇到壞事》一書中,對於此一論題,有更切身的描述,建議讀者參閱。總之,不論是「自身」的受苦,或者是「他者」的受苦,都有待吾人以「責任」加以回應,有志於學習意義治療者,則應該認同弗蘭克在書中強調放棄「導師」的角色,學習列維納斯(E. Levinas)對於他者「容顏」的倫理回應,也或許最後才是蘇格拉底「意義接生」的技藝。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