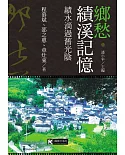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物裡看花,從物裡學。〉
晚春某個晴朗日子,水悄悄從系館三樓的排水口湧現,沒有人發覺。它緩緩沿著週末無人的教室走廊,自門縫流進了我的研究室。每一珠水滴都熱切吻著木質地板,滿屋子瀰漫著濕漉漉的腐朽氣味。待我發現時已近黃昏,幸好滿牆的書籍唱片無恙,賴以維生的電腦無恙,有用無用的各類物品也都安在高處,未遭這魔幻般突來水患的波及。
即使擦拭擰乾、又連續除濕了兩天,滯留在裡面看不見的水,還是三不五時就從地板的縫隙探出頭,隨機形成一個又一個小水窪。而寬一米多的仿古彩繪木板,因為和水的交媾而改變了其平坦姿態,接合處開始隆起,彷彿地層變動擠壓而成的小丘。怎也沒想到,只不過是些偶然闖入的水,就足以讓我日常棲息的小小世界,產生如此哭笑不得的地景變化。
接下來的一星期,半個處女座、無法忍受凌亂的我,幾乎是在一種「無奈面對這般失序狀態,以致於有點自暴自棄沒法專注工作」的逃避心情中度過。每天矛盾想著:要如何修繕重整?又該怎樣抽出時間、擠出經費?人因此煩躁起來。淹水後的研究室,如蔡明亮電影裡潮濕幽暗的空間隱喻,也暫時沒了音樂、閱讀與冥想。直到某天午後,窗邊的馬口鐵機器人,彷彿跟我說話似地,把我拉了回來。
那是個年代久遠的鐵皮玩具,跟隨我飄洋過海回到此處。只要轉上幾圈發條,就會喀吱喀吱地搖晃行走。那天他一如往常靜靜站在矮櫃上,外頭春陽暖暖,光線穿過窗外的樹梢,把他投射得神采奕奕,即便連?斑都有了光澤似的。我凝視著小機器人,這才發現他周遭積了點灰塵。有趣的是,那些灰塵非但不讓人感覺髒污生厭,甚至在份量恰到好處的日照中,產生一種如亮粉加乾冰般的氤氳。
彼時,我有一種說不出、別人也不見得能懂的滿足感。就像村上春樹在《蘭格漢斯島的午後》中所描述,「抽屜裡塞滿了折疊整齊捲好的乾淨內褲」,或「將嶄新散發著棉花味道的白色汗衫從頭上套下來」的時候,某種名之為「小確幸」的東西。就是這細瑣微小、但明確紮實的幸福感啊,足以令所有潮濕陰鬱瞬間揮發在光亮之中;讓倒楣的無妄之災,消融在乍現的靈光裡。
於是我擱置了整修裝潢此一過於龐大的計畫,放棄「恢復原狀」或「打造新居」等種種完美想像。學院裡外忙碌的工作重新啟動,隆起的地板、隱晦的水漬、潮腐的氣味,逐漸被日常的起伏、身體的活動,撫平、抹去、稀釋。相對的,我開始利用餘暇,逐項檢視堆積在房裡的各類物件。這些東西有的可實用、有的卻很「沒用」,有的貼近地面、有的盤踞高處,無論如何都不捨晝夜環繞著我。它們是這個小宇宙裡一顆顆無足輕重、孤寂存在卻又發散溫暖的星球。
或許,人對某物的擁有,與其說是擁有它「作為工具」的這個實用層次,不如說,是擁有某種從它特定功能中抽象而出的事物。如此,物(thing)才會真正成為人的「物件?對象」(object)。而既然這房間裡的所有物件都面向著我、成為我的「對象」,它們之間也就巧妙地相互指涉。本來沒關係的物件,此時此地都有了新的意義聯結。
這讓我憶起在劍橋的某個隆冬,陷在永遠讀不完的書堆裡慌張不已。偶然進入了班雅明(W. Benjamin)對巴黎拱廊街的研究筆記,深深著迷於那種蒐藏、凝視、剖析細瑣物件的奇趣,而幾乎忘卻了屋外的大雪紛飛以及課堂報告的火燒屁股。據說班雅明是個狂熱的藏書家,蘇珊?桑塔格(S.
Sontag)說他「藏書並非為了專業用途,而是藉以當作冥想的對象物和引發沈思的媒介」。此外,他還喜歡舊的玩具、郵票、明信片,以及「輕輕搖動裡頭就會出現飄雪小鎮」的玻璃球。
孤獨的班雅明,既是卻也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和當時講求科學、宏觀的左派主流背道而馳,默默進行著一種顯微鏡式的日常觀察,用他的「第三隻眼」窺看這個由物與人共構的大千世界。班雅明喜歡反覆探訪乏人問津、細瑣微小的事物。小物件對他(收藏家與漫遊者的雙重身份)而言,是可以隨身攜帶的適切「對象」。此外,事物的微型化也意味著對所謂「正常狀態」的扭曲、打碎和重組,於是成了有利於凝視與冥想的對象物。而這一切,不只構成班雅明的研究主題,或許也是在他長期憂鬱的歲月裡,賴以延續生活的小確幸。
如果說,波特萊爾(C.
Baudelaire)是浪遊在城市邊緣、尋找詩意碎片的拾荒者,那麼班雅明則是個擁有自己小宇宙的收藏者(儘管他的生活並不闊綽)。這裡的「收藏」並不是指那種藉由佔奪商品以炫耀自身、甚或等待增值以求取利潤的布爾喬亞嗜好;相反的,在使物品得以逃脫商品化的市場禁錮,納入擁有者自己的價值與意義體系。班雅明如此宣稱收藏的政治意義:「讓東西不僅僅是為日常生活世界所需所用,更讓它們從實用而單調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來。」
無論在晨間或深夜,每當我靜靜閱讀這研究室裡的一書一物,或為之拂去灰塵,就會感到一種奇妙的慰藉和安定。在一切都可以機械複製、城市生活看似多樣其實單調的年代,物被大量生產而消費、甚至丟棄;人則被捲進市場,和物一起受禁錮。只有在我們不斷凝視與閱讀物件的練習裡,人才真正自由而富足地擁有了這些對象物。漢娜鄂蘭(H. Arendt)說得好:「這是對物的拯救,也是對人的拯救的補充。」
由此,自我和物件所共同構築的小小宇宙,是對我們所失去世界的小小補償。對物的收藏、凝視與閱讀,成了一種建築工事,既是不同時間的堆疊、也是相異空間的混凝。在這裡頭,自我被微妙地從外在世界的混亂與虛無中隔開,在記憶和想望的碎片中,悄悄而紮實地重建。
突如其來、擾亂生活秩序的一場小水患退散了,即使它留下的改變還清晰寫在腳掌和地板之間。然而,因為一個小物件所偶然帶來的冥想,或者說,一顆平凡小星星引發我重新感受自己賴以生存的小宇宙,這樣的體驗足以抵禦一切不可預測的災難以及日常無趣的反覆。於是,我計畫起一段旅程,但這次既不走遠、也不像果戈理(N.H.
Gogol)所說「要發現自己的地理學」;而只是,在生活轉角處,重新探訪各種尋常物件,嘗試建立屬於自身的物「裡」學,發現取悅自身的,小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