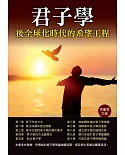明清以來,西學開始東漸,受此影響,明清士子持續討論著中學與西學的關係,爭論著西學是否源自於中國,還是有其自身發展脈絡?本書的主要問題是:西國士子如何面對西學東漸?為了瞭解此一問題,筆者試圖以明清的西學來自中國與否的爭議為課題,探索其中過程,釐清其歷史發展與流變。
目錄
第一章 序論 1
第二章 明清處理西學的主流看法及其演變-西學中源論 13
第一節 明末西學中源論的起源及其清初發展 14
第二節 自強運動時期的西學中源論 52
第三節 晚清西學中源論者的自然知識表述 70
第四節 結語 100
第三章 明清學者對於西學中源論的質疑與批判 103
第一節 明清之際士子對於西學中源論的質疑 104
第二節 傳教士對於「西學源始」的介紹 117
第三節 王韜與《西國天學源流》 140
第四節 結語
第四章 《天演論》作為反西學中源論的存在
第一節 中、西哲學比較與重新詮釋
第二節 突顯「迥異」的西方歷史
第三節 不同的西學知識基礎
第四節 結語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序
黃克武
雷中行先生將他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2007)修改出版,我感到特別的高興。他自幼生長在史學氣氛十分濃厚的家庭環境,其後秉承庭訓,考取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這一本論文最初受到徐光台教授啟發,其後由我與該校黃敏枝教授共同指導,口試時又承蒙師大洪萬生教授、清華大學鍾月岑教授多方指正,可以說是結合了台師大、清華與中正大學三所學校的史學傳承,而孕育出來的一個作品。口試時委員們均認為這一篇論文花了很大的功夫,深具價值。一年多之後,我們終於看到這一本書的問世,無論是對於較廣的明清科學史、中國近代思想史而言,或者較專門的嚴復研究來說,中行這一本書都具有突破性的貢獻。
中國近代史上的「西學中源論」和一個相關的題目如「中國文明西來說」一樣,是一個不太受到學界重視的題目,主要的原因是現在的讀者大多會覺得這類的理論是過時的,甚至可以說荒誕不經的,因此不值細究。然而,如果我們回到明清以來的文化脈絡,卻會發現,這些理論都曾經風行一時,甚至許多一流的知識分子都對之深信不疑,而撰文鼓吹,如黃宗羲、章炳麟、梁啟超、俞樾等。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此一現象呢?我們必須返回到當時歷史的場景,重新來檢視這些問題所源生的文化場景與思想論域。「中國文明西來說」最近有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與李帆等人的研究,中行這本書則重新檢討了「西學中源論」。
過去學界有關西學中源論的研究甚少,我們對此議題的認識多半依賴全漢昇教授在1936年所撰寫的〈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或是王爾敏、熊月之等學者的作品,這些研究成果或是為時已久、或是較為簡略,難以窺其全豹。中行的專書可說是首次從長時期的歷史演變與深入的文本分析兩方面,來探討此一議題。他不但仔細地討論了明末清初以來幾位重要的「西學中源論」論者的想法、釐清其脈絡,而且指出了「西學中源論」內部的複雜性。
例如當時有人考察知識源流,進而指出「新學新知只是深入補充中學的粗疏之處」(劉嶽雲);有人則在古籍中找尋各種依據,來證明「西學中源論」的成立(王仁俊)。有的學者藉此抒發己見,或企圖貶抑西學、鑽研中學(阮元、張自牧);或藉此消除人們對西學的敵視、強化西法學習之正當性,進而促成中西學的會通(如梅文鼎、奕訢、張自牧)。此外還有學者,像薛福成,不但本身的想法有所轉變,而且又將「西學中源論」改為「西學東源論」,綜合考察埃及、希臘、印度、中國等文明對西學形成的影響,使此一理論更為圓融。上述的各種觀念都冠在「西學中源論」的大帽子之下,經過本書作者的釐清,我們得以瞭解其內部複雜、多元的面貌。
本書不但深入分析「西學中源論」的內容,也描繪了當時學者對它的質疑與批判的情況,這兩者猶如兩軍之對壘,展現思想界的交鋒。如李之藻、江永、趙翼等都指出南宋時陸九淵所謂「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中國與歐洲其實互不交流,只是因為具有一些共同的心理趨向,而觀察、發明出一些類似的科學理論;另一些人如新教傳教士與王韜則是對於西學源流的考察,展現西學自有其本身的體系,與中學無涉。順此理路,作者提出了他對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他認為嚴復翻譯此書的原因之一,就是藉此說明西學本身獨特的歷史發展、批判西學中源論,以糾正官紳士子對西方的淺薄認識。我認為這個說法完全可以立足。
有關嚴復對西學中源論的反應,最早要追溯到他赴英國留學期間的經驗。1878年3月12日在英國留學的嚴復與當時擔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討論到張自牧(力臣,1833-1886)的〈瀛海論〉(張自牧的「西學中源論」,可參見本書第二章)。張自牧是郭的好友,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兩人討論時事、洋務,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郭稱讚他「於洋務所知者多,由其精力過人,見聞廣博,予每嘆以為不可及」(1879年5月9日日記),由此可見兩人關係匪淺,且在積極認識西學上具有共識。在郭出使之前,曾保舉當時為「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的張自牧作為二等參贊官,後張因故未能成行。
嚴復在與郭嵩燾討論時很直率地批評了張自牧的「西學中源論」。例如張自牧認為基督教其實是源於墨子的想法,加上印度、阿拉伯的觀點。他在〈瀛海論(中篇)〉中說,「耶穌天主之教……蓋墨氏之本旨,而緣飾以桑門天方之說,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一以朋友之道處之,博施尚同,而昧於本末親疏之道。」[ ]張自牧並表示「天主」二字源於中國。郭嵩燾記載了嚴復對他的質疑:其辟力臣論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以為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傳實始東土」,不識所流傳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則羅虛克蘇力也,何處覓「天主」二字之諧聲、會意乎?
嚴復也知道郭、張為好友,並認識到張自牧的「西學中源論」說法具有積極開拓西學的意義,張自牧藉此指出不應排斥西學,且儒者應以不知西學為恥;不過嚴復也看到張自牧思想中與舊有觀念的妥協面,他批評張自牧對鐵路、機器的保守態度,以及對海防工作的忽略。由此可見嚴復對西學中源論,或藉此論來接引西學的作法,早有質疑,而後來他在〈《天演論》自序〉(「富文本」)中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可謂其來有自。
作者在論證嚴復以《天演論》批判「西學中源論」時,有一個在材料運用上的重要特點。他運用了與目前通行的《天演論》不同的早期版本,亦即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於1998年出版的《嚴復合集:天演論匯刊三種》中所收錄的「味精本」、「手稿本」,與「富文本」。尤其文中對於「重構聖人意義」之分析,最為精彩,作者引用「味經本」中的兩段話:
今夫移風易俗之事,古之聖人亦嘗有意於此矣。然而卒不能者,格物不審,見道不明,而智慧限之也。居今之日,藉真學之日優,而思有以施於濟世之業者,亦惟去畏難苟且之心,而勿以晏樂媮生為的者,而後能得耳。
〔世人〕視聖智過重,以轉移世運為聖人之所為,而不知世運至,然後聖人生。世運鑄聖人,而非聖人鑄世運也。徒曰明自然而昧天演之道故也。
這兩段話的確展示西方的「智慧」讓嚴復對聖人觀念作出新的詮釋。對嚴復來說,新的聖人可藉西方的智慧去實現以往「移風易俗」的道德理想;然而另一方面聖人的能力又有所限制,必須要依賴「世運」而起。此一想法與嚴復在〈論世變之亟〉(1895)中所論完全一致: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日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唯知其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睹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
由此可見嚴復所謂的「世運」其實是結合了西方的「天演之道」與宋朝邵雍的「運會」觀念,這也顯示此一聖人仍與宇宙有直接的關係,不能以「除魅化」或「世俗化」的觀點來看。換言之,嚴復所重構的聖人概念既有延續,亦有創新。
上述的討論依賴早期《天演論》的初譯本,而非後來的定稿本。在此可約略對這些版本的差異加以說明。「味精本」是由陝西味精售書室刊印,該書有「去今光緒二十二年丙申……」(頁39)的字眼,可知是嚴復譯於1896年的初稿本,根據陝西學政葉爾凱與汪康年的通信,此書係味經書院劉古愚(與康梁關係密切,可能是透過梁啟超取得此一版本)編校出版。[ ]孫應祥、王天根兩位先生對此版本的源流有詳細考證,可以參看。至於「手稿本」題名為《赫胥黎治功天演論》,現藏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手稿墨書,以紅藍綠各色筆作修改」(頁81),冊中有刪改過程的日期標示多處,如「丁酉六月初六刪改」(頁155),可知是1897年嚴復修改的版本。根據筆者考訂,這一個版本是1897年3月請呂增祥至保定面交吳汝綸的本子,吳汝綸在上面以黃、藍筆作批註,再由嚴復改定。有關吳汝綸對嚴譯《天演論》的具體貢獻,可參看拙著〈走向翻譯之路〉。「富文本」由南京富文書局出版,印於1901年。它與1898年正式出版的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本,大致相同,僅刪去後者〈譯例言〉中說明版本來源而註明「嚴復識於天津尊疑學塾」的一段話。「富文本」與1905年商務印書館的版本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在「味經本」與「手稿本」刊行之後,多數人只是藉此考訂其版本流傳,而忽略了經吳汝綸建議而為嚴復所刪除的許多字句,以及它們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這些句子是嚴復翻譯赫胥黎著作的最初感受,只要稍微比對「味經本」與「手稿本」就可以發現,這些被嚴復「勾去」的文字主要有以下兩類。嚴復在「手稿本」的「譯例」(這一部分在「富文本」中被改為「譯例言」,其內容或有所擴充,或被刪除)對此有以下的說明:
原書引喻多取西洋古書,事理相當,則以中國古書故事代之,為用本同,凡以求達而已。……有作者所持公理已為中國古人先發者,謹就譾陋所知,列為後案,以備參觀。(頁85)
在「富文本」的「譯例言」中前半段完全被刪除,而後半段則被改為「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則就譾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考」。這個對照很值得注意。這顯示在1897年春天嚴復將譯稿給吳汝綸之前,他對中西學的關係有一些徬徨,他知道「由此而必謂西學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固無所事於西學焉,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蓋發其端而莫能竟其緒,擬其大而未能議其精,則猶之未學而已矣,曷足貴乎?」(「手稿本」序,頁83~84,作於1896年秋)這一段話在「富文本」之中略有所改動,但大旨相同。問題在於他同時也相信赫胥黎的觀點之中有「所持公理已為中國古人先發者」,這樣的想法也使他很大膽地採取所謂「換例譯法」,將西方的事例取代為中國古書中的事例(嚴復在1908年翻譯《名學淺說》時仍多次運用此一譯法)。在吳汝綸批改嚴復的初稿之後,嚴復在這方面變得更為小心,他不但刪除了中國事例,也勾去了正文之中插入的《易經》、《書經》、《孟子》等古書上的話。換言之,吳汝綸的提醒使他更意識到西方歷史的獨特性,而且不再說有些西方公理「已為中國古人先發」。此後嚴復轉而強調「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這種對中西學關係的矛盾態度,亦即一方面認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又以為兩者部分相合的想法,與嚴復一生中企圖建立一個會通性的理論來解釋「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係的問題」與追尋富強、自由與文明之新中國的理想,一直交織在一起。如果說在1890年代末期嚴復集中火力攻擊「西學中源論」的話,那麼到了1900年代,他又把焦點放在攻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在這方面1902年所撰寫的〈與《外交報》主人書〉一文最具代表性。而民國成立之後,他再將矛頭對準陳獨秀、胡適等五四健將的「全盤西化論」,很可惜此時他只能發出很微弱的聲音,激進的時代掩蓋了嚴復對中西文化接觸、互動的深沉思索。嚴復與清末民初三種最具影響力之文化理論之對壘,足以映現他本身「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或所謂「繹新籀古折以中」的理想。本書作者對於「西學中源論」的深入討論,幫助我們釐清了這一段糾葛不清的歷史與嚴復在這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新書9折$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