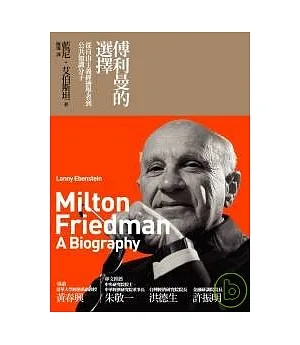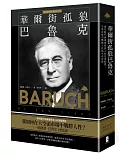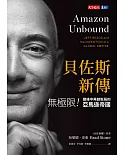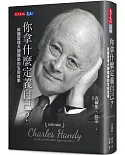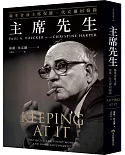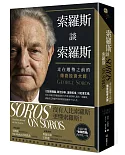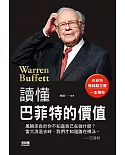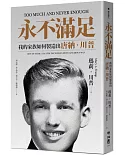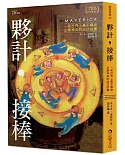導讀
傅利曼的選擇 清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黃春興
I.
本書論述二十世紀後半期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大師,也是1976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一生的志業。國人對傅利曼不會太陌生的。他的兩本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與《選擇的自由》,分別於1973年和1981年發行中譯本,即時提供台灣社會經濟自由化所需的理論和勇氣。1988年,他和中國大陸總理趙紫陽的對話紀錄也曾撼動兩岸。1998年,他和妻子的共同傳記《兩個幸運的人》,讓國人更深層認識他的生活點滴和奮鬥過程。除了他自己的著作外,吳惠林發表在報章的介紹、邱正雄的推薦、張五常借用朱自清的標題另寫的〈背影〉等文章,都讓我們忘不了這位自由主義大師的身影。
除本人外,我們對他的經濟理論也不算陌生,畢竟他所領導的芝加哥學派或重貨幣學派主宰70-80年代的經濟學界,而廣義解釋的新古典經濟學派至今仍是主流。讀者只要帶點耐心,就能從本書的論述讀懂傅利曼在經濟理論的主張,也會發現他的經濟理論和自由主義分不開。但是,我們對他一生宣揚的自由主義就沒那麼清楚,好像也不容易搞清楚。
傅利曼選擇的自由主義偏向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我譯為自由人主義),主張「只要不做傷害人的事,成年人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以任何形式形成的政府都應該扮演更不重要的角色」。這個流派有時被稱為自由主義右派,和當前台灣知識界普遍接受的自由主義左派在政策主張上有蠻大的差異。更麻煩地,學派或流派只是個通稱,每位稱得上大師的學者都有自己的邏輯體系,即使和同流派的學者之間也存在差異。在自由意志主義陣營中,傅利曼的思想算是最左的,也因此一位自由意志主義右派學者莫瑞.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1926–1995)就指責傅利曼骨子裡是集權主義和國家主義。
或許樹大招風,我們可以這樣說:學者們似乎不願意為其蓋棺定論。傅利曼的政治經濟哲學的價值仍充滿著爭議。讀者若有興趣,可連結英文Wikipedia的傅利曼網頁,就會立即看到如下的警語:「本條內容存在爭議,編輯期待能有第三種意見。」這是其他思想大師的網頁看不到的現象。
II.
2006年底,傅利曼與世長辭,本書也剛好完成。本書作者在序言說「這並不是一本正式或經過授權的傳記」,明顯地,他不想出版一本更完整的傳記。另外,在出版《兩個幸運的人》到去世的七年間,傅利曼也沒太多新的活動,也就不需要新的傳記。因此,作者把書定位在「聚焦於傅利曼在經濟領域的研究成果與他倡議自由意志主義概念及政府改革的立場。」
本書的最後一章是兩頁的〈結語〉,這應是完稿後巧遇傅利曼的過世,作者才補上的,而原本的最後一章是〈第二十四章 傅利曼的價值〉。在這章裡,作者藉著華盛頓智庫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對傅利曼的推崇來定位其在政治經濟哲學上的價值,因為卡托研究院是美國自由意志主義最重要的基金會。本書作者藍尼.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是自由意志主義的資深學者,他於2001年出版了另一位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傳記。海耶克也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和傅利曼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共事十多年(1950-1962)。作者在2000-2005年之間五度訪問傅利曼,估計是在完成海耶克的傳記稿之後開始寫作本書。從這些歷練看,作者有意要為傅利曼定位,而他也的確具有這資格。
給一本傳記寫導讀是很白目的,所以我也得幫自己找個書寫的說詞,把導讀定位在幫助讀者理解傅利曼的自由意志主義。其實也是,對這位影響甚巨的自由主義大師,我們多麼不願意在讀完整本書之後還困惑其思想地位。
III.
站在金字塔前仰望,見強烈陽光繞射,塔尖高聳卻模糊:誰不震撼於國家權力的無所不能?個人何其渺小,連一塊堆積金字塔的石塊大小都不如。想想,有多少滿懷理想的青年人,企盼能爬上塔尖,指揮國家權力以造福百姓;若有自由的嚮往,不過是想逃避被權力宰制的夢。直到十八世紀發現了市場機制,有了自由主義,人們才敢於挑戰國家權力和集體動員,因為有了讓社會與人類發展得更好的知識。
海耶克早年相信政府規劃的效率,直到在經濟景氣研究中認識到市場機制,才轉到自由主義。年輕的傅利曼也一度支持凱因斯政策和小羅斯福的新政,直到進入芝大,才逐漸認識市場和自由經濟。2005年,年老的傅利曼寫下了一段類似海耶克口吻的話:「一個以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為基礎的體制,讓人類得以在經濟活動上合作但卻不受壓迫的一種高超手段。它讓分散的知識得以確保每項資源都獲得最有價值的使用,而且以最有效的方式和其他資源結合在一起。……世界上充滿各式各樣偏離完美市場的情況,很多……都是因為政府干預而產生。」
傅利曼認識市場的過程較為間接,起點是從他與芝大的考爾斯委員會 (Cowles Foundation)
爭奪經濟系的主導權開始。「委員會所秉持的數理方法不僅充分反映當時全世界經濟專業領域的趨勢:…數理表達方式是描繪與瞭解經濟活動的最好方法」(第88頁)。聰明的他承認對手強調「數理表達」的方法論的確邏輯嚴謹,但也指出其弱點是對經驗事件和知識沒有貢獻--除非這些數理模型能滿足「預測能力」之判準。在戰勝考爾斯委員會之後,他繼續以「預測能力」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批評奧斯卡.蘭區(Oskar
Lange, 1904-1965)的社會主義計畫模型。蘭區不久離開芝大,回到波蘭推動計畫經濟。「當時一般約定成俗的觀點,認為共產國家所採行的集體主義和指令式經濟制度的生產力高於…西方國家採行的經濟制度。」。雖然傅利曼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成功地幫他立足於芝大,但是,缺欠嚴謹數理模型的自由經濟體系憑何能耐勝過集體主義和指令式經濟制度?若無好的說詞,他對自由經濟的信心又如何能產生?
本書詳細陳述了傅利曼在芝大期間的三件學術工作,它們看似獨立,卻相互交織出他對自由經濟體系的透徹理解和信心。
第一件工作是完成《消費函數理論》。(第十一章) 當時,凱因斯認為「當經濟趨於成熟,平均消費傾向就會降低」,並以此展開赤字財政和宏觀調控等理論。傅利曼依舊認為「除非理論符合事實,否則就必須否決」。在提出假設並進行測試之後,他認為凱因斯用以建立其系統的關鍵點在實證上站不住腳的,因為事實發現是:隨著所得通盤上升,消費傾向並不會降低。
第二件是出版《價格理論》。(第十章)不同於《消費函數理論》強調的是代表性個人的消費選擇和對外在環境的反應,他在《價格理論》中強調「經濟學……涉及不同個人之間的合作與互助」。由於本書本身作者是一位自由意志主義的經濟學者,因此他能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經驗對傅利曼在發展他的自由經濟的重要性:「實證經濟學裡的主要差異存在於貨幣理論與價格理論之間,貨幣理論是用來解決通盤價格水準……價格理論則用來解決資源在不同用途的分配情況」。也就是說,經濟學者若以價格理論去觀察現實社會,看到的是個人對其持有的資源有不同的利用主張,然後透過市場完成不同人之間的合作與互助。但是,這些包括主觀主張的個體資料並非實證經濟學所蒐集的數據;實證經濟學蒐集的是以加總方式去除個人差異性之後的總合數字。經常研究這些總合數字的經濟學者無法理解市場的運作,只看得見政府政策所造成的總體影響。一位經濟學家若只懂得政府政策的總體後果而未能理解市場的運作,如何可能發展成一位捍衛自由經濟的學者?
第三件是他與修瓦茲出版的《美國貨幣史》。(第十三章)在《美國貨幣史》出版之前,世人認定1929年大蕭條的禍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剩餘加上投機者的貪婪,聯準會也已經竭盡所能,因此政府必須負起總體經濟的管理責任,這也促成了小羅斯福的新政。他們花了七年時間整理資料,追蹤長達一世紀的美國貨幣政策,認為聯準會應該為大蕭條負起全部責任:「人類應該記取的真正教訓是:政府讓他們失望。貨幣體系的管理不當才是引發大蕭條的元兇,而不是市場制度的失敗」。另外,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說:「引起大蕭條……不是民間創業體制天生不穩定的訊號,而是少數人錯誤對貨幣體系行使巨大力量而形成龐大傷害的證據。」由於《資本主義與自由》於1962年出版,而《美國貨幣史》於1963年出版,我會認為兩書的觀念同時成形。
傅利曼對於政府應有的角色本無預設立場,由於消費函數的實證結果駁斥了凱因斯理論的關鍵假設,讓他難以接受凱因斯對民間創業經濟體系先天不穩定的指責,也無法同意政府可以藉口充分就業或經濟成長而介入市場。當他從大蕭條的研究發現政府的不可信任和其政策錯誤導致的龐大傷害後,傅利曼進一步相信政府其實較市場更不穩定。他也假設如果聯準會當時在貨幣政策沒有失誤,大蕭條就不會發生。由於《美國貨幣史》質疑的並非政府操控貨幣政策的權力,因而引起自由意志主義者質疑傅利曼的自由主義立場。自由意志主義者視貨幣為一項社會自然長成的制度,不僅貨幣的價值不宜受到政府的干預,連貨幣的發行都不宜讓政府介入。
的確,從實證經濟學走向自由主義的傅利曼在看待政府功能上傾向於從現實和歷史經驗的成效著眼,這種態度和他的同事George Stigler以及芝加哥大學的另一位自由主義者但否認是自由意志主義的Ronald Coase相近,而Coase也是強調以個案研究為中心的實證方法論。相對地,出身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von
Mises或羅斯巴德則較傾向自由意志主義右派,他們嚴格畫定政府權力不能跨越的界限,因為他們擔心政府一旦跨越界限,人們會逐漸習慣於失去自由的生活,就如同熱水煮青蛙,等到青蛙覺悟時已經為時已晚。
IV
傅利曼自豪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被自由意志主義右派批評為自由主義的成分不純,因為它允許政府採行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教育券的構想和負所得稅制的設計,而這基本上是冒犯自由意志主義的禁忌。其實不只有他,贊同教育券構想的海耶克也遭受自由意志主義陣營類似的批評。
傅利曼與海耶克在芝大共事十二年(1950-1962),雖然兩人交情和學術對話不如人們的想像那般密切,但傅利曼在自傳中說到:「……以前,我對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學的興趣只屬插花性質。……1950年海耶克到芝大任教後和他討論而進一步強化。」(《兩個幸運的人》)本書作者認為「傅利曼在哲學方面受海耶克的影響更加明確……《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裡有很多章節的內容都可以看得到海耶克的影響力。」海耶克或許真的啟發了傅利曼對於公共政策的高度關心,但重要的是:是否對公共政策的高度關心,使得他們相較於其他自由意志主義者允許政府有較大的活動空間?
讀者得注意,這幾項都屬於具有正的外部效果的公共政策,都是屬於補助而非管制或干預的政策。對自由意志主義右派來說,政府只要跨越界限就不可以;但對自由意志主義左派來說,政府補助並不會侵犯人民或其私有產權,雖然問題的確是轉移到租稅去了,而租稅也是自由意志主義右派必須面對的議題。
譬如低所得問題。自由意志主義有著和傳統中國類似的「救急不救窮」的界線。然而,由於窮的問題已經被分割為二,傅利曼僅視貧富差距問題為傳統的救貧問題,而貧窮問題則是接近於救急問題。他反對政府對窮人提供各種福利,因為那會影響個人與家庭的消費權利,但他主張政府直接將補助款發給個人,其方式採取負所得稅的一般原則,也就是政府以固定的稅率補助所得低於免稅所得的個人或家庭。明顯地,負所得稅的邏輯得依附在單一稅率或等比例稅的所得稅制下,而這是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長期主張。不過,到了晚年,傅利曼就不再提負所得稅制,並不是他的立場轉得更右,而是他擔心會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發展。他說:「如果一個人生在一個鮮少社會救濟支持的世界、生在一個要求人們必須為自己負責的文化中,那麼這個世界裡的那種人就會明顯少於一個把政府協助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裡的那種人。」
再如教育,自由意志主義者通常認為最好透過家庭來做,而自由意志主義右派更認為政府權力不宜進入家庭,即使他們明瞭教育對社會具有正的外部效果。傅利曼也不希望政府去辦教育,只要求政府提供教育經費,因為他擔心會有家長們不願意或無能力為孩子們提供,尤其是社會經濟背景較低的家庭。(第二十三章)他的辦法是讓國家為每個孩子的教育提列準備金,但不是為一般的教育項目提列預算,而讓市場去提供教育。「學生可能因教育券制度而獲得的利益因多元、選擇和競爭,他們將體驗到更多的機會。另外,他們也將體驗到所有學校績效的改善。」由於教育券制度一直無法實施,直到去世前一年,傅利曼還痛心地指責美國教育的問題都是「因為美國教育體系是由政府獨占的事業。」
對於教育,他的立場較負所得稅略左,因為他把教育視為改變窮人的唯一手段。2005年,他在訪問中說到:「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貧富不均的程度有多大,而在於市場上存在多少可以讓個人擺脫最下階層,擠身上流階層的機會。如果人們的地位向上推進的情況良好,他們就會接受市場效率。一旦存在這樣的機會,人們對貧富不均的容忍度就很大,這就是美國體系的可取之處。」
V.
早期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執在於政府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相對效率,這些考慮使傅利曼投身自由主義陣營。上個世紀底,市場機制贏得勝利,社會主義從此也不再「意味政府掌握所有以及政府管理生產方法。……目前的社會主義只代表政府從有錢人手中取得收入,並轉將之轉給沒有錢的人。……保有所有權的還是人民。」(第355頁)。既然所有權只在人民之間轉移,自由主義陣營便隨之分裂成自由主義左派和自由主義右派。傅利曼選擇自由主義右派,也就是自由意志主義,不希望政府在移轉所有權時直接影響到個人的消費選擇。
由於進入自由主義的過程是起於他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傅利曼傾向於從相對效率而非絕對界線來看政府的功能,因而也就進一步選擇了自由意志主義左派。從自由意志主義右派看來,丟開了絕對界線的權宜策略是相當危險的,時常會陷入困境和危險而不自知。海耶克較為接近傅利曼,也常遭自由意志主義右派的批評。海耶克理解絕對界線的重要,但他不從哲學層次去論證政府不可橫跨的界線,而是以制度的社會演化角度為高一層的判准,並以此保護自己的理論體系不會陷入困境。傅利曼必然知道絕對界線的重要,他也不從哲學層次去論證,而是以人類的發展為高一層的判准。早年,他在《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導論中就說到:「即使行使這種(無限制)權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權力也會吸引人,並塑造出另一種型態的人。」到了晚年,他依舊擔心社會救濟與社會服務計畫會「創造了一種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人類。」
他堅持他的選擇。去世前一年,他還提醒人們「競爭市場並非整個社會的全部……有很多事取決於人口的品質」。
推薦序一
我看傅利曼的一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朱敬一
稍微了解經濟學的讀者都知道,經濟學界有所謂的「芝加哥學派」,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尊重市場機能,與美國的共和黨政綱比較接近。芝加哥學派當然是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重心,其第二圈的勢力範圍是拿到芝大經濟學博士學位,而後在其他地方教書、研究、從政者為主。以各地教授為觀察點,則明尼蘇達大學與羅徹斯特大學大概是芝加哥學派的堅強堡壘。以從政者為觀察點,則智利應該是受芝大經濟思潮影響最大的國家。此外,每年也有為數不少的訪問學者到芝加哥大學遊學,在當地耳濡目染一年半載後,有時也就變成了芝大學派的死忠支持者,算是第三圈的勢力範圍。
但是芝大經濟系教師僅僅卅人左右,即使加上企管學院中的相關經濟教師,也不超過五十人。美國各大學經濟系教師人數超過五十人者滿坑滿谷,傳道授業的機會也比芝大多出甚多,為什麼經濟學界沒聽說過什麼「加州大學派」、「紐約大學派」,卻只有芝大學派聲名如雷貫耳呢?筆者認為,固然芝大經濟學教授的學術根基深厚,內功一流,但這也多少與2006年11月去世的傅利曼教授有關。
我們如果讀一讀傅利曼的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以及《選擇的自由》就會發現,傅氏是極為聰明、極富機智、極能在言詞上抓到重點的人。這樣機敏出眾的思辨與對話能力,在廿世紀經濟學界恐怕是無人出其右,其課堂論述自然對芝大的學生與過客有極大的渲染力。而且,這種語言機敏功力雖然是以英文表達,但即使在中譯本的著作中卻也一展無遺。巧的是,我在另一本中譯作品《世界是平的》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精銳幽默言詞,而作者也恰好名傅利曼,真不知這是巧合還是基因遺傳。
我不曾留學、遊學過芝加哥,未曾到該地給過學術演講,甚至不盡同意芝大學派的若干學術觀點,當然不屬於芝大學派,但是總覺得自己對傅利曼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好感。談理念,他大力鼓吹選擇自由,顯然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我所研習的自由主義與傅氏相差甚多,但總是有萬法歸宗的共同理念。論批判,傅氏堪稱為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勢不假辭色。尼克森總統請他不要責怪為尼氏執行政策的部長舒茲(G.
Schultz),但傅氏卻回答:「我不會責怪他,我怪的是你」。他也曾說「當你站在一個公僕面前時,你有沒有懷疑過究竟誰是主子,誰是僕人?」個人非常崇敬這樣的知識分子高度,也希望自己及所有台灣學術界的朋友,都永遠能秉持相同的理念,對權力不卑不亢,做稱職的知識分子。傅氏又說,「不管是什麼個性的人,要一個人承認他的重大專案計畫有瑕疵,絕對是件最困難的一件事」。這樣的評語,用在動輒提出數百項政見的台灣政治人物,又是何其精確呢!講學問,傅氏治學領域寬宏,從貨幣到消費、從管制到教育、從自由理念到計量經濟,都是他專攻的範圍。像他這樣的社會科學通儒,廿一世紀後已不復見,卻也是許多後生學者景仰的典範。
我自己大概也屬於傅利曼那種口齒機伶之人,雖然學問上差一大截,年輕的時候卻不知天高地厚,莫名其妙得罪了不少人。傅利曼在美國學界樹敵甚多;既把芝加哥弄成一家「學派」,自然與另一家凱因斯學派也就常有文字交鋒了。由國內財信出版的譯作《傅利曼的選擇》一書,將傅氏與凱因斯學派之間的爭辯做了清楚的描述。隨著年齡漸長,自己變得慈眉善目,也漸漸覺得凱因斯似乎未必與傅利曼有那麼大的差別。凱氏身處大恐慌時代,亟思以非常簡單的言論見解呼籲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不得不立論精簡。而傅氏在恐慌過後,再以嚴謹論證批判凱氏論見之疏鬆,自然也有補足之功。與其說是學派歧見,倒不如說是凱、傅二人想要說服的對象不同、時機不同而已。爭到後來,其實是學派的徒子徒孫在爭而已矣。這些小磨擦,對凱氏傅氏等大師而言,卻是一羽難加。
傅利曼教授學問好、辯才好,掀起學界大風潮,看似處處機鋒,卻可在其傳記中看到他的圓融一貫。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傅氏顯然有他獨特的詮釋。
推薦序二
傅利曼的經濟思想的啟示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洪德生
傅利曼是貨幣主義經濟學派的主要提倡者,主張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有著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近年來全球飽受原物料價格高漲的衝擊,不論先進或開發中國家都正面臨龐大的通膨壓力,依據他的看法,影響經濟趨勢的關鍵因素是貨幣數量,而非政府的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源於貨幣供給量擴張,亦即控制通貨膨脹應該是從各國央行對其國內經濟提供的貨幣數量著手。傅利曼曾提出,「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永遠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只要對貨幣供給控制得宜,就不需要太擔心會發生通貨膨脹。
傅利曼所帶領的「芝加哥學派」認為不論在配置社會資源或規範人類事務上,自由市場是最佳策略,傅利曼是自由企業的忠實信徒,強烈反對以金融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手段,並且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嚴格限制。他亦深信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傅利曼從其對於美國貨幣史之研究中對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提出一些相反的論據,促使了一般人對凱因斯理論之價值重新加以評估。他認為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發生並不是由於貨幣政策失靈,而是由於貨幣政策沒有正確適當的運用。因為他發現在1929年至1937年間,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將貨幣供給減少了三分之一,導致了經濟蕭條所經歷的時間延長,受到影響的程度更為嚴重。
傅利曼是在1950年代期間提出負所得稅建議,他的想法是要以一個單一計畫取代政府支助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計畫,其優點是高效率化和簡化。負所得稅的概念廣受學界的支持,但卻未被當時的美國政府接受採行。負所得稅的概念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環,在對中低收入戶的補助方面,負所得稅補助的對象是有工作的貧戶,一方面可以鼓勵工作,另方面又可以確保其所得收入水準。負所得稅可提高中低收入戶的恆常所得,對促進消費的增加是有幫助的。
傅利曼一生職涯裡所倡議的主要公共政策建議有很多,從1960年代迄今,他對經濟政策討論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負所得稅、以薪資物價指數連動法來調控通貨膨脹、針對稅賦和政府支出進行限制、支持政府預算赤字以遏止政府擴張、以及降低高邊際所得稅率等概念。另外,他在海外倡議國有產業民營化亦成效卓著。
從1962年「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開始,他開始積極倡議減少政府干預與更自由且更開放的競爭市場,他認為這些作法可以讓社會變得更有秩序。從1960年代開始他為「全國評論」、「新聞週刊」撰寫專欄文章,發表他的觀點。
傅利曼於1963年出版「1867年-1960年的美國貨幣史」一書後,他漸漸轉移方向,轉而希望能直接透過政府領袖來影響公眾意見,而不是間接透過學術管道。在1960、70年代期間,隨著通貨膨脹上升,傅利曼認為在因應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時,部分抵銷可能比完全消弭它更可行。原則上,他主張所有合約和其他付款協議都應該予以物價指數連動化,以因應通貨膨脹。同樣地,所得稅級距也應將通貨膨脹列入考慮。實際上我國也有採行兩種相同的作法,讓物價指數與之連動。不過近一兩年來在政府公共工程採購上,遇有物價指數無法反映實際原材料價格上漲的現象,導致公共工程延宕,顯然政府在執行上確有值得改進之處。
傅利曼支持聯邦政府預算赤字,讓赤字達到能夠限制政府支出的程度。他認為寧願政府因赤字高漲而減少支出,而不希望政府因預算平衡而增加支出。如果為了讓赤字降低而提高稅賦,結果很可能導致高政府支出成為常態。台灣政府多年來處於赤字現象,不過95和96年度的政府財政赤字已大幅縮小。然而,97年度歲出預算較96年度增加2.88%。政府若為了擴大內需而增加政府支出,並無可厚非,但對政府赤字水準必須控制得宜。
2000年年底,美國經濟歷經繁榮期崩潰後,經濟卻僅陷入溫和的衰退,貨幣政策是其中的一大重要功臣。對照日本而言,傅利曼在1999年曾經表示,1992年以來,日本反覆採行許多財政刺激政策,但同時卻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六年多來平均貨幣供給成長率為2.8%,結果,這期間日本的景氣並未改變。這顯示出影響經濟方向的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多年來,各國在遭逢經濟不景氣時,就採取擴大公共投資的財政政策,或許對刺激短期景氣有所幫助,但若要促進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實有必要在貨幣政策上多下一些功夫。
近幾年來傅利曼主要聚焦在學校教育券議題的研究,他所關注的是要追求一個自由社會的哲學。傅利曼認為公立學校不但沒有效率,也缺乏創新。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下,自由權與自由才會蓬勃發展。他認為學校教育券制度將會促進一股教育復興,尤其是對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學生。學生將因多元、選擇和競爭,而體驗到更多的機會。所有學校的績效也會跟著改善。台灣多年來實施教改,也實施多元教學,然而實施成效不彰,也帶來學生、家長及教師的反彈。教育券制度的理念正好可適切地作為當前教改方向的參考。
傅利曼除了貨幣理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之外,他在公共政策領域上也善盡了知識分子的職責。以上對台灣的啟示只不過是列舉了一些例子,咸信傅利曼的經濟思維,尤其是對政府角色的理念,仍然還有許多值得挖掘的寶藏。
本書作者將傅利曼生平的學術創作過程,不論是描述他的個性表現,或是彰顯他的學術成就與貢獻,都能以深入淺出的筆法,闡述地淋漓盡致,的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傅利曼多半都擁有看透未來的過人眼光。
推薦序三
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許振明
這是一本好書,它描述米爾頓.傅利曼一生的行誼。從早年歲月一直至晚年。我們對於其個人行徑及價值觀深深感佩。就本書所描繪的情景,吾人深深瞭解做為一代思想家,其所受之煎熬,是不可等閒視之,無以倫比!
本人曾造訪芝加哥大學兩次,一次為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為國科會訪問學者,訪問經濟學系。第二次訪問管理學院,係一九九一年。在管理學院,我仍親臨經濟學系,參加各種研討會。對於傅利曼所珍留的遺產,都能一一品味。
芝加哥大學之創建,係因白種人之歧視而設立的。當年為規避白人對猶太人歧視,猶太人在芝加哥設立大學,協助猶太人就讀,以因應其被排除進入美國東岸之常春藤盟校就讀機會之不利影響。基本上,芝加哥大學是猶太人在美國之主要立足之大學。此點值得吾人學習。
傅利曼身為猶太人,進入芝加哥大學就學及在該校服務三十餘年應不足為奇。應該引以為傲的是,傅利曼身為猶太人,而能於異國奮發圖強,充分發揮其才智,造福人群,才是吾人所應效法對象。
本書對於傅利曼一生行誼描述可謂言簡意賅,為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本人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從事教學研究,主要課題為總體經濟理論與貨幣銀行學,對於傅利曼的學說有深深的感觸。
猶記大學求學時期,本人受老師啟發,對於傅利曼之思想學說,甚為崇拜。然而彼時,凱因斯學派學說風行,許多著作之評論,多偏向不利傅利曼之論點。然而,真金不怕火煉,傅利曼之論點終究如石破天開,廣為人們接受。
傅利曼之諸多創見頗值得吾輩學習。尤其是其為學之方法論,更是吾輩所應注意學習者。在本書中,作者就指出當代經濟學之分析方法論主流原來在戰後初期(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0年代)尚區分成兩群:一以考爾斯委員會為主導力量,另一以傅利曼為代表之分析方法論。考爾斯委員會成立之初係位於芝加哥大學,後來於一九五三年搬至耶魯大學。其強調以嚴格的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及發展經濟理論。換言之,考爾斯委員會偏好以數學公式來表現經濟理論。
傅利曼較側重以統計方式表達經濟資料的意義,並主張經濟理論的攸關性應取決於對各項經濟事件的預測的經驗確證。這就是傅利曼最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
猶記得我們於一九七0年代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唸書時,無論是用個體經濟理論或總體經濟理論,傅利曼之〈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是必讀文章。而在課堂中,老師所引用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僅止於以幾何圖形及微積分為主要的數學工具。計量經濟學及數理經濟學僅為輔助的學科。
然而,隨著時間經過,以數理方式表示的經濟分析方法逐漸取得優勢。尤其在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後,在芝加哥大學教授亦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魯卡斯教授的大力鼓吹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