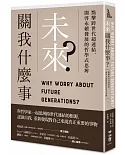WOW!
想一想「WOW」這個美到不能再美的字。思考一下在舌頭上形成這個對稱完美的字時的那種快感。想像一下這個字表達出來的那種特別的熱情:驚嘆感、驚訝感和絕對的參與感。「WOW」是我們必須去博得的,在現代,我們所給的起立鼓掌太過頻繁了,而我們這麼做只是為了客氣,可是我們又變得太冷漠了,吝於叫聲「WOW」。這個字有著那麼點諷刺的意義,就好像只有加上引號才能說出來似的。我們的表現或許不會像「綜藝半月刊雜誌」裡某個藝評人那麼冷漠,他對於一對連體雙胞胎在十分鐘的歌舞雜耍秀裡,表演了模仿秀、唱歌、跳交際舞和踢踏舞還玩雜耍,他的評論就只是「就這類表演來說還算不賴」,而這句話卻遠遠不及一聲「WOW」給人的感受。
張藝謀二○○四年執導的「十面埋伏」,影片開始不久有一段值得叫「WOW」的連續鏡頭:有個瞎妓被帶到地方捕頭前面,捕頭懷疑瞎妓是秘密幫派「飛刀幫」份子,而不是妓院的歌伎,於是命令來場表演,捕頭說有一種「聽音辨位的遊戲」,就要瞎妓來賽一場,瞎妓被帶到房間的中央,四周排著柱子,柱子上掛了鼓,人群就聚在樓座上觀看,捕頭擲出一顆豆子,擊中一面鼓,瞎妓就把一對長袖啪的一聲打了一下,往同一面鼓擊過去,這時,一團樂師對於瞎妓在感知上拿捏精準的表現,表達出興奮之情,捕頭然後擲出第二顆豆子,這顆豆子在好幾面鼓上彈來彈去,最後落在地板上,瞎妓於是又把一對長袖甩出,擊中第一面鼓,然後擊中第二面鼓,接下來就飛躍、旋轉,頗為壯觀,最後捕頭把整碗豆子擲出去,像雨點般灑在那些鼓上,瞎妓這時豎起耳朵聽著,等了一個拍子,然後開始一場精心編排的舞蹈,一面鼓一面鼓地敲,想要找出這些鼓的軌跡,然後把一對長袖再次甩出,把放在桌上的一把劍裹住,於是就拿起劍來威脅捕頭,做出威脅姿態之後,就帶出一連串扣人心弦的武術鏡頭。
這個場景從頭到尾讓我們看了,卻不能完全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快感是由這段鏡頭非比尋常的特性所引起的,像是走鋼絲特技、慢動作的攝影以及特效。這種表演就在我們眼前即興演出,我們看了印象深刻,這點很容易可以理解。比較難理解的是,處在這個我們知道每個元素都可能是捏造的時代裡,這種表演為什麼還能讓我們感到驚嘆,但是這段連續鏡頭在銀幕上處理得實在壯觀,讓人不禁讚嘆。這段鏡頭有它自己的軌跡,每一個姿態都是以前面的姿態做為基礎,每一個動作的精彩程度都要比之前的動作略勝一籌。這個場景在建構上是戲裡有觀眾,也就是排列在樓座上的人群,這些人唉呀和啊呀的聲音,就替代了我們看得瞠目結舌的反應。張藝謀可能犯了一個美學上的錯誤,因為他把這段鏡頭擺在影片這麼前面的地方,於是在隨後的場景裡,就得努力去超越,這是場期待的戰爭,但張藝謀沒能完全打贏這場仗。
這個場景可以從影片取出,做為一個獨立的片斷來欣賞,而且仍會產生幾乎同樣的快感。這段連續鏡頭是張藝謀用來為隨後一切要發生的事預做準備的。片子進行後來時,又回到那個「聽音辨位的遊戲」,而這次是捕頭自己被蒙住雙眼,被迫試著去重演瞎妓的神技。我們最後發現女主角的眼盲是裝的;捕頭和女主角都是正式的扈從,那場表演是種做愛的方式,而且兩人儘管都渴望依偎在對方的懷裡,被迫裝出互不認識。影片裡的敘事讓我們對於女主角的神技添加了一層又一層的賞識之心。功夫片的傳統就是玩弄人物的身分,而張藝謀則是進一步地擴展了這個傳統,直到沒有一個人物和他們的表象是一樣的,而且這些人物的情感在先前都是裝出來的,到後來才發現自己對於這種情感實際上是有感受的。所以這一切都往悲觀的結局發展,因為效忠的對象各有不同,結果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殉難了。這一切都說明這個場景在這部電影的敘事結構裡外,都能發揮效果。
《WOW效應》這本書裡的文章所談的,就是讓我叫「WOW」的事情。我這個人看電影的時候,會哭得不成人樣,尤其是在飛機上看爛電影的時候。我這個人會大聲笑出來,即使是笑話讓人不愉快也會如此,而且笑話讓人不愉快時尤其如此。我這個人看到表演雜耍的做出後空翻,或者看到有人表演吃火時,就會邊喘氣邊鼓掌。小時候在當地的遊樂場裡,家母曾讓我進到表演雜耍的帳篷裡,一小時之後,家母由經理陪著進到帳篷,因為她相信我被人綁架了,結果卻發現我坐在那兒,眼睛睜得好大,在觀看一名男子把一根釘子放在鼻子裡往上敲。總之,我這個人酷愛通俗的流行文化。
多半的流行文化是由增強情緒這種邏輯型塑出來的。流行文化所關心的,與其說是要我們思考,不如說是要我們去感受。不過這種差別又太過簡單了,當流行文化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時候,因為讓我們有感受,所以也會讓我們去思考。在前面提到的「十面埋伏」的那個場景裡,我們對這點就有瞭解,因為之前只是一個精彩的片斷,結果卻成為瞭解全片的關鍵所在。流行文化只要去遵循用過無數次的公式,就能大量引發出很容易就會出現的情緒;但要讓我們叫「WOW」,就必須去扭轉或去改造這些公式,讓公式變得絕妙而出人意表。最近出版的幾本書尤其是姜生的《凡是壞的對你都是好的》,就提出理由說明當代流行文化的複雜性,以及流行文化加在消費者身上的要求。我對這本書的頭一個反應,就是接受書裡的論點,因為我長期來的興趣就是協助大眾更能領略流行文化的複雜性和多元性,而這本書的論點和我本身這種興趣是一致的。不過,我第二個反應是對於這算是新鮮的論點,我要提出挑戰。在流行文化的歷史裡,自始至終都擁有複雜性和多元性,只不過多半的知識份子不具備那種知識和能力,所以不能用真正的欣賞態度去消費流行文化。我們對於流行文化的反應唯一會出現真正腦死的時候,就是流行文化變得太過於公式化,以至於不再能夠引起情緒的反應,在這個時刻,流行文化就是在它自己設定的條件下失敗了,而且就我們加在它身上的任何其他條件來看,它也失敗了。不管別人怎麼跟你說「看了一件作品就是看了所有的作品」,反正情形絕非如此。不過下面的情形就幾乎是絕對沒錯了:要能徹底去欣賞一件流行藝術品,就得把其他的例子看個夠,以便觀察這件作品是如何的以現存的公式做為基礎,又是如何的與現存的公式一刀兩斷。第一流的流行藝術家有能力運用那些公式,並且能從中探尋最大的自由空間,拿閱聽人來冒險,並且對素材做實驗,以便尋找那更難得的「WOW」。
這些年來,我的文章已經發展出本身的一套公式:我在文章開始時,幾乎總是會描述某種元素,因為這種元素能夠體現文章主題裡最煽色腥的層面,然後我就對於出現那個「WOW」的時刻加以解釋,以便做為我進行文化面分析的出發點。對於這些會造成「WOW」的時刻,我們通常的反應方式,就好像這種時刻是無法做出任何解釋的,就好像這種時刻是純粹發自內心的層面對我們說話。不過這種「WOW」的時刻或許是進行文化面分析的絕佳良機。我首先假設這是流行文化所引起的情緒,從來不是針對個人的;相反的,文本如果要通俗流行化,就必須把大眾廣泛所共有的感受喚起。凡是碰觸到文化裡關鍵性的衝突、焦慮、幻想和恐懼時,這種時刻通常就是情緒最強的時刻。
本書的書名源自於歌舞雜耍表演秀裡的一個老詞。在表演當中,最壯觀、能對情緒造成最大衝擊的時刻,一般的形容就是「WOW的高潮」、「WOW的結尾」、或者就是簡簡單單的「WOW」。劇評人里昂一九二五年為「星期六晚郵」寫文章時,歌舞雜耍表演秀的巡迴演出已逐漸要壽終正寢了,里昂寫道,「表演在結尾的時候額外帶來一個快感,這是一件困難的小事情,但每個歌舞雜耍表演團都試著要去捕捉,這當中的原因完全可以瞭解,能掌握到結尾的快感,通常就能保證巡迴表演之路會走得長遠,而且帶來的利潤也讓人眉開眼笑。能或不能讓觀眾鼓掌,就要看表演怎麼樣結尾了。鼓掌的質和量透露出觀眾從表演裡得到快感的程度。表演凡是能為最多不同的觀眾帶來最大的快感,這種演出就會最穩定,而且會持續得最久。」
歌舞雜耍表演和說故事沒關,表演是上演一場秀,而且不只如此,歌舞雜耍表演是有關每一位演出者個別的努力,希望自己的演出能讓熱烈的掌聲給打斷,因而大出風頭。歌舞雜耍表演不喜歡戲劇裡寫實主義的排場,歌舞雜耍表演是有關壯觀的、奇異的、新穎的,不喜歡連續性、連貫性、或統一性,而喜歡片斷、改變和異質性。雜耍節目的基本邏輯是有一種假設做為基礎的,而這種假設就是,如果要吸引並且滿足廣大的觀眾,異質性的娛樂就屬必要。雜耍表演的節目是從各個不同素材的模組單位建構出來的,每個單位的長度不超過二十分鐘,把這些單位並列呈現後,希望能帶來最大的多樣性和新鮮感。
演出者的責任是,把自己的表演內容創作出來,與製作專家商討素材和道具,排練以便改善表演技巧,以及運送並且維修舞台佈景。這種以演出者為中心的製作模式,造成的結果就是強烈聚焦在演出技巧上的那種美學。一般期待演出者在表演自己的特殊才能時,能夠一以貫之地維持著高水準的速度和精準度。在設計表演內容時,經常是聚焦在演出者的技巧上,至於其他方面就意興闌珊,或者興趣缺缺了。這些技巧的衡量角度就是觀眾顯現的情緒反應,因此歌舞雜耍表演不喜歡細微的差別,所有事情都設計成保證能引起大大的轟動。在老的制度裡,地方上的劇場經理在每一場表演接近尾聲時,就會把頭伸進觀眾區,用耳朵聽聽觀眾的反應情形。經理所做的筆記就會決定演出者能不能續約。因此演出者的生計就要看自己有沒有辦法透過表演來型塑、控制觀眾的情緒軌道,以期在真正重要的時刻達到最高點。
歌舞雜耍表演的演出者發展出自己那一套民間的情感理論,這點並不令人詫異。里昂又寫道:「美國的觀眾生來就含蓄,至少習慣是如此。這種現象就類似在河流築壩攔水的作用,演出者如果能打開水門,或者打開溢洪道,掌聲就會和潮水一樣競奔而出,而這奔出來的水流,我們希望是強勁而緊湊的。如果是因為缺乏合適的高潮,或者因為不具有夠水準的演藝才能,不能讓圈禁起來的熱情有一個發洩的途徑,就會涓涓地慢慢流過水壩的頂端,或者在淤水的緩流裡微弱地打轉。」里昂的文字華麗,甚至有點情色,他所談的是演出者和觀眾之間浮現出來的關係。畢竟里昂所談論的那種高潮,會讓觀眾的情緒失控,甚至對身體的機能也要失去控制。歌舞雜耍表演的演出者希望我們笑到淌下眼淚、笑到臉紅、笑到尿濕了褲子、發狂也似的搖來晃去、或者一掌拍到旁邊觀眾的背上。造成這種基本的情緒上的衝擊,就是歌舞雜耍表演的整個藝術在建構時的中心。
里昂認為歌舞雜耍表演是一種通俗藝術的形式,本身有著一套完全成形的美學原則,雖然有時候歌舞雜耍表演的美學原則是不明言的。我所寫的第一本書是《開心果是用什麼做的?早期有聲喜劇和歌舞雜耍表演的美學》。在這本書裡,我設法要指認出歌舞雜耍表演傳統的特徵,以便瞭解下面這個過程:好萊塢吸收了一個世代的雜耍藝人,然後創造出一些方法來剝削這些藝人的表演技巧,最後把這些藝人再拉回到支配著美國電影製作慣例的傳統規範裡。我所關注的是以下幾件事:以景象和以故事性為基礎的美學,以及兩者之間所出現的緊張狀態;發展能把屋頂衝掉的高潮的美學,發展解決敘事裡的困惑點的美學,以及兩者之間所出現的緊張狀態;還有就是用表演技巧的角度,用人物性格描述的角度來解讀表現的美學,以及兩者之間所出現的緊張狀態。我的目標是要形成一種新的評論字彙,好讓我們透過這些字彙來鑑賞這些早期的有聲喜劇所獲致的成就。我們評價這些早期有聲喜劇的標準,不必是那種為了其他的文化形式而發展出來的標準。
當然,也不是只有里昂才能看出型塑了流行文化的情緒動力。艾森士坦在〈吸引力的蒙太其〉一文裡就概述了正統的戲劇和電影界,或許可以學學馬戲團讓觀眾感到興奮的那種機制。艾森士坦選擇了一個與露天遊樂場有密切關係的詞語,而把吸引力定義成「在劇場裡所出現的任何一種有攻擊性的時刻,也就是這種時刻能讓觀眾在情緒或心理上受到影響的任何一種元素,而這種對情緒或心理上產生影響的現象,是透過經驗而獲得證實的,而且是精確、精心設計出來,以便在觀眾體內製造出特定的情緒震撼,而這種震撼就整體而言是有條不紊的」。艾森士坦和里昂一樣,接下來又列出能夠造成「震撼」及「驚嘆」的方法。對於艾森士坦來說,有關「吸引力」的最鮮明的例子,可以在巴黎一處以演出恐怖和刺激性的戲劇而馳名的「大木偶劇場」裡發現,「在舞台上,眼睛被挖出來,手和腳被肢解」。艾森士坦不單單要我們笑,他還要我們坐立不安。艾森士坦把「激情活生生地演出來」看成是一種起始點,也就是他想達成的那種在意識型態上發生轉變的起始點。艾森士坦把「花招」和「吸引力」做了區分,「花招」的設計是要展現演出者的成就,而且通常是有自制力的,而「吸引力」的設計則是要煽動,而且完全從觀眾反應的角度來衡量。與艾森士坦同一時期的庫賴雪夫則對他所謂的「怪物」特別著迷,而他所謂的「怪物」是能夠對自己的身體發揮驚人控制力的演出者。
這些蘇俄電影理論家對於情緒的結構感到著迷,這種現象要透過下面這個背景才能瞭解個中的原委:這就是在更廣泛的面向上,蘇俄形式主義者對於通俗戲劇在情感方面的入迷現象。例如戲劇評論人布魯海提就詳盡闡述過「通俗劇的詩學」。戲劇歷史學者吉勞德指出,布魯海提這篇大作是從下面這個前題做為起筆:「通俗劇裡的所有元素(它的主題、技術原則、結構和風格)都隸屬於一個高高在上的美學目標,這就是設法引起『純粹的』、『鮮明的』情緒。而情節、人物、對白則協同一致地發揮作用,讓觀眾感受的強烈程度達到最大。」布魯海提主張,通俗劇所憑藉的,就是「簡單明瞭的情緒基礎」、精簡的人物、一連串讓人震驚的命運轉折、簡易而且是可以看得到的衝突,以及運氣突如其來的改變,以上這一切的設計都是為了要引起「直接的印象」。布魯海提認為,通俗劇裡的行為是不是合理,並不是靠意識型態或者敘事的邏輯來斷定,靠的是場景在設計上所要表達出來的那種情緒力量。
博德威把艾森士坦對於吸引力的興趣加以延伸之後,討論到當代的香港動作片。這類影片也採取類似的手法,把片子圍繞在表達式的表演和情感的強化:「流行藝術為了要吸引廣大的觀眾,就要對憤怒、厭惡、害怕、快樂、悲痛和憤慨之類的情緒做處理……電影尤其擅長用動態的方式,透過動作和音樂把情緒激起。李小龍要求學生在武術裡要有「情緒的內涵」,比如有意識地運用憤怒。如果動作虎虎生風,有精確的招式,再搭配判斷良好的架構,活潑有力的剪輯,和充滿震撼力的音樂,在這些條件下捕捉到李小龍所說的那種情緒特質,你會發現自己將隨著打鬥的節奏而緊繃和抽搐了。」博德威歌頌香港電影「千變萬化」、「把表現增強了」,而且能造成感官的快感。這種說法聽起來類似里昂、艾森士坦、布魯海提、以及與這三位同時期的人的看法。
艾森士坦有關「吸引力」的觀念,在應用方面最著名的例子當推肯寧在一九八六年的文章〈吸引人的電影〉,這篇文章具有影響力,勉強稱得上是一種宣言,也就是用新的方法探討早期電影的宣言。對於一九○六年以前製作的電影,肯寧並不認為這些電影是一連串的墊腳石,藉以邁向用更正統的手法建構敘事(這種觀點長期來都形塑了有關那個時期的史學研究方法)。肯寧堅稱,對於早期的電影,要用不同的美學邏輯來解讀:「吸引人的電影是直接就能引發觀眾的注意,而能激起視覺上的好奇心,並且透過刺激的景象給人快感,這種景象就是一個獨特的事件,也不管這是虛構的事件,還是有文獻紀錄的事件,只要事件的本身讓人覺得有趣……這類電影的能量被公認是向外移動到觀眾那裡,而不是向內移動到以角色為中心的情況裡,而這對於傳統敘事是絕對必要的。」這種聚焦在景象和表演技巧的論點,與歌舞雜耍的「WOW」邏輯是一致的,而且也與蘇俄理論家認為型塑舞台通俗劇的情緒結構是一致的。肯寧把「吸引人的電影」與歌舞雜耍表演的舞台聯在一起,而且不只如此,聯在一起的,還有二十世紀初的流行文化走向煽色腥和刺激作風的更為廣泛的趨勢。肯寧以上的描述影響極廣,其他想要思索景象在流行文化裡佔了什麼地位的人,都受到他的影響,這些人隨後的作品也向外擴散到其他主題,包括喜劇電影、音樂劇、動畫、色情文學等。
佛里曼最近出版的《在電玩遊戲裡製造情緒》這本書裡所指認出的一些技術,里昂要是看到的話,也應該會辨認出來的,像是訴求於科學專業技術(佛里曼是在談到「製造情緒」這個公認屬實的原則時,讓這種訴求不言而喻)。佛里曼接著在書裡指認了三十二類製造情緒的技術,可以讓電玩設計師用來增強玩家在玩遊戲時的體驗。佛里曼這麼解釋,「把情緒加到電玩遊戲裡,就會吸引更廣泛的人口,新聞界在報導時就比較會捧場,玩家的口碑也會比較好,而且還更可能製造品牌忠誠度。遊戲研發小組對於研發案子的熱情也會增加。這一切現象就會轉化成利潤的提升,以及對於電玩的體驗更為豐富。」畢竟,這類的電玩遊戲就和電影一樣,在開始時是以放在街頭吸引人的姿態出現,因此,為了要讓玩家不斷把兩毛五分硬幣投入機器裡,就需要讓玩家感到興奮,而這也就成為這類電玩最主要的美學原則了。在電玩搬到家裡之後,就有了「抽搐」娛樂的名號,這個用語指的是,玩家需要不斷敲著按鈕,好讓畫面的動作運轉不停,但同時這也暗示了電玩讓玩家產生亢奮的情形。
我們或許不太願意看到可敬至極的路易斯,竟然也一起在提倡流行文化裡的煽色腥現象。不過路易斯在〈有關故事〉這篇文章裡,對於型塑了我們與文學的文本相遇時那種情緒的體驗,他似乎特別有興趣將當中的特質標示出來。路易斯一方面對於把精彩故事裡的細節簡化成隱喻或諷喻的傾向不表同意;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傾向路易斯也不同意,那就是把閱讀流行小說的現象,簡化成某種可以概括化的對於「興奮」的追求。相反的,路易斯要我們把這些細節當成是建構豐美的想像世界裡的一部分,其中每一個想像的世界都會產生出自己獨特的方式,讓情緒可以發洩:「不同種類的危險會在想像裡觸動不同的心弦……有一種害怕是敬畏的孿生姐妹,例如戰時,一個人第一次身處在槍聲範圍之內的那種感受;而有一種害怕是厭惡的孿生姐妹,例如一個人在臥室裡發現到蛇或蝎子時的那種感受;另外還有緊張、顫抖的害怕,在一剎那間,這種害怕簡直與感覺愉悅的刺激無法區別,比如騎在一匹危險的馬上,或是處在危險的海上,或許就會感受到這種害怕。其次,還有我們以為自己罹患了癌症或霍亂時,那種麻木、啞口無言、沮喪和失去感覺的害怕。另外也有一種害怕與害怕危險完全無關,例如害怕某種無害但碩大而醜陋的昆蟲,或者對鬼感到害怕。所有這一切的害怕,在現實生活裡是相等的。但在想像裡,害怕對於可鄙的恐懼是不會有反應的,也不會發洩成行動,這在質方面的差別就要大得多。」路易斯建議,故事要說得精彩,就需要深入去瞭解細節以及細節所具有的情緒力量這兩者之間的關聯,另外也需要說故事的人透過每一個字來型塑讀者在情感上的體驗。
不同的媒介所採用的技巧各自不同。不過,歌舞雜耍表演裡的演出者、早期電影的演藝人員、摔角選手、動作片或恐怖片的導演,以及電玩遊戲設計師等等,都設法把各自的媒介所提供的每一種手法拿來使用,以便讓閱聽人呈現出最大程度的情緒反應。這些通俗藝術家和演出人要是會想到自己的技術,同時也就會想到如何去達成情緒上的衝擊。
《WOW效應》這本書是把過去十五年來所寫的一系列文章加以重新組織而成,這些文章跨越了不同的媒介(電影、電視、文學、電玩、漫畫)、不同的類型(打鬧式喜劇、通俗劇、恐怖劇、兒童小說、剝削型電影)、以及不同的情緒反應(震驚、笑、多愁善感)。不過我在回過頭讀過早先那些文章時,發現到我之前在檢視情感和美學之間的關係時,在寫作上的呈現竟是如此前後一致。例如,這些文章談到了做為「靈犬萊西」這個跨媒介作品核心的多愁善感現象;檢視了像是克雷凡和柯能堡之類的恐怖片導演,以及前衛藝術家巴尼等人,是如何在許多相同的主題和圖像的基礎上,創造出基本上是不同種類的情緒體驗;另外還探討把職業摔角看成是一種男性通俗劇形式時,這當中的意義何在。我所使用的方法,能讓我盡可以具體去討論在特定形式的流行文化裡,對觀眾的吸引力和文化的含義。不過這當中的每一篇文章,同時也對於一個範圍更廣泛的理論研究計畫做出了貢獻,那就是我設法要對流行藝術的情緒動態做一番瞭解。
我們要如何去研究通俗流行藝術的「WOW」現象?在所有促成強烈情緒體驗的通俗媒介中,我們需要從多重的角度來檢視通俗文本。例如,在研究通俗劇時,注意力要集中在敘事和性格描述這兩個層面運作上的情緒元素。而在研究電玩、體育或武術時,則要探討能不能百分之百整合到故事裡的動力元素。至於研究喜劇時,在對笑話感到莫大興趣的同時,凡是能透露出喜劇演出者獨特個性的姿態,我們也極感興趣。博德威在寫到有關香港的功夫片時,就要我們去檢視這些片子裡「每一刻的神韻」,因為影片裡每一個時刻在設計上都是增加我們在體驗上的直接性。
不過,由於這種美學是如此聚焦在觀眾的反應上,因此我們如果純粹從形式主義的角度來看的話,對這種美學就永遠沒法瞭解。其他人曾經設法透過心理分析的角度、或者認知科學的角度來瞭解情感,而我所偏愛的方法,則是利用文化分析的工具,也就是去了解這些作品在製作和消耗當中的情境,去呈現出在某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裡,對流行藝術極為重要的意義和感受,去探討文化層級是如何的尊敬或排斥流行藝術的情感層面,或者去探討檢查規範是如何的反映出在不同的文化裡,以不同的方式運作的「恥辱的限度」。
如果要站得遠遠的來沉思,對於這些層面的流行文化就很難能夠有所瞭解。要了解流行文化是如何對我們的情緒造成影響,我們就必須把流行文化拉到近距離的地方,跟它親密地相處在一起,讓流行文化發揮魔力,對我們產生作用,然後寫下我們本身的參與情形。我心目中流行文化方面的頂尖作家,包括李普席茲、布凱曼、戴爾、達帝、史派哥、伍茲、哈特利,幾乎每一位似乎都曾參與過與這種類似的研究計畫,,這些作家把自己對於通俗文本的主觀反應捕捉下來,做為一種切入點來瞭解範圍更廣泛的文化過程和美學問題。不幸的是,不同形式的文本客體化已經嵌進我們在研究流行文化時所憑藉的理論傳統和美學範疇裡了。有好多事擋在學者與作品之間,甚至還有更多的事擋在教授與消費流行文化的大眾之間。通常而言,這些擋在那兒的障礙,與其說是實際存在那兒,不如說是想像出來的。不過這些障礙讓我們的寫作變了形,因此就越發不容易在文章裡提出某些問題,或者提出特定的見解。本書各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一種繼續進行中的探索,而所探索的是一種新的評論語言,以便表達出流行藝術讓我們興起的感受。
在有些例子裡,這些文章有著自傳的體式:例如漫畫書裡的超級英雄曾經協助我哀悼家母的過世,我對此所做的深思;我在小時養過狗,我對那隻狗狗的回憶;以及我兒子和我在長大過程中,各自擁有不同種類的遊戲空間,我對此所做的思索。在有些例子裡,這些文章是民族誌的性質,例如我檢視了幼稚園孩童把「皮威電視劇場」當成一種工具,透過它就可以探查對於自己犯錯時,心理那種既有快感又覺得羞愧的不相容感受。在有些例子裡,這些文章所憑藉的是仔細的解讀,例如我思索了有關萊西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影集,透過童年和寵物的情感結構而表演出來的文化作品。這些文章也憑藉了正式的分析,例如我嘗試去找出型塑了當代電玩設計的美學原則。這些文章還憑藉了論證的分析,例如我探討了圍繞著墨西哥裔女星露凡麗演藝生涯的醜聞。每篇文章是用稍微不同的角度來討論文章的題目,不過彙集成書之後,這些文章就呈現出一系列的核心問題,可供我們了解在流行藝術裡情感和美學之間的相互影響。
請注意我在這裡使用了「流行藝術」這個有些過時的詞語,而不是比較當前比較常見的「流行文化」。流行藝術所強調的,是型塑了商業娛樂在製作方面的美學邏輯和情感邏輯;而流行文化出現以來所要表達的,則是把這些商業文本併入到消費者的日常生活裡。我們在設法瞭解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裡,娛樂對於生活的重要性時,這兩種概念就都值得我們去利用。討論流行文化始終都是極有價值去做的事,因為這能幫助我們思考製作與消費之間的關係。對於純粹為娛樂目的而製作的作品,即使在流行藝術家裡面,也有人傾向於拒絕承認這種作品可以稱之為具有藝術地位。例如,我近來有好幾次發現自己與傑出的電玩遊戲設計師在唇槍舌劍,因為這批設計師相信自己的作品是根據商業的動力而製造出來,因此不能以藝術來看待。這種排斥流行藝術的態度,影響所及,就出現以下這種現象:巴尼借用了恐怖電影而創造出自己的作品,藝評人對這點持歌頌的態度;然而,藝評人對於柯能堡和巴克這類導演的藝術抱負,卻沒能嚴肅以待,而巴尼的靈感就是緣自這些導演的。這種現象你也看過了,法官裁決電玩遊戲不受憲法保護,原因是電玩遊戲不能視為是有意義的表達形式。有能力討論美的價值,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就有很大的份量。至於挑戰,則是找出可以在流行娛樂本身的條件下去談論流行娛樂的方法;另外的挑戰則是,我們要尊敬媒介製作人和消費者所具有的鑑賞力,而不強加那些構成藝術價值的等級標準。
本書副標題的那句話:「流行文化如何抓得住你」,我在書裡從頭到尾都有提到,而隱含在這句話裡的意義,就是我對前輩作家致上的重視之意,像是里昂、艾森士坦、塞爾德斯、華修等等。這些作家對於他們眼裡的新興的流行藝術形式,做了滿腔熱情的論述。對於這些作家提出的核心概念,我把其中的若干拿來做為本書的框架,我這麼做,是要去恢復流行藝術的範疇,同時也清楚我們的目標是從社會、文化、意識型態、或經濟的角度來瞭解這些作品,而美學的鑑賞與這個目標是相配的,而不是對立的。在研究流行文化時最重要的關切點就是性別、世代、階級和性徵;對於這些,本書當然也極感關切,不過這些文章通常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處理有關的辯論。這些文章顯示出,如果要找出並且瞭解社會的「核心課題」,就有效的方法就是檢視以下幾種現象:用感傷的手法把狗狗建構出來的現象,女性主義對於剝削型電影的抑揚,或者傳統男性文化裡面通俗劇式的層面。
本書第一篇〈活潑的藝術〉,是從思考高級藝術與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做為出發點。第一章是讓塞爾德斯有關活潑的藝術這種概念復活,以便探討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把電腦遊戲和電玩遊戲看成是藝術。第二章則是把這種極性的現象顛倒過來,以便說明當代前衛藝術家巴尼,對於自己能向不同的流行藝術家有所採擷,應該心存感激。
第二篇〈直接的經驗〉則把焦點轉移到在玩弄強烈的情緒和具有爭議性的內容時,流行文化所使出的手法。這篇裡的幾篇文章討論了性、暴力和心理創傷。這些文章實質上是在問:誰被容許在什麼情況下表達什麼情緒。
最後一篇的篇名是〈歡迎光臨遊樂場〉。裡面的幾篇文章,把兒童的文化解讀成是夾在兒童的欲望和成人的期待之間。裡面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我們思考以下幾件事:與兒童的遊戲有關的意義;成人是怎樣型塑了兒童的幻想生活,以便塑造兒童正在成形的思維;以及一個是兒童日常經驗下的現實,一個是流行文化提供給兒童的那個世界,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所在。
就讓好戲上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