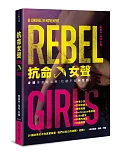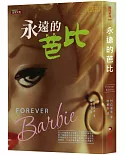開啟雙重衣櫃的門∕王蘋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於將人擺放於定點,你是什麼,你叫什麼?似乎這是永遠不變的。我們輕忽了過程,看不見人其實會改變,人不是固定、單向的存在,人是有無窮可能性的。
婦女運動的發展讓社會不再能父權獨大;同志運動的發展撼動了異性戀霸權;跨性別運動的發展挑戰了二元的刻板性別專制。然而,什麼認同被漏掉了,什麼主體不在其中?
兩本重要的雙性戀論述同時問市,《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異∕同之外:雙性戀》為我們開啟了新的視窗。
這兩本書讓我們看見雙性戀的真實存在,它並不是個新生事物,只是從未有機會清楚的自我表白,同志運動中亦未有清楚身影。但當一個一個雙性戀者坦然表露自己、驕傲現身時,如石破天驚般,讓大家不得不張大眼,聽個仔細、看個明白。
雙性戀不是隱藏起來的同性戀,也不是隱藏起來的異性戀,雙性戀就是一種性的表達方式,包含了異性戀和同性戀行為。雙性戀是忠於自己的本性,面對自我的慾望模式。然而在沒有雙性戀論述的時空條件下,雙性戀的身份認同和慾望很難被社會主流和經過運動洗禮的同性戀社群接受。
多數的雙性戀者,必須偷偷地隱藏自己的性實踐,在同志圈中避談自己的異性戀情,在異性戀圈子裡,更是隱藏自己的同性傾向。隱藏是為了自保,而真正的自我,就成為深藏的祕密,只有自己知曉。孤立的個人,躲在雙面衣櫃之內,生命的內涵只是不斷的欺騙。直到遇見同類的人,直到有機會參與雙性戀團體或聚會。
依據克萊恩醫師提出的性傾向量表,其中七個變項:性吸引力、性行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交偏好、異性戀∕同性戀生活方式、自我認同。因著這七個變項,人的性傾向就變得複雜起來。於是雙性戀被表現出來,雙性戀並不是一半異性戀一半同性戀,而是具有非常異質的差別。
這個量表同時也得以看出,同性戀、異性戀也是動態的,非固定不變、人人皆同的性認同。真實生活中,許多人發展過雙性關係,但因為只有「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兩端定點,所以,不是被類歸於(或自己認同)同性戀就是異性戀。
任何一個衣櫃的存在就是壓迫的證據
同性戀也許被鄙視,但同性戀的存在不會被質疑;雙性戀同樣被鄙視,可是雙性戀的存在還被質疑。大多數人對於雙性戀的性傾向不能理解,於是將其視為不存在;也許這些不能理解,能讓一些有同性行為的異性戀者,稍稍安慰,因為他的行為並不表示什麼,他依然還是個「正常的異性戀」,只是偶有同性行為。
對於雙性戀的刻板印象大多是充滿負面的想像,如:雜∕濫交、多重伴侶、自我困惑,以及伴隨而來的責難:騎牆、劈腿。大家說:雙性戀就是沒有出櫃的同性戀;雙性戀若有婚姻,那婚姻就是個幌子。對於不是同性戀就是異性戀,這種立論於只有二元男∕女性別的「單性戀」思維,似乎不可能假設雙性戀可以是身心健全地存在。
我們把人貼標籤、分門別類,我們誤以為有了定位,天下太平;不確定、模稜兩可,帶來恐懼和威脅。
在美國的雙性戀社群發展過程中,愛滋議題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對雙性戀者嚴重的錯誤假設而來的社會汙名,指控雙性戀者的性關係是將愛滋帶進家庭的元兇,使得雙性戀者在愛滋議題上成為最被攻擊的目標,因此在社會主流道德的打壓下,雙性戀者切身體認到社群必須建立、出櫃、以對抗愛滋和歧視。
以雙性戀認同做為一個發聲的主體,選擇出櫃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也許將失去一切。當自我身分被瓦解,就會需要重構,但也許已然被孤立,孤立於異性戀、也孤立於同性戀,擺盪於兩者皆非的無定點狀態。
意識到出櫃重要性的雙性戀運動者高呼:「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經驗,這已經足夠出櫃的理由了」
雙性戀運動者在同志遊行隊伍中所揚起的美麗口號:「我們不是騎牆派、我們是橋樑打造者」,「雙性戀是可實行的選擇、給予均等機會的愛人」,充實了同志運動的內涵。
看見存在看見差異
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從九零年代初期的萌芽,到二○○○年得以公開團體形式,正式進入公領域,並透過官方資源編印《認識同志手冊》。但這本手冊一直出到第四年,才出現了雙性戀的專題。當我們撿拾了字面上的政治正確說法,同志包含: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但在實際工作上,雙性戀常常是消失的。
雙性戀多元異質的聲音,證明了雙性戀的寬廣存在,我們不能不看見。性別不是兩個端點,非男即女,雙性戀也不應該只是能愛男也能愛女,當性別能開展無限可能的時候,愛上不同性別也就有無限可能。於是會有女同志認同的女性愛上男同志,女跨男跨性人愛上男跨女跨性人,男跨女跨性人愛上另一個男跨女跨性人,但她們認同的是女同志而非男同志……。性別的光譜如果有無限的可能,那麼我們就應該能夠想像和理解雙性戀是一種「多性戀」的認同與實踐,不狹隘於單一、固定不變的位置。
人類的慾望模式,千奇百怪,不是每個人都順著同一模式。是男是女,是跨性是變性,是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人人都有著個別差異。雙性戀讓我們看到慾望流動的多元,慾望的無窮可能。每個人即使已經有了清楚的自我認同,都依然有空間發展更新的自己。
當我們開啟了雙重衣櫃,我們已然開啟了無窮可能。
(本文作者為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櫃中之櫃?—雙性戀在台灣∕陳錦華(文字工作者、譯者)
為什麼要談雙性戀?
「我們都已經有了酷兒(Queer),為什麼還要談雙性戀?」當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時,心裡頭真是百感交集。早從九○年初台灣情慾解嚴的那個年代,女人開始走上街頭高喊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同志運動也同時悄悄在校園女性主義的養分下滋長,十幾年來,從地下小眾社團、媒體,一路沸沸揚揚走向專業化運動組織,去年才剛在台北市政府前升起了一面彩虹旗;象徵著酷兒式張狂美學的扮裝文化,也不曾在每年同志遊行中缺席,雌雄同體、「跨性別」(Transgender)等早在幾年前就成為部分學院裡性別研究的重點,而「情慾流動」四個字,也已堂而皇之成為大眾文化中耳熟能詳的字眼。另類情慾議題從學院派性別論述裡,溢散到了電影、文化與藝術的場域,甚至一路跨入了主流媒體;近年來關於同志╱雙性╱跨性的題材愈加受到注目歡迎,儼然成為消費市場中非主流中的「主流」。
儘管台灣的性別研究與同志運動落後西方數十年,但八○年代末期之後,以奇蹟似的速度急起直追,我們從同志、酷兒╱怪胎、一路走到跨性,在研究論述上幾乎毫無時差地與國際「同步接軌」。有論者憂心,這論述上的「突飛猛進」恐怕過於快速、跳躍,是否可以接合在地文化脈絡,根基紮得夠不夠穩當深入,都值得深思觀察。不過至少,就在這些斷裂和跳躍之中,某些議題似乎真的就跳過了、存而不論了,比方說,雙性戀。
由於那些不符合主流性╱性別標準的、偏差越軌的、混雜流動的、在情慾階層底層的主體,好比邊緣同志、雙性戀、變性、反串、SM等,都可被歸為酷兒一族,因此,雙性戀很容易就這麼混在「酷兒」議題中,希哩呼嚕給一併談掉了。但說老實的,像是「酷兒」這類後現代概念,其實僅現身在同志圈或藝文界等特定的文化領域,用以形容某些電影類型、文類或藝術創作,到底有沒有真正成為一個具有顛覆能力的「動詞」,實踐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台灣,「酷兒」恐怕還只是一個形容詞罷了。
除了「酷兒」的範疇,要談雙性戀,恐怕就要到「同志」的主題?去找尋了,然而,把各種邊緣性身份一股腦地往「同志」這個名目下頭塞,究竟是擴大了、細緻化了同志概念的意涵?還是被「同志」這一個大一統旗幟給隱匿消聲,恐怕還有些爭議。而「雙性戀同志」如果可以被視為同志社群的一員,究竟是因為其可作為挑釁異性戀體制的盟友,還是其實是因為她╱他擁有「同性情慾」的那一半?
同運份子可能會很友善地這麼說,我們並沒有忽視雙性戀,我們不僅稱為同志(Lesbian and Gay)運動,我們也用「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或「Lesbigay」這個詞,裡頭早就已經把雙性戀給擺進去了呀!也或者,在某些同志社群或網站裡,也會發現有個「雙性戀同志」的討論版可以抒發心聲,儘管有時也有些來踢館的「雙性戀者算不算同志」的論戰文章,但總之,雙性戀並不是毫無生存之地。但別忘了,「LGBT」、「Lesbigay」這些在同志運動中對雙性戀者友善的新字眼,在西方社會中,可都是經過雙性戀運動者一番赤裸裸的對話、血淋淋的革命才獲得的成果。然而我們似乎跳躍了這個過程,直接挪用的結果,恐怕反而對雙性戀者造成某種壓抑或噤聲的效果。
回顧西方(北美)雙性戀運動的脈絡,一方面肇因於七○年代以降,(女)同志圈內要求純粹性、不與敵人(男人)共枕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八○年代全球愛滋病的興起,被視為性濫交的雙性戀者立刻成為代罪羔羊,在兩股力量夾殺之下,雙性戀運動萌生於八○年代初期,全美各地雙性戀組織紛紛成立,並與異性戀和同性戀者展開激烈而豐富的對話,《Bi any Other
Name》一書,可被視為是這個時期累積下來的里程碑之作。比起七○到八○年代的歐美,現今台灣的雙性戀處境的確沒那麼艱苦,但這似乎只是表面和諧。
雙性戀是什麼?
「當雙性戀應該很爽吧!因為他們可以交往的對象是一般人的兩倍耶!」「雙性戀給人感覺很花心,而且私生活應該都蠻亂的,男女通吃…」這是最常聽到的說法。
「如果發現我的男友是雙性戀,我一定馬上分手,因為這樣情敵太多了,而且我不是男人,永遠也無法滿足他『另一半』的需求,遲早有一天他會劈腿的!」一個異性戀女生說。
「我倒寧可我兒子是雙性戀,也不要是同性戀呀,因為這樣他可能有一半的機會可以變正常…」一個憂心忡忡的媽媽說。
「他們(雙性戀)雖然男女皆可,但遇到了社會壓力,還是會選擇回到異性戀社會的,畢竟,他們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為什麼不挑容易的路?」一位男同志這麼說。
當我隨機採訪人們對於雙性戀的看法,我得到了許多類似以上的回答。在和諧噤聲的表層底下,潛藏著對於雙性戀的恐懼、歧視與偏見。而一位雙性戀朋友則這樣告訴我,「在(女同志)圈內,如果有人問我,我會坦白說我交過男友,但我不會隨便用雙性戀這個詞,這個身份在圈內很有爭議性,很可能會被認為非我族類,或妳根本是個來圈內玩弄同志感情的異性戀…」
除了來自異性戀社會與同志社群的「恐雙症候群」之外,還有另一種常見的說法讓雙性戀更不具有正當性與能見度,「那只是一個過渡或是混淆的階段而已,他們終究會搞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言下之意,雙性戀根本不存在,充其量只是一個邁向終極認同(異性戀or同性戀)的過程而已。
情慾本身充滿不確定性、變動不居的性質,似乎無法被主流社會的知識分類體系所理解。我們有「異性戀」與「同性戀」兩種明確選項,但雙性戀的身影卻是模糊的,他╱她可能被認為是偽裝的異性戀,或是同性戀中的叛徒。人類把各式各樣的情慾經驗硬是裁切工整,塞到既有的框架裡,甚至劃分出高下優劣,讓某個類別比另外一個類別更正常正確。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拒絕理解,很多時候真實的人生並非如此。為了鞏固自我認同,找到定位,或是取信於他人,很多人,當然包括雙性戀者,必須把部分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情慾經驗隱藏起來、淡化處理,甚至告訴自己,那些不重要、不存在。
雙性戀,在主流異性戀體制下,和同性戀一樣,被劃歸為「不正確」的邊緣位置。但某種程度上,雙性戀躲在櫃中之櫃,一個比同性戀更曖昧、更幽微的位置:一個櫃中之櫃。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台灣雙性戀者的身影如此曖昧模糊,以及,為什麼她╱他們不輕易把這個認同標籤貼在自己身上。
雙性戀在哪裡?
被貼滿負面標籤、不被承認、不被看見,要不隱藏在異性戀社會,要不在同志社群?低調沈默,這是台灣雙性戀的處境。如果雙性戀者可被視為一種族?,他╱她們的人數恐怕比妳我想像中的多上許多。事實上,一個屬於台灣雙性戀者自己的社群目前正在網路中逐漸醞釀形成,雖然還處於初步草創、尚在架設平台的階段,仍不免令人好奇,晚了西方社會近二十年的雙性戀運動,是否正在台灣悄悄展開?他們將以什麼樣的姿態、展開什麼樣的對話,又會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都讓人拭目以待。
期待台灣的雙性戀者,有一天也能像《另一個衣櫃:雙性戀的生命故事與認同》的作者們一樣驕傲現身,大聲地說出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