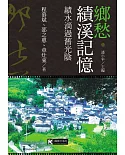開窗放入大江來
要看銀山拍天浪,開窗放入大江來。
一一宋.曾公亮〈宿甘露寺僧舍〉
十五歲進入婚姻,十六歲初為人母,母親在大家庭裡,侍奉公婆、丈夫,教養九個子女,在刻苦、混亂,堪稱極其艱難的少婦生涯裡,端賴坐落街市角落一家租書店裡的言情小說排遣委屈與壓抑。尚未學會做個女人,已然成為人母,年紀小,尚且來不及從娘家萃取足夠養分,母親所有的人際應對,悉數從哀感頑艷的中、外小說裡借鏡、取法,幾十年來,抓緊時間,在生活的隙縫裡閱讀,習染言情小說的誇飾、虛構手法,母親膨脹現實裡的小奸、小詐為深冤、大恨;放大生活中的小歡、小樂為巨喜、狂歡,八十餘歲了,仍然黑白篤定、愛憎分明,全然沒得商量。文學的感染力,穿透時光,浸浸乎直探生命底層,為人生設色定調,而母親自己當然是渾然不覺的。
那樣的年代,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戒嚴的世界看似簡淨安穩,其實險巇難測、暗潮洶湧;小我的苦悶也膠著難解、波瀾漸興。一個小小的、寂寞的女孩兒,自轉學到城裡後,一腳踩空,便掉入舊雨新知眾叛親離的窘境,原本只能躲在閣樓窗簾後,和路上指天畫地、自言自語行走的瘋婦遙遙招手,進行自認的通關密語對話遊戲,而因為街角的那間租書店,自憐被同儕孤立的孩子,偷偷和母親搶看同一窗口,也以那小小的租書店為根據地,似懂非懂地鯨吞蠶食,書本成了她和寂寞握手言和的仲介。她開始看小說排遣孤獨並養成自言自語、自編故事給自己聽的習慣。租書店為母親開啟了一扇對外的窗口,可惜那扇固定的窗口,視野侷限,景致不夠精采,走不遠、飛不高的母親,終於沒能看到銀山拍天浪的壯闊蒼茫。而小女孩兒循著這扇窗口,一路往外迤邐前行,不只見識了海深浪闊,在風雨陰晴的日子裡,還看見「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看見「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更看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絕妙景觀。
或者應該還可以更往前溯。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聽狂風怒號,真叫我心裡害怕。爸呀!爸呀!我們多麼牽掛!只要你平安回家,就算是空船也罷。
國語課本上,天黑風大猶然不能回家的爸爸,讓三年級的她,每每在天色將暗之際,便無端升起憂懼,在颱風夜裡為了遠方不知哪個孩子的漁夫父親輾轉不能成眠;從沒見過海峽的她,因為「海峽的水,靜靜的流。上弦月啊月如勾!勾起了恨,勾起了仇。」而萌生對海洋的嚮往和對彼岸的仇視,使得「買棹歸帆」成為五年級時的天真想望。不經意間,文學慢慢走進女孩的心底。
國、高中階段,因為一本《人間詞話》,她被精雕細琢的字句所收服,瘋狂迷戀起詩詞韻文。買不起課外書,向租書店裡找;租書店裡沒有的,站在台中中央書局裡抄。往往一站便是整個黃昏,像貪婪飢渴的孩子,狂抄、記誦,不管數學、地理或公民的課本上,文本的周邊,全填滿柳周詞、雙李(李商隱、李賀)詩,當然沒有遺漏當年最膾炙人口的泰戈爾。慘綠的歲月中,眼光總是搜尋著幾近病態的華麗悲傷,《紅樓夢》看了又看,專挑寶、釵、黛三角戀愛部分,不斷反芻悲壯。
但行刻薄人皆怨,能布恩施虎亦親。
一一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五》
她試著用文學來抵抗寂寞,並不代表閱讀就可以讓她心滿意足。心底的那個大窟窿,空空的,無時無刻不提醒著她的形單影隻。胡適的一句話在絕望之際映入眼底:「獅子和老虎向來都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跟狗才聯群結黨。」她若有所悟,人緣差,竟得了「獨一無二」的新詮,她因之感到短暫安慰,卻納悶到底在何時、為何故,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老虎、獅子!如果可以選擇,她情願加入狐狸或狗的行列,和他們成群結隊。一日午後,無意中讀到唐人變形小說〈李徵〉,寫博學善屬文的書生,生性疏逸,恃才傲物,平常和友朋飲酒,常口出狂言,所以僚佐都很嫉恨他。忽然在一個夜晚,被疾發狂,不知所終。其後,才被發現居然變形為一隻老虎。雖然「念妻孥、思朋友」,卻自慚形穢,怯於和前往述職的朋友相見。讀到李徵臨走吩咐友人:家人若問消息,「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她忽然心情大慟,淚流滿面。雖然只是一則虛構的志怪傳奇,卻狠狠地在心上一擊!這則故事像度人的金針,為她開示了虎性傷人的前因後果,而她,終於不再只是傷心束手。因為一則奇幻故事,她決心追根究柢,窮究「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處世哲學,期盼有朝一日能因篤行「得饒人處且饒人」的信條,終達「能布恩施虎亦親」的境界。莊子以為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文學正是道的另種變貌,它無所不在,端看是否和生命的經驗相契合、起共鳴。這一刻,她隱約省悟幾年來的文學養成原來旨在開發情意,培養多元解讀人生的能力,為自己找尋一條路、一個說法,它絕不只是區區「聽說讀寫」而已。
樹影興餘侵枕簟,荷香坐久著衣巾。 一一唐.方幹〈睦州呂郎中郡中環溪亭〉
大三,她得了個機緣到文學雜誌工作。每到月底,雜誌即將付梓前的好幾個黃昏,她總和主編據案面對面校對,就著昏黃的燈光,她細細地一句句誦讀著名家的作品,以便主編據以校勘。讀姚一葦談李商隱;看陳世驤論中西文學;念琦君、王鼎鈞、許達然的精緻散文;朗誦余光中、楊牧密度、張力俱足的現代詩;姜貴的桐柏山開始連載了;顏元叔的西洋文學批評史也出場了……一點一滴地,文字的節奏韻律在腦海逐漸形成自己的旋律,淪肌浹髓地殷殷滲透到心上、流露在筆端。幾年後,她終也自己提起筆來,才恍悟閱讀原來不只是「翻閱」而已,要想竟其全功,還得靠高聲「朗讀」!韻律感不止存在於詩,所有順暢的文章都具備優美的旋律,念誦久了,潛移默化,掌握住其中的韻律感,形諸文字時,自然便會隨著熟悉的節奏寫出順暢可讀的文章來。
多少年後,她還清楚記憶著那些個黃昏。王鼎鈞的〈最美的和最醜的〉,曲盡小宦官用最醜的手段維繫最美的信念的過程,曾經讓她多麼驚豔;為了一篇題為〈婚禮鞋〉的文章,又是如何邊念邊涕淚漣漓、泣不成聲;還有當年迫不及待搶先閱讀田納西.威廉斯作品《慾望街車》及余阿勳翻譯的日本小說《草花》連載的熱切心情……年少時,對文學的癡迷,讓她在大學畢業後負嵎頑抗,不惜退還母親在故鄉為她苦心孤詣求來的中學教師聘書,堅持留在和文學最為接近的出版前線,並轉進古典文學的鑽研。而這一留,便再也不曾離開。那種童稚時期劈頭直擊的心頭一點,慢慢引燃了星星的火花,終至在多年後開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燒出三十本的創作並作育英才二十餘年。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一一杜甫〈戲為六絕句〉
求學過程裡,女孩的成績一向不甚理想,即使是喜愛的國文,也從未有過亮麗的成績。她視課文裡的忠君愛國思想為應付考試的虛辭詭辯;孔、孟被闔上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夾死在書本裡頭,〈大學〉、〈中庸〉,充其量只是無聊的制式教條!直到長了些年歲,才知是老師教死了經典,四書無端被聯考怪獸株連迫害。學習原是為了讓生活更容易,然而,短視近利的餖飣字句解說及無趣的作者生平強記,讓文學陷入死胡同,讓許多學生痛恨不已,立誓考完試後,立刻將文學碎屍萬段。
站上了大學講堂,在第一線上從事語文教育,當年那位冒著被活逮的危險,也堅持要在國文課上偷看卡夫卡、大仲馬,甚至於梨華小說的女孩兒,終於了然語文教育一旦讓學生失了興味,光談上課時數或文言、白話比例都是白搭。當老師的,推窗放入了大江,天浪如何拍擊出銀山,得有本事將它說得虎虎生風。教授四書,得讓學生明瞭這些所謂的金科玉律究竟和他們有何關聯,又憑什麼成就其經典地位;閱讀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如果可以讓學生順便看看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再比較一下林語堂的《唐人街》和老舍的《駱駝祥子》,文學的流變傳承就不言自喻!當老師的,如果在語譯之外,還能將〈訪隱者不遇〉裡隱者飄忽的行蹤勾連上詩裡一反一正的結構;讀到膾炙人口的李白〈靜夜思〉,若知指陳空間結構的點、線、面、立體空間的巧妙變化;而王維〈渭城曲〉除了道別贈柳的意義外,若還能說明「舍青青色新」的尖銳齒音所造成的音響上的刺痛感……文學剎那間便添了活力、增了華彩。老師的教學如果不再陳陳相因,如果能自出新意,學生上課怎捨得打瞌睡?當老師的,如果能透過有效的引導、鼓勵,激發學生的想像,讓他們產生參與討論的成就感,學生怎會在進教室時灰心喪志!當老師的,若能將考試視為情意教育的延長,讓學生反思文學和生活的關聯,讓他們藉此看到文學與生活的雙重繁花盛景,並允許他們找到合適或另類的角度切入去詮解人生,學生又怎會視考試為畏途!
杜甫〈戲為六絕句〉詩說明了文章哪須分古今,一切唯「精采」是尚。多麼期待清詞麗句所構築的文學作品,能成為人生行道上一勺解渴的清泉、一處乘涼的遮蔭,而永遠不再是糾纏學生的可怕夢魘。
廖玉蕙
推薦序
玉蕙的書
平 路
「從我們一起重遊舊地歸來的那日起,我忽然開始罹患強烈的相思病,你已然回到身邊,卻才是思念的開始.你一定覺得奇怪……」
音韻感十足,立即可以譜曲。
書中,〈陪你一起找羅馬〉結尾一段。
〈陪你一起找羅馬〉,這篇堪稱經典的散文,我一遍一遍地讀,到底讀了多少遍?每次讀,都有欲淚的衝動。
猜猜看,作者是寫誰?
從開頭第一句,「那年,你十八歲,提起簡便的行李……」簡直有小說的懸宕感,一路寫到重回女兒寂寞時光顧的拉麵店,再寫到女兒逛百貨公司的孤單心境,以至於買來成打成打化妝品:眉筆、眼影、髮箍、小刷子等等,我這讀者早已淚光閃閃,既魔幻又寫實的場景裡:母女在燈下四目相視,大堆的眉筆、眼影、髮箍、小刷子正在床上發出異色閃光,用繪畫的語言說吧,它兩三筆竟然描摹出人生玄奇(懸歧?)而刻骨的感情,所以我也情深必墜,好像也陷在場景中,四壁閃爍著星星月亮,原來,自己正滿心憐惜地設身處地。
「我忽然開始罹患強烈的相思病,你已然回到身邊,卻才是思念的開始……」多麼貼心揪心,玉蕙的這篇散文,其實也補足了父權傳統之下常被漠視的母女情深。
對我心儀作者的作品,我永遠虔誠如小學生,把它們一一排出順序,譬如說,對卡爾維諾,最喜歡的是《如果冬夜一個旅人》,其中,又最最喜歡第八章「月光映照的銀杏樹」。
〈陪你一起找羅馬〉,是玉蕙這本書裡我的第一名。
玉蕙也寫兒子,母子不若母女,與兒子相處,多了一份理性清明。
她寫女兒,我讀起來牽動心肝;她寫兒子,輕鬆多了,還會讓我這讀者哈哈笑。 在書中,她寫兒子購物的心情,引用唐人小說的〈李徵〉,母親想像兒子開始還節制著,心裡掙扎著,「自覺心愈狠、力愈倍」之後,「沒多久就忍不住開始衝動地吃起人來了」,繼續刷卡繼續血拚:「而自從吃過第一個人後,接續下來便沒什麼心理負擔,把吃人的事視若稀鬆平常」。
就用這唐人小說的典故,她形容(其實孝感天地,出差之便而好心幫媽咪買名牌包)兒子是隻「食人虎」,我笑得躺在地下打滾。
怎麼會有這麼詼諧的筆法?
還有那位老太太,讀者一定早就從玉蕙的文字中熟若家人。
曾經把女兒情史一把火燒成灰的母親,在玉蕙筆下總是生動而興味,這本集子裡,讀者卻窺見倔強、好強又逞強的老太太漸漸在繳械,包括廚房裡烹調的堅持也必須放棄,面對這種風燭窘狀,玉蕙形容失去巧手廚藝的母親:「她進退失據,在垂老之年,陡然跌落到陰暗的井底,四顧茫然」。
井底想來藤蔓鬱結,做女兒的玉蕙心惻難當,我們讀來亦覺哀然、悚然。
玉蕙寫身邊親人,看似以雋永寫深情,其實,卻又不止於此,正好像年輕的玉蕙就感悟到的,「文學的養成旨在開發情意,培養多元解讀人生的能力」。說白了,我總覺得玉蕙最擅於舉重若輕,她輕巧著墨,卻點出了人生世態(包括親情倫理)的複雜性。
因為複雜難解,所以有笑的必要,甚至於笑到忘形的必要……,即使遇上的是最荒唐的事體:無論是身上咯咯作響的頸椎、還是買到頂樓私設神壇的公寓,甚至撞到坦露私處的變態男,玉蕙都有辦法應付裕如(讀那段西門町麥當勞前與慈眉善目老男人的對話,保證拍案驚奇)。
她有問有答,兼之自嘲自謔,傻呼呼地問一一這是什麼意思?
跟玉蕙在心裡相親,除了文字因緣,更因為在人世間的溫暖相知。
只要她說她自己,像那篇〈教授別急〉、那篇〈尋尋又覓覓〉,無論在高速公路迷途的無依、還是在公車上找不到按鈴的慌張,但凡別人認為不可思議的事,對我而言,累累前科、歷歷在目,啊,巧的是,竟都屬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糗事。
於是這兩人心證意證。有時候眼神交疊,我們彼此意會,無言地慨嘆天地不仁,竟把這種「瑕疵品」拋出人間(好說是「謫仙」!),害我們在世上吃盡苦頭;有時候我縮在一角,望著她被簇擁在中央,與一干文友說故事,聽眾們嘴角輕咧、眼光如醉,一陣嘻哈過後,玉蕙總以百萬名嘴功力,拋出明快的結語,綜結所有的錯綜複雜。
那一刻笑中有淚,真覺得此生沒有虛度。
都是結識玉蕙的特殊恩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