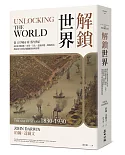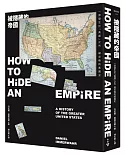奇人與奇書(代序)
──威爾斯及其《世界史綱》
時常為我們這些受過歷史學專門訓練的人感到慚愧。就對大眾的影響力而言,有幾位史學家的著作能夠與房龍、茨威格、威爾斯等人的著作相比。這些人很難被認定為嚴肅歷史學家。不過他們的著作無疑比一般史書有著高得多的可讀性,有著大得多的吸引力,有著另一種迷人魅力和風味,字裡行間透出難以抗拒的激情(這一點尤為史學家所詬病)。一部《寬容》,一部《昨日的世界》,一部《世界史綱》,傾倒了來自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多少人!這幾個人都非常多產。相比之下,威爾斯更為驚人(看看卷末所附他作品的目錄,即可有些初步了解)。他的著作之多,興趣之廣泛,也許是最近幾代人中無人可以匹敵的。而他在英語世界中的影響,大概除同時代人蕭伯納之外,也是無與倫比的。不知道到底該把他歸到哪一類人之列,小說家、記者、政論家、預言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可以說他一人具有所有這些身分。筆者寧願稱之為奇人。
說威爾斯是奇人,主要是基於如下考慮:首先,他在不足八十年的人生中創作了一、兩百部作品,在年近七旬之後仍以平均每年不下兩部的速度進行創作。這些作品中,不下十部仍在不斷被重印,近十次被拍成電影上演。它們涉及科學、文學、社會、政治、戰爭等各個領域。一個取得了如此驚人成就的人,竟然主要靠自學,靠其廣泛閱讀的習慣而成才,這難道還不神奇嗎?
威爾斯全名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英國肯特郡布倫萊一個下層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家小商店老闆,母親一直在附近的厄帕克莊園任管家。七歲那年,他進入布倫萊的莫利學校讀書。不過,威爾斯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甚至在還是一個嬰孩時,特別吵鬧的他就對事物有著非常敏銳的感覺,總是強烈地表現自己的情緒要求。這種性格致使他接受的教育不系統、不連續。十四歲時他就離開了該校,開始步入社會,到溫莎和紹斯西的布店當學徒,一做就是四年。這段時間對他來說並不美好,後來他曾在《客棧》一書中記錄過這種讓人深惡痛絕的生活。一八八三年,他再次反叛,到一所私立學校任教。一年之後,由於偶然的機會他獲得了獎學金,到南肯辛頓科技師範學校(後來的皇家學院)學習生物學,成為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的學生。威爾斯對生物學的興趣,以及他對進化論的迷戀,都來自赫胥黎的影響。在大學期間,威爾斯創辦並主編過《科學學校雜誌》。但到了第二年他就對這所大學的教育感到厭倦。一八八七年,他未拿到學位便離開了學校,又到一所私立學校教了四年生物,直到一八九○年拿到倫敦大學理學學士學位。一八九一年,威爾斯開始在倫敦發展,在一所函授學院教書。他與表妹伊莎貝爾結了婚,但這一婚姻為時非常短暫,不久兩人分了手,威爾斯與他的一位學生埃米.凱瑟琳.羅賓斯重結連理。此後,他放棄了教師職位,開始在小說創作方面發展。
威爾斯的創作生涯始於一八九一年在《雙周評論》上發表的《珍品的重現》一文。一八九三年,其第一部著作《生物學讀本》出版。一八九五年,《時間機器》使他一舉成名。此後幾部更為成功的著作,《莫羅博士之島》、《隱形人》、《世界大戰》、《當睡著的人醒來時》、《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和《空中戰爭》等,確立了他作為科學小說作家的聲譽。這些作品還使他在美國成為名人。讀者面很廣的《時尚雜誌》(?Cosmopolitan&)連載了《世界大戰》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科利爾雜誌》(?Collier's
Magazine&)、《新共和》(?New Republic&)和《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也刊載了他的作品。一時間威爾斯稿約不斷,幾十家報刊、出版社搶著他的文稿。
威爾斯的文學創作可以劃分幾個方面。上面提到的幾部書反映了他早期創作的成果。這些作品都是一些與科學相關的作品,可稱作科幻小說。它們是威爾斯眾多作品中最為現代讀者所熟悉的,其中充滿了想像和迷人的推測、猜想,具體體現了他那一時代人們的政治和社會信念。書中預言了科學創造提供的機會,預見到了坦克、原子彈等現代武器的發明,並發出了關於其危險性的警告。但威爾斯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自一九○○年開始,他以正規小說形式寫作,由想像轉向社會現實,創作了第一部非科學類小說──《愛與劉易斯先生》,寫他在南肯辛頓的學生生活,關注男女之間的關係,並把性當作這一關係中有機的組成部分。評論家認為這部書及威爾斯的其他作品給英國小說帶來了活力,威爾斯也因此被認可為作家。他還創作了其他成功的半自傳體小說,如《客棧》、《托諾—邦蓋》、《波利先生的故事》、《恩典》等。這些小說諷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秩序和支持它的正統派意識,被認為代表著威爾斯文學作品的最高成就。
作為一個對社會負有強烈責任感的作家,威爾斯創作了大量與社會密切相關的作品,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思想。他渴望直言不諱地批判過去,希望像先知那樣寫出一些作品來。《預測》、《未來的發現》、《創造中的人類》、《機械和科學發展對人類生活和思想可能產生的作用》、《現代烏托邦》、《生命科學》、《世界史綱》和《未來事件的形成》等,這些作品使威爾斯獲得了對預言家的稱號。身處動蕩不安的時代,尤其是面對兩次世界大戰,他撰寫了大量政論性作品,如《布特林先生看穿了它》、《工作、財富和幸福》、《公開的密謀:世界革命的藍圖》等。他對頻繁的戰爭憂慮重重,認為這會毀了世界文明。他曾渴望用戰爭制止戰爭,但戰後的各種和約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他希望通過教育改變世界──這是那一時代許多人的理想,但結果並不令人樂觀。威爾斯很早就對社會主義產生了興趣,曾參加英國激進的政治派別費邊社,試圖把它擴大,致力於宣傳和群眾運動,但因蕭伯納和西德尼.韋布夫婦等資深成員的反對而落敗。他曾數度訪問蘇聯,與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等進行過交談,但蘇聯的發展令他失望。威爾斯相信未來將是「教育與災禍之間的競賽」,解決世界災禍的辦法是進行世界性的教育。按照他的夢想,國際聯盟能夠消除世界秩序不穩定的危險,創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但其晚年世界危機的日益加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他幾近絕望。結果他愈來愈陷入悲觀主義的情緒之中,《威廉.克里索爾德的世界》、《即將來臨事物的形態》、《世界大腦》、《走投無路的心靈》以及他最後一部有持久價值的著作《自傳實驗》,都表達了他對人類未來前景的悲觀態度。
不過,雖然他對未來不無悲觀,但仍是一個行動主義者,而非消極等待。在此,我們不妨引用威爾斯自己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末的幾段話來看看他的信念:「如果我有點像社會平等論者的話,這……是因為我要使機會普遍,不讓一個有價值的人失掉機會。如果我要求經濟上的變革的話,那是因為目前的制度保護而且培植著一大群揮霍的浪子……如果我反對民族主義和戰爭的話,這不僅是因為這些東西意謂著精力的巨大浪費,而且還因為它們維繫著一大堆盲目的紀律和忠誠的教條,以及各種各樣的旗幟、制服和閱兵式;我反對民族主義和戰爭,還因為它們把我們的生命置於一些受過訓練的傻瓜的擺佈之下。如果說軍國主義和戰爭不比幼稚可笑的東西更可怕的話,它們至少也是一種十分幼稚可笑的東西。……我的政治思想是一個公開的圖謀,其目的是加快這些討厭的、浪費的、邪惡的東西──民族主義和戰爭──的消滅,結束這個和那個帝國,並建立起一個全人類的帝國來。」他篤信科學的價值,「正是在科學領域裡,我找到了那種對偉大目標的大公無私的忠誠,我希望這種忠誠最後能擴展到人類活動的整個領域中去。也正是在科學領域中,我發現了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相互合作,來增長人類的知識。我們都可以成為科學的自由國度裡的公民」。固然,「世界在過去幾年裡顯然變得更黑暗、更危險了。在廣大的地區裡,公開的言論自由消失了;混戰廝殺、大量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經濟生活的分崩瓦解愈來愈嚴重。暴力已經向世界和平進逼;人類文明生活的水平顯著地在下降。我們許多人對蘇俄的生活方式所懷有的希望已逐漸消失,幾乎化為烏有了」,正因為如此,「採取積極行動來阻止這種衰敗現象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我們「必須構想出一個可以接受新世界的遠景。要工作,要努力工作,產生出一個經過探究、試驗和考驗的共同計畫,把人類的思想統一在一個世界的新秩序裡!……任何更美好的生活的基礎必須是一種教育革命,一種新的百科全書主義,一種新的精神方面的統一平衡;不能做到這一點,人類就必定滅亡」。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威爾斯與世長辭,當時他正主持一個研究如何應對核戰爭的種種危險的專案。
仍記得第一次閱讀《世界史綱》的情景。那是一九八三年年初,該書的中譯本剛剛出版的時候。仍記得一些當時閱覽此書的一些感受。當時國內史學界關注的是土地關係、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經濟關係、資本主義萌芽等,在歷史教學和歷史課本中隨處可見的是馬恩列斯等經典作家的論述。不記得課堂上有人講過文明問題,似乎更沒有人關注過人類的命運等問題。「文化」一詞倒時常被提及,但它被理解為狹窄的文學藝術建築等,在每一節的最後孤立地論述,完全是一種點綴。本應豐富多彩的歷史變得枯燥乏味。《世界史綱》讓人為之一振:歷史竟還可以這麼去寫,歷史竟還具有如此的魅力!再次翻檢此書,仍有這麼一種感受。
撰寫歷史並不容易,撰寫通史更加困難,而以一人之力完成這麼一部巨作,更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事。因為「接受編寫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綱的這項任務,對任何已經成名的歷史學權威來說,會意謂著危及學術聲望的災難」。一個未曾接受過歷史學專門訓練的外行人卻完成了這一宏業,完成了一部影響了許多人的巨作,這不能不讓人再次嘖嘖稱奇。
《世界史綱》出版於一九二○年,它的意圖就在於「以平直的方式,向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展示,如果文明要想延續下去,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發展成為世界性聯盟是何以不可避免的」。而其一個主題就是要說明,世界只有通過教育而不是戰爭和革命才能得到拯救。概括起來,我們認為《世界史綱》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該書達到了一部世界簡史所能達到的高度。它從地球的形成開始談起,一直敘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簡明的筆觸敘述了世界上各主要文明、文化的進化、發展過程,描寫了人類取得的勝利和遭到的失敗,指出了人類面臨的主要危險。這麼一冊書在手,能對整個世界歷史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威爾斯就像一個導遊者,領你沿著文明之路(包括如何進化到文明)從遠古最早的開端走到現代,讓你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長和變化。誠如作者所言,他是一個導遊者,領你拜見亞歷山大大帝、波斯諸王、羅馬皇帝、十字軍戰士、中國皇帝、基督教教皇、法國公民、俄國沙皇等,當然,也領你去細細體會人類文明永恆的東西。然後,他會在你身邊站住,輕輕地對你說:「這就是我們的遺產。」
其次,這是一部「私人的史綱」。雖然作者不是一個歷史學者,但他有一個癖好,即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神往不止。曠野是他的家,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史學領域裡遨遊,而不必顧忌種種清規戒律。因而,本書在章節的安排和著力的大小上,甚至在對事件的評價上,可以比較充分地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在本書中,可以讀到在其他煌煌史學鉅著中也語焉不詳的東西,比如,書中可以用相當的篇幅敘述亞特蘭提斯的傳說,可以用三十餘頁去講述亞歷山大大帝,可以用十幾頁去講亞歷山大城的科學與宗教,可以專節敘述一八五一年的世界博覽會。受作者個人思想的影響,作者對各種進步運動,如宗教改革、達爾文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等人的實驗、社會主義運動(帶有作者所處時代的特徵),不惜筆墨。這是一部獨具特色的老書,即便到了今天,閒暇時翻翻它,仍會發現不少讓你覺得新鮮的東西。
這無疑是一部通俗的史書,但它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在筆者看來,也具有非凡的價值。它沒有嚴肅史著的學究氣,而且比那一時代的許多著作都要早地擺脫了民族主義乃至(在某種程度上)歐洲中心論的褊狹。書中關注的是人類文化的遺產,包括思想、文化、宗教等遺產,而這是人類文明歷程中真正具有價值的東西。本書獨具的還有對科學的關心。我們不妨擷取幾句:「在野蠻人和原始人看來,大地似乎是整個宇宙的一片平坦的底板……望遠鏡的發展的確標誌著人們思想的一個新的階段,人生觀的一個新的境界……它解放了人們的想像力。」「自從最初的文字出現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開始有了一種新的傳統,一種能永存不朽的傳統。」作者稱頌了中國人的智慧,但也對中國智慧的侷限性感到困惑:「中國在六世紀就知道火藥……但為什麼他們從來沒有組織起一個對世界近代科學起先導作用的記載和合作探討的體系呢?雖然他們的一般訓練是有禮貌而克己的,為什麼思想教育從來沒有滲透到一般民眾之中呢?雖然他們天賦才智特別高,為什麼中國廣大群眾從來一直是,而且至今仍是文盲居多呢?」也許你不同意作者的結論,但無疑你會同意,本書注意到了人類發展史上一些有重大意義的東西。
從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字裡行間傾注著激情。佐以作者非同尋常的文筆,你會感到讀這麼一部書是一種享受。厚厚的三十八章,計約八十五萬字,涉及的不乏枯燥的歷史事件,但深入進去這部書,你絕不會有這種不好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當作一部小說來讀。作為一位受到蕭伯納推崇的作家,威爾斯在書中充分發揮了他的這種才能。比如,在描寫佛陀得道的經過時,作者這樣寫道:「喬達摩獨自遊蕩了一個時期,歷史上最孤寂的人,正在為光明而戰鬥。當一個人的心靈抓住了一個巨大而複雜的問題時,它向前邁進,一步一步地鞏固陣地,並不了解已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直到突然間,就像黑暗中忽然大放光明一樣,它實現了它的勝利。看來,喬達摩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他坐在河邊一棵大樹下,就食時,達到了這種徹悟的境界。他似乎覺得自己已明白了人生的奧祕。據說他坐著深思了一天一夜,然後起身把他見到的傳諸世人。」然而,人世間還有災難,還有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了四年零三個月,它幾乎逐漸地至少把西方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拖進了漩渦……戰爭已變成一種氣氛,一種生活習慣,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然後。它又突然結束了……人們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興奮的青年們和度假的年輕士兵們組成稀疏而嘈雜的遊行隊伍,擠過人群,盡力做出歡樂的樣子……鞭炮和花炮到處亂扔。但是人們並沒有什麼共同的歡樂。每一個人幾乎都因為損失太重,忍痛太深,沒有什麼熱情去慶祝了」。你不得不歎服,豐富多彩的歷史就應該用這樣的文筆來寫。
自然,書寫得好,還需要譯得好。翻翻版權頁,你就會發現,在現在速食文化盛行的情況下,再找到如此強大的翻譯隊伍幾近夢想: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他們哪一位不是中外兼修的大家!這個譯本依據的是在威爾斯原著基礎上由後人修訂過的版本。此前,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國就出版過另一大家梁思成等翻譯、梁啟超校訂的威爾斯原著初版本。但如果有暇,到圖書館找來那一已經發黃的譯本與現譯本對照著看一看,相信會有不少收穫。筆者甚至覺得,拿來梁譯重印,同樣會產生引人注意的效果。
肖昶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導言【1】
《世界史綱》編著的經過和宗旨
【1】現在這個中譯本,是根據原著一九七一年增訂版重新譯出的。這一版除修訂了一部分威爾斯著作中已過時的材料外,還增加了主要是第一次大戰後到一九四九年的部分,即第八篇的第三十九章一部分和第四十章。但為了盡量保持威爾斯原著面貌,這個中譯本把增加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全部略去了。
本書譯者除已署名者外,還有李佩娟也參加了部分翻譯工作。地圖的翻譯工作由聞宥、陳佳榮擔任。地圖和若干表解的繪製工作由王傳紀、楊節鏗、何春鳳、皇崇尼和黨力文擔任。
地圖和插圖均據原書,書中方括號內的文字係譯者所加。
◎一、本書是怎樣編寫成的&
這部《世界史綱》最初是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編寫的。分冊出版時各附有插圖,一九二○年詳加修訂,合併成全書重印。一九二三年(一月)為了再版又一次嚴格修訂和重新編排,一九二五年重新發行一個修訂的和附有更豐富的插圖的版本。一九三○年發行的是全新版本,多處經過重新編排和重新編寫,並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這個版本一九三九年又進一步經過修訂。
推動一個作家在一九一八年去嘗試編寫一部世界史是有許多原因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末、最膩人、最令人感到幻滅的一年。到處是罕見的匱乏,到處是悲痛的哀悼。死亡和傷殘的總人數高達好幾百萬。人們覺得面臨著世界事務的危機。他們過於疲乏和悲痛,無意去考慮錯綜複雜的前途。他們弄不清楚他們究竟是碰上了一次危及文明的災難,還是面對著一次人類集團生活新階段的開始;他們用了如此直截了當的非此即彼的簡單眼光來看待事物,他們一直抱著希望。關於可能發生的國際政治的新安排,關於廢除戰爭的國際條約,關於國家之間的聯盟、民族之間的聯盟,議論紛紜。每個人都是「從國際的角度來思考」,或者至少試著這樣做。但是有一種普遍的認識,到處覺得對於這樣突然地和悲劇性地落到世界上這些民主國家頭上的許多重大問題的要害所在是了解得不夠的。「這些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他們問,試圖從有關●塞拉耶佛的爭端和比利時的「一紙條約」的背後去查究引起這些事情的更廣泛、更深遠的原因。這次跨越萊茵河的悲劇性的仇殺的開端是些什麼呢?為什麼它竟會影響整個世界呢?為什麼日本在半個世紀之前還是個詩情畫意的地方,還是個淺薄手筆下的傳奇世界,還是個幾乎和另一個行星一樣遙遠的詼諧喜劇的鄉土,而現在卻正以巨型戰列艦在地中海上巡邏呢?為什麼沙皇帝國會像夢一般的消逝了呢?土耳其老實說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這樣重要?什麼是一個帝國?帝國是怎樣開始的?是什麼使德意志從多種多樣的小邦轉變成一種侵略性的意志和權力的象徵,並使人類的一半對德意志的威力產生恐懼呢?
人們,男的和女的,試圖回憶他們在短短的學生時期從學校裡學得的褊狹的歷史,他們發現那無非是一張枯燥無味和部分已忘掉了的各國帝王或總統的名單。他們試圖查閱這些事件,面前是浩如煙海的書籍。他們發現,他們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義的眼罩來學歷史的,除了自己的國家之外,一切國家都視而不見,現在他們突然發覺周圍光輝奪目。這使他們在確定所討論的各事件的相對價值時特別困難。許許多多的人,世界上一切有識之士,當然──他們並不是已經受過專門訓練的──多多少少有意識地在尋找整個世界事務的「訣竅」。事實上他們為了他們自己所用,都在頭腦裡即興地編寫著世界史綱。
作者在任何專業意義上都不是一個歷史學者,但是自從他一生事業的開始起,一直在編寫他自己私人的史綱。他經常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神往不止。這是他的癖好。即使在他還是一個愛好自然科學的學生時,他常保有一本閱讀歷史的筆記。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說《時間機器》(1894),是關於人類命運去向的異想天開的一種推測;《當睡著的人醒來時》是對我們文明發展的生動形象的誇張;《預測》(1900)是想論證當代潮流某些可能的後果。在他所寫的許多書裡,例如《輝煌的研究》和《不滅的火焰》中都綴上了小世界史綱的花飾。因而當他碰到戰時思想動亂的時候,他即使不是特別有了準備,至少也是特別傾向於對過去的和現在的事物採取一種通觀全局的看法。在他開始編寫這部《史綱》以前的一些時候,他曾從事於研究戰爭善後問題和創立一個國際聯盟的計畫;那是在已故的威爾遜總統接受那個建議以前的那些日子裡。做這樣的工作就必然要參與各式各樣的宣傳團體和會社的爭論及組織活動。在這些集會上的討論十分生動地顯示出在一切政治活動裡一個人對過去的看法是極其重要的。的確,一個人的政治活動豈不就是他對過去的看法在行動上的表現嗎?所有那些對國際聯盟的各種計畫感興趣的人,他們的思想是亂七八糟的,因為他們對於這個人類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曾經是什麼,因而將會是什麼這些問題,只有一些極為模糊的、異樣的和雜亂的臆度。很多情況是異常精確的專門知識卻和對一般性歷史的最粗淺和最幼稚的臆度相結合在一起。
對作者來說,似乎越來越應當把地圖和筆記收集在一起,比過去更有系統地進行閱讀,把那些對他還是極為模糊的歷史問題搞個清楚。當他著手這樣做時,就清楚地看到,要是把他私藏的關於歷史概要的備忘錄,變成一種提供給比他自己更忙碌和經常被別的事務分心的人們使用的普通讀本和手冊,這會比越來越沒有希望地糾纏在未必會產生的世界聯盟的那個不可能出現的憲法的爭吵上有益得多。他越是打算對人類在時空中所處地位的現有知識寫個評論,越覺得承擔這項任務困難、引人和欲罷不能。
一開始,他打算整體回顧一下歐洲的統一體;對羅馬體系的興亡,對帝國這個觀念在歐洲頑固地存留下來,對不同時期所提出的統一基督教世界的種種計畫,列出一份提要。但是很快就明白,沒有任何真正的羅馬或者在猶太從頭開始的事物,也沒有可能把這個故事侷限於西方世界。這些都不過是一出巨大得多的戲劇裡較後一幕而已。他發現,這個故事一方面把他帶回到了在歐洲和西亞的森林裡和平原上的雅利安人的起源時期,另一方面又把他帶回到了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一度曾有人類生息而現已淹沒了的地中海盆地的那些早期文明。他開始認識到歐洲歷史學者怎樣嚴重地貶低了亞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國等文化在人類這出戲劇裡所分擔的部分。他開始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遙遠的古代怎樣依然生氣勃勃地活在我們的生活和制度裡;看到如果對人類集體生活的早期階段沒有一些了解,我們對今天的不論是廣泛的政治、宗教或社會問題的理解就會怎樣地淺薄。這裡也包含著對人類起源的一些了解。
當他思索推敲怎樣編寫這部《史綱》時,這部《史綱》本身就已伸展和擴大了。有一個時候,他面對這不斷在擴展著的工作的史詩般的無邊天地猶豫了起來。他追問自己,這項工作由一個歷史學者來做,比起由一個迄今不是寫推論性的論文就是寫小說的作家來做,是否會更好一些。但是現在似乎又找不到哪一個歷史學者能夠這樣膚淺──我們是否可以這麼說──能夠這樣廣博和這樣淺顯,以致可以概括這個計畫的浩大的領域。
現今的歷史學者大多是些學究氣十足的人;他們唯恐有微小的錯誤,而寧可使歷史互不連貫;他們害怕寫錯一個日期,遺人笑柄,甚於害怕做出可以爭論的錯誤評價。這樣做是正確和應該的,在一個匆忙和輕率的時代裡,所有專心從事工作的人們應當遵循一個要求精密準確的嚴格標準。但是這種要求細節上準確的高標準,使我們無法從歷史學家那裡找到我們這裡所需要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這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任務,而是一件苦惱的工作。從他們那裡可以得到的只是積累起來的資料,而不是裝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他們現在確實已給我們提供了極其有益於學者們的卷帙浩瀚、手筆眾多、觀點繁雜、神旨意趣各個殊異的傑出的和可貴的編著。但這些宏偉的功績,對於在人生旅途中過往的普通公民來說,為了日常的目的,在感染力和應用的便利上都和卷冊可以滿架的百科全書並無二致。
在美國誠然可以找到若干有用的小本世界通史,著名的如魯賓遜和布雷斯特德合著的古代和近代史,以及赫頓.韋伯斯特的和W.M.韋斯特的類似著作;但是這些作者的對象是中等和高等院校,而不是普通讀者。F.S.馬文的《活著的過去》又是一本值得欽佩的關於思想的進步的論文,但是沒有提出多少扎實的事實。接受編寫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綱的這項任務,對任何已經成名的歷史學權威來說,確會意謂著危及學術名望的災難;即使做出了這個許諾,普通讀者要讀到這部書,也還是要等待很多年。然而,本書作者的地位卻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意願上與學術界的尊嚴相隔有如他與公爵的爵位一樣遙遠。這使得他能引起公眾對歷史的興趣,而不致像一個公認的權威那樣會招來任何尊嚴和榮譽上的損失以及惡意批評的危險。不受觸犯是他的一項可喜的特權;他是一個文學上的貝都因人,曠野是他的家,除了自己的姓名,不知道有更值得驕傲的稱號,唯一可以想像到的榮譽是他自己的人格。冒失地忽略了這個或那個專家所壟斷的這個或那個珍貴的專案,也許會引起他們的震怒;但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他能毫無愧色地去利用標準讀物和普通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他甚至無須佯作新穎的發現或獨創的見解;他所要做的較為簡單的事是收集、安排、衡量人類的偉大驚險經歷的各個部分和各個方面,然後動筆寫下來。他沒有給歷史增添什麼內容,至少他希望沒有增添什麼到歷史裡去。他只不過為大量的資料作一個摘要,其中有些是很新的資料,他是以一個通俗作家的身分考慮到其他像他自己一樣的普通公民的需要而這樣做的。
然而,這個題目是這樣的輝煌燦爛,以致任何一種寫法,不管多麼不出色,都不可能使它完全失去它固有的所向披靡的瑰瑋和莊嚴。這部《史綱》如果有時寫得吃力和可憐地不足,卻也有時似乎有它本身的計畫和它自成的體系。它的背景是深不可測的奧秘,群星的謎團,無可量度的空間和時間。出現了生命,它為獲得意識而奮鬥,結集著力量,積聚著意志,經歷了億萬年代,通過無數兆億的個別生命,直到它抵達今天這個世界的可悲的紛擾和混亂,這個世界是如此地充滿著恐懼,然而又如此地充滿著希望和機會。我們看到人類從孤獨的開端上升到現今世界友誼的黎明,我們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長和變化,它們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變化得更加急速。這場表演在一個極大的問號上結束。作者只是一個導遊者,他把他的讀者最後帶到當今的邊緣,各種事物正在前進的邊緣,然後在讀者身旁站住,輕輕地向他耳語說:「這就是我們的遺產。」
這本《史綱》不過是對過去百年內地質學者、古生物學者、胚胎學者和任何一類博物學者、心理學者、民族學者、考古學者、語言學者和歷史研究者的大量活動所揭示的現實的初始圖景加以通俗的敘述。如果認為它在任何意義上超過了這一點,那將是荒唐的。歷史學在一個世紀以前只是些書本上的東西。鑽書本的歷史學者現在相當勉強地和冷淡地承認,他的地位只是對廣闊的整體提供可疑的文件罷了。
我們的《史綱》描繪了這幅巨大的圖景。這是作者盡了最大的努力描繪的今天所見到的這幅圖景的情形。但他是在他本人的侷限性和他的時代的侷限性下寫作的。這本《史綱》是一部適合於現今用的書──它並不奢望成為一部不朽的著作。它不過是一種通俗的敘述。這部一九三一年的《世界史綱》有朝一日將跟著它以前的幾版一起進入舊書箱和垃圾爐。更有才能的手筆,具備更充分的資料和更豐富的工具,不久就會用更美妙的詞句寫出嶄新的史綱。本書作者會覺得比起他自己所寫的這部《世界史綱》來,更喜歡讀的那部將是二○三一年的史綱;不但閱讀,甚至會帶著更大的好奇心去仔細地翻閱它的插圖。
所有我們這些人,如果通過某種奇蹟,能得到一部二○三一年寫的世界史綱,我猜想,一定會一開始就翻看最後幾章裡令人吃驚的插圖,然後去閱讀和這些插圖相配的正文。多麼驚人的大事呀!多麼難以相信的成就呀!但是,隨後,至少本書作者會翻回到前面那些章節去看一下這本書裡所講的故事有多少依然倖存。
大概前面那部分的總體輪廓大體上還是相同的,但是會有千百條現在還不知道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細節,以及現在還想像不到的許許多多關於人頭骨、工具、被埋沒的城市、消失了的和湮滅了的民族的殘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