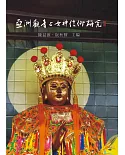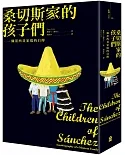前言
巫者的意義生成
余德慧
對台灣巫療遇的研究興趣早在我念台大心理系博士班的時候。也許天生無法適應實驗室的科學思維,每每在做博士論文的實驗室研究,心裡恍若沙漠成片,對那些被硬弄成模型的心理學知識一片麻木,只好偷空到廟裡走走,結果逛了不少乩童的堂口,也權充信徒,讓乩童為自己辦事。
其實自己小時候常跟著祖母到一位女乩童家,一群婦女圍在圓桌邊,很家常地聊天。慢慢地,女乩童開始打哈欠,隨著裊裊香煙,神祇溫柔地附身,然後為婦女們辦事,有說說話的,有做做小法術的。說話裡有教訓、有安慰、有排解也有預言,小法術則包括除煞、去霉、消災與祈福。
這個小小的空間,一群受苦的婦女,有的作媳婦的、有作婆婆的,也有著老姑娘。我祖母曾經生下我小叔,三歲夭折,只有我父親一個孤子,那時她雖已經作了婆婆,但是婆媳不睦,自己身體也不好,一個女人家孤伶伶守寡二十幾年,日子怎麼過的,我這孫子當然就不得而知,但是在我長大之後,目睹乩童的堂口人來人往,憂苦的、生病的、不受教的、糾紛的、外遇的、不順的、破產的,全都上門找乩童辦事。
那時我已進心理研究所,多年來既接受心理諮商的訓練,也一直接受學院式的臨床心理學的訓練,但是我十分確定,這些人如去找心理治療師,絕對會失望而回;從西式心理師的觀點來看,這些人缺乏接受諮商的「心理能力」,對自己的心理過程缺乏敏銳的觸覺,更缺乏文化素養以理解「心理學的觀點」;反之,從這些人看心理治療,則覺得心理師固然一派說理有理,心裡卻既不感動,也難以舒坦解憂。
後來我才開始明白,人生其實是場殘酷境遇,不斷地給出斷裂的處境,生老病死還算人生常態,許多的意外,讓我們看到殘酷的本質,而這個大黑洞不斷地襲擊著任何活著的人,而所謂風花雪月、人生美景都只是在殘酷被遺忘的短暫時刻裡的喘息,而巫者正是被這殘酷所引出,在長久的歷史底蘊之下,用來減低人間殘酷的療遇(healing
encountering),就如宋文里教授所說,人間不一定有療癒,我們的苦痛不一定能抒解,但卻不斷出現療遇,為了有一絲希望而彼此用療傷的心情而來見面。
在心理學領域探討本土療遇的研究不多,幸虧在三十年前有一位年輕的美國精神醫學的人類學研究者,為台灣帶來了乩童療遇的研究領域,他就是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他在六○年代在台大精神科與文化精神醫學者做研究,但他並沒朝國際所關注的文化殊性的精神病學走,而是以人類學的方式做台灣乩童的療遇過程,也寫過許多這方面重要文章。
凱教授的研究對我個人是個引路燈,而中研院民族所的前輩、長輩與師輩們更是替我這後進提供一個被允許的背景,人類學前輩們的民間宗教研究替我們打下台灣巫宗教的基礎,無論儀軌文本、廟會、祭祀圈、現象描述都有一定的水準,而我心理學的老師,特別是楊國樞教授,在實證科學強力執政的氛圍底下,有雍容的胸襟接納走偏路的生徒,實在是我一生最幸運的機遇。而如今在心理學界願意投身研究台灣本土宗教的人也慢慢多起來,宋文里、余安邦、盧蕙馨教授都是同行的知識伙伴。而喬健教授以一個人類學前輩,寬容地接受我到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任教,使我有機會開啟牽亡的療遇研究。我的一些研究生對巫宗教的研究興趣,也使本書得以出版,他們是劉宏信、彭榮邦、劉美妤以及石世明。
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巫」是一種由社會情懷與個人另類身心狀態的組構,在個體的那邊,它不似人格或自我那麼明確地由個體所確定,而是逐漸朝往第三人稱的他者經驗發展,也就是個人的另類狀態。在西方理論強調薩滿的夢幻空間,好似與社會情懷無關,但以台灣的乩童或尪姨為例,他們卻非常需要社會情懷的誘導,也就是對人生苦難的感受。
在靈知系統方面,巫的收圓理論與諾斯替宗教非常近似,一方面顯示它們可能同源於社會情懷的因素,一方面也顯示它們的「地下」性質:即對經文的自圓其說,不受限於正典文本,甚至缺乏正典文本。這樣的型態顯示巫宗教的身體性優先於文字性,而且許多巫宗教的自我生產皆不在經文層面,而保留在身體的直接性,這可以由乩童訓練的各種訓身、踏步法、天語(舌語)、天畫(塗鴉)看出。
由於是在宋文里教授的「任意畫」實驗以及「碟仙」實驗更清楚地顯示「巫」空間存在於沒有意義、沒有明確秩序的領域與符碼領域的重疊空間,例如任意畫的畫筆所觸有著各種身體的滑動、顫抖、緊繃、放鬆,這些身體所顯示的各種畫筆並不組構秩序,而是提供一個基底,讓意識摸不著意思,甚至連象徵都還是很隱晦地不明朗。在碟仙實驗更接近將現存的斷片加以拼湊,這往往是促動意識思考的刺激,使得意識試圖要去「使之完形地出現意義」。從不確定朝向確定是非常精細的過程,但是巫者並不見得有這些細工,因此,某種意識的技巧就被發展出來,供為修補術。我們固然可以從意識的修補(如自圓其說)看出其鑿痕之跡,但若以此為追索其意識的造作,可能會失之毫釐,繆之千里,因為意識作用已經是很後來的事,真正要注意的是巫者的夢幻空間的孕育過程。
首先,我們必須先接受維特根斯坦主張「宗教無真假」的前提,宗教本身是苦難人類的相伴相生的東西,其源頭正是來自「冥識」,也就是在昏暗意識、不明所以的狀態,而冥識的出身地正好是「非現實」的區域,在那裡,身體的千頭萬緒依舊以無序的方式亂竄,連意象都呈現混亂的流動。這個源頭在一些高制度化的宗教已然被遺忘,但是對巫宗教卻依然還是一個重要的初始狀態。
非現實一直是宗教最核心的質素,所有的虔信、順服與大愛皆在非現實裡實現,因此非現實有時被誤解為」「新存有」(new
reality),實則不然,非現實一直是原初的,靈知的神話正是在非現實展開的語言,若過度被引伸到現實裡,非現實即遭取消,這點可以從張光直在《美術、神話與祭祀》指出,後來巫咸是政治權威掌控統治知識的工具,混入現實裡的巫咸被說成「明察聰慧、專心一致、內心虔信」之人,以「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宜朗」
,這顯然是俗世裡界定宮廷文書資訊人員的說法,與我們在台灣民間看著搖頭晃腦附身的乩童不很相近,到底巫者是以冥識而能通天地,還是能「上下比義」而成為人神之間的交通,涉及負性與正性兩論的看法。
負性論是以榮格的弟子Erich Neumann(1963)所主張的母體空間為孕育神話的原生處,只有大母神與如胚胎的孩子,這孩子還在子宮裡,還在母體的胎盤裡被搖晃著,此際母子一體,猶如靈知裡所謂「未墜落之前的狀態」,透過歷時性的機制,Neumann
認為初民的冥識逐漸沿著自我意識的分化產生不同的對象性,而表徵於幼男神、小男神,終至大男神與父神。如果用精神分析的語言來說,男神的出現意味著父親的律法以疊層的方式覆蓋了母體空間,使母體空間只能以裂隙透光的方式,顯露出母體的殘餘斷片,這種疊層顯示在巫宗教的符號生產方式。
正性論所謂的巫者已經是「以父之名」的掌權者(祭司兼國王)或賦權者,也是符號生產排序而宰制著世界,因此才會賦予精明才智。我們觀察民間宗教的乩童作法,在自信之間含著暗影,很明顯的重現符號生產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隨興」的強言,也就是說,巫者非常容易接受各種來源的暗示,而且接受暗示的邏輯是「碎碎邏輯」,每個邏輯點都黏附在當下的情況,無論是牽亡時師姑與家屬的應答,或是附身乩童的言語多少有「逞強」的意味,即使當他們的預測不為求者所附和甚至是相反意見,他們也很能夠從一個邏輯點移到另一個邏輯點,兩者之間無須同一的連貫性。但是,巫者還是隨著共構的同時性平面出現符號秩序,但又不取消意義的浮浮沈沈的模態。
過去的科學主義者將巫者的強言視為想像的強力捏造,這個指控的基礎其實來自理性主義的自大與無知,從符號意義生產的觀點,毋寧說巫者是母體殘片的追索者,暗示的消息來自陰影與曖昧,來自某種隱晦的岐義,這些殘片都等著求者某種意義生成事件的啟動,可能是某個受難的刺點,可能是某種違常的警覺,而這些刺點正是使巫者產生詩歌、發出聲音、突然怒吼、瞬間流淚的情懷,當這些殘片刺點與巫者的詩意連接起來,某種人情義理或倫常的虛構就開始發揮作用,所以,我們可以從外表的顯義語言聽到巫者的「辦事語言」充滿庶民世界的倫理道德,必須記得那絕對只是表象,在這表象的底層,有著自由的如夢空間,在那裡,人的記憶如深井的迴音,不斷去搖撼震動表象的符號,使得剛生成的符號無法站穩它所代理的意義,雖然巫者的辦事語言充滿了決疑、判斷、預言、指示的秩序,但是這些明顯可見的話語只是派生的生產,根本還是冥識與身體兩者的「非符碼的真實」。
「非符碼的真實」意指意義生成的事件所指向的真實是隱藏不見的,可見的只是巫者的辦事語言,然而正是辦事語言的遮蔽,使得減低殘酷與受苦的真實部分不見了,而以被否認的狀態保留在前符碼或非符碼的真實域。真實始終是一直被否定著,始終是「非」,真實始於其中的「非」 。而巫者的決疑術的形成則是如克里斯托娃所謂的意義生成的過程
會使巫者主體處於圍繞意義的「法」(秩序)的訴訟場,這時已經是意義生成的晚期,「法」(秩序)已經在象徵意義秩序的約束性與強制性底下形成圍場,為了合乎「法」的要求秩序而進行的糾紛與矛盾的過程,因此使得符號象徵群相互申訴、交互裁決、強迫變化。
若然,巫者主體必然是說話主體,在研究者與其同僚所發展的「裂隙動力學」指出:
當裂隙不斷形成可見的要求時,我們不會保持「無話可說」,而是用一種飛躍的姿勢,擺明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成為說話主體。以裂隙為主體是一個黑洞欠缺的匱乏,沒有辦法說自己的主體,就如人置身於黑暗當中無法超拔,但由於在黑暗史中的智人的意識啟蒙,主體總是要逃出冥識的,所以就開始轉身裝扮成說話主體;在此,作為與聖多姆相異的層次,說話主體就須得承認語言的必要性。
然而,為何巫者之語不同於日常語言?識者以為宗教用語的譬喻性是巫者的主要部分,以及巫者對譬喻語言的修辭行動,但筆者認為這觀點還是未盡其義,真實的非語(被隱藏的語言)應該具有米謝爾.亨利所說的「生命語言」。所謂「生命語言」是:
當生命處於痛苦的感動(pathos)之中時,它並沒有說,「我很痛苦,某人有罪」,它還?有與「我」發生關連,意向性在這裡還?有構成含義,含義也還?有構成對「痛苦」的言說,言說本身還不是某種理想(ideal)之物。可是,一旦我們詢問「痛苦如何言說?」時,我們便不可避免地感覺到它在自己的痛苦肉身之外,還對我們說了某種東西,因為任何痛苦都不會作為無人的痛苦而降臨。實際上,痛苦在自身之中(in-itself)有承受痛苦的自身(the
Self)。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在與世界語言根本不同的量度上重新思考「如何」這一問題。哭泣正是痛苦的言說方式,它是?在生命的表達,它完全不同於「我處於痛苦中」這樣一個語言學命題。初看起?,哭泣具有現象學的雙重特徵:哭泣一方面是外部空間中的回音,另一方面是痛苦的原初開啟,但經過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儘管我們的身體對這種回音是開放的,但這種回音只不過是事後被加到這個開啟之中。回音和開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言說模式,雖然這兩種語言都在同一種單純的哭泣中言說,但只有後一種語言才是哭泣的真正的言說方式。
哭泣是身體語言,它是痛苦對自身的訴說,它訴說?肉身的痛苦,生命能?無比清晰地聽見這種哭泣的聲音,但不是通過回音。它哭泣?,同時它體驗到這種無聲的聲音。這種無聲之音就是生命語言,「每一個生物在生命的第一次戰慄中都已經聽見了這種生命語言,就像我,我總是能聽見我出生時的聲音,這種聲音就是生命的聲音,在這種無法打破的沉默中,生命語言不斷地向我訴說?我自己的生命」 。
生命語言原本是屬於受苦者的語言,但是也應是巫者緩解生命憂苦的底蘊,我永遠記得我學生家裡發生的一件事。那是三十餘年前,當她還是五六歲的時候,她七歲的小表哥被蛇咬死。當時,她表哥與祖父母住在一起,孩子的父母則遠赴他鄉打拚。孩子沒跟過去,一方面是祖父母捨不得孫子,一方面是年輕父母出外掙錢,生活不易,能由祖父母來照顧可說是一舉兩得。
但是當這蛇咬事件發生之後,全家傷心之餘,卻扯出更深層的痛苦。原來孩子的親祖父很早就過世,祖父的好友來陪伴傷心的寡母,寡母在喪夫之後要養兩個稚兒,生養難繼,就再嫁丈夫的好友。寡母為了讓繼夫能專意扶養前夫的兒女,遂將子女的姓改為繼夫的姓。而孫子不幸意外過世,鄰舍即傳言祖母當年為子女改姓,有奪前夫子嗣之嫌,前夫怨氣不能消,所以來索命。
這個惡毒的傳言使得祖母百口莫辯,鬱鬱寡歡。直至有一天,祖母全家到石壁部堂牽孫子的亡魂,師姑附體之後,告訴阿嬤,這不是她的錯,天庭只給他七年的陽壽,所以本來就是要走人,跟奪嗣傳言無關。此言一出,老阿嬤老淚縱橫,一樁無底洞的罪惡感頓時消散。
這些意義生成事件來自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來自人類切身的體驗,當我擠身在乩童的堂口,我比較能看到深沈的痛苦,而在醫院反而有種希望的矯飾,有種無法直逼痛苦的炫光。所謂痛苦,往往是超過人能想像的「不可能」的實現,包括令人恐慌的「逆料」,無法擺脫的苦惱意識,於是人們追討著「啟示」、「指點」,這正是巫者與求者接壤之處,雖然「辦事語言」好似把求者的難題加以解答,我們卻須更重視巫者的身體搖晃之間的逃逸路線。所謂「逃逸路線」指的是,巫者往往並不直接回答求者的問題,而是以一種隨興的「亂談」作為說話的靈感,而一些前符號可能的「破綻」會以「非」的方式提供巫者靈感,而這樣的過程本來就是意義從無到有的自然過程,卻經常被誤識為「強掰」。
相對於巫者,求者本身也被誘導墜入非現實的時空,在那裡亡者栩栩如生,宛若一切如過去的歷史時間,關係也彷彿如昔,這是惦念空間,也是夢幻空間,更是縈繞人心的空間,在這非現實的空間,生者與死者再度見面說話,虛空的真實立現,反而顯示現實的虛幻。人們在非現實空間的感情反而更為真摯,我曾見一病婦在台南城隍廟牽亡,乩童由過世的婆婆附身,只見兩人大聲互罵,然後和解,長達一個多小時,好似一齣舞台劇的內心戲。許多話直來直往,其中不乏現實的爭執,媳婦淚眼婆娑,一方面覺得婆婆以上欺下,過分霸道,一方面又顯示自己也不怎麼孝順,反抗在心。幾經爭執,終於和解,婆婆答應放過媳婦,但須依她幾件事,其中不外是改風水修墳頭等象徵事宜,只見病婦歡喜求去。人在非現實空間裡,事情反而容易解決,主要是恩怨情仇容易滑動,並不似活著的現實容易打結,而且人在非現實容易有自由的氛圍,不似現實繃得那麼緊。
因此,在我們的研究看來,巫宗教的療遇剛好就是巫者為求者建立非現實作為內心複雜心緒的舞台,而非現實剛好提供求者自由的空間,他們可以透過記憶進入惦念空間,也可以透過夢魂縈繞進入夢想空間,甚至巫者的附體也提供了虛擬的對體,讓對談的話語獲得實現。所有非現實空間的自由正是療遇(healing encountering)的元素,只要能夠引入,所謂心靈療遇的條件即以俱足。
另外,巫宗教做為信仰圈的療遇網絡,則是透過多重自我的界定(三世因果故事)追求「我是誰?」的多元空間,將人間現實的關係模糊化或多重化,例如現世朋友在前世被界定為兄弟或夫妻,使得現世的身分被三世因果的關係所重疊,彼此的關係有實有虛,既相連又分離,構成一種非常立體的交互性,而不會只陷在角色關係的平面上。這是在現實加上非現實的因素,使得現實的苦難不會那麼令人窒息。而當一個有限的信仰圈在巫者的「三世因果」的繪聲繪影之下,往往滑順地形成某種擬似家族的社群,彼此以家人相稱,而成為潛在的療遇網絡。當然,這種療遇網絡隨著生活情事的發展,也有可能增強擴大,也有可能分崩離析。
我相信西方植入式心理治療的本土化過程中,必定能從本地的巫宗教獲得啟發,特別是對非現實的開發。西式心理治療面對東方子民總有削足適履的格格不入,本書的一些反思或許有助於華人心理治療的本土紮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