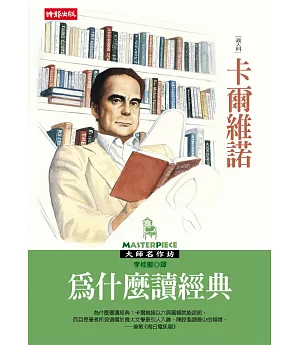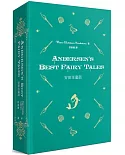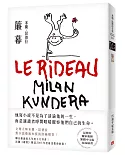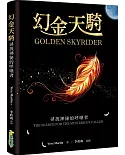寓言魔法師鑄造後現代乾坤——翱翔卡爾維諾的綺麗世界
.南方朔
1985年,當卡爾維諾逝世時,他仍在寫最後那本《在美洲虎太陽之下》(Under the Jaguar Sun),他要把五種主要的感覺藉小說而呈現。讓人遺憾的是,他只寫完吃、聽、嗅三覺,留下了無人可以彌補的缺欠。而這時他只不過六十二歲。
單單以卡爾維諾寫吃作為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想像是如何的奇幻有致。一對夫婦到墨西哥旅行,由異國的食物和佐料,早期的以活人獻祭的儀式,而推論出愛慾的本質即是相互的啃嘴撕裂與吞嚥。吃或被吃竟然可以寫到如此的深入程度。
而這就是卡爾維諾——當代最奇特,想像力無法揣度,而又不斷替小說尋找新邊疆的卡爾維諾。在他的小說世界裏,電子、原子、分子等無機物可以談戀愛,青蛙恐龍的人格化被賦予歷史哲學的奧義。故事裏的人可以被切成兩半,各自衍展出不同的情節,甚至紙牌也可變身成了主角,人的感覺可以藉著角色的設定而被擬人化……。卡爾維諾的想像世界從來不曾在任何一處作長久的停留。他的父親是長期在加勒比海地區服務的農藝學家,他誕生於父母即將束裝返回義大利的那個驛馬星動的時刻。卡爾維諾後來自剖道:「或許這個未出生的經驗影響了我的一生,我一直追求外國式的神奇。」不止他的小說世界裏,「主角」的可能性被極大化,在實體上,他的小說地無限的向每個領域伸展。他用小說講今古混同的寓言,用馬可瓦多這個虛構諧趣的小人物來探索現代都市的荒誕以及人對自然的追求,這是喜鬧諷刺的小說。除此之外,他還用小說來呈現宇宙的創生和物種的進化,用小說來闡釋符號語意學和歷史哲學。他的小說是各種不同寓言所組成的辭書,這些辭書編織成複雜變幻的意義網路。卡爾維諾也自剖的說過:「所有的小說都起源於傳奇和寓言,它們組成了影像,影像堆疊出意義的網路!」
因此,卡爾維諾用小說來講故事是一流的。他的作品總是予人意外的驚喜!「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的寫!」而他無論以任何形式來呈現,他的作品總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我們義大利的寓言故事總是在談愛與命運。」
而真正讓小說研究者驚訝的是,近代的小說家們總是嘗試著要從古典寫實主義的桎梏下獲得解放,「意識流」打破了時間的桎梏,寓言式的筆法打破了空間的限制,但「作品」與「作者」的相連不可分卻是終極難解離的孿生嬰,這是小說可能的最後枷鎖,而60年代末以後,與當代法國主要作家思想家合組「未來文學研究組」,每月在巴黎集會一次,為該「研究組」要角的卡爾維諾卻以他的超級想像力這樣的設想:「我可以寫一本被火燒掉一半的小說,「我」乃是「我的小說」的負擔,我一直在思考,當「我」不存在時,「我」將如何寫作。」他的這個想法,後來即蛻變成《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早已成了「後現代小說」的新經典,它的意義,也被不斷解釋,而最真切的意義或許是「當我不存在時,我將如何寫作」這個最基本的命題,因為它是近代文學中「作者」將自己解消掉的首次嘗試。
閱讀卡爾維諾的作品是一種空前的愉悅。他的作品絕不艱澀,他也從未用大河式的滔滔文字來驚嚇讀者,相反的卻是,他的作品幾乎可以說都是寓言或傳奇,在簡短的空間裏承載高度想像的模稜內容。卡爾維諾自己說過:寫作是一種視野,拉得愈高,也就愈能看見真實。他自己也曾論說過純屬幻想的《格列佛遊記》絕不比巴爾扎克的寫實小說更不真實。卡爾維諾的超級想像力是真實的。他畢生最推崇的小說是史蒂文生的《金銀島》,認為它好看,有想像力,令人快樂。由他喜歡《金銀島》這件事,其實已為它的想像力作了注腳!除了《金銀島》之外,他最推崇的詩人則是悲觀的義大利象徵主義詩人蒙地利(Eugenio
Montale)。想像超級發達,不斷為小說的各個面向探索新的邊疆,而自己則反覆在愛、命運、歷史等最基本的地方探尋它的蒼茫,這就構成了卡爾維諾的全部。
近代作家裏,寫實作家由於突出作為作者的「我」,多數是自我意識強烈的理性主義者——不論他們相信的是那種理性主義。而著重象徵感覺者,多少難免有些紈性格。而「後現代作家」則因祕思神話的一定排除,經常依違在犬儒嘲諷和洞明世事的睿智與豁達蒼茫之間,而毫無疑問的,卡爾維諾乃是後者——他曾是義大利共黨黨員,1956年匈牙利革命後退黨,但他說:「我仍是左派,只因我不願成為右派,這乃是我們這種老輩的忠誠。」「我不是改革者,因為有太多壞的改革,因而我不再相信它。」這種對現實政治社會事務的逐漸冷淡過程,遂有了他逐漸發展為以想像力為主體的創作生涯。根據他的想像發展過程,卡爾維諾的創作大體上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47年的《蛛巢小徑》,它是自身二次大戰期間經驗的重述,屬於「新寫實主義」的黨派性作品。但卡爾維諾旋即放棄了這種創作方向。
第二階段為50年代,對黨派性活動趨向冷淡後的卡爾維諾倒回到義大利的寓言傳統之中,將寓言以奇幻怪誕的方式呈現。「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屬之。《分成兩半的子爵》所寓意的乃是冷戰結構下分裂的世界,《樹上的男爵》則有自我影射的含意——它等於卡爾維諾日益脫離政治黨派化活動的宣告。
第三階段乃是60年代,它以《宇宙連環圖》和《零時間》(T
zero)為代表,這兩本心書裏Qfwfg乃是許多篇章的敘述者,它是電子,原子等無生物,也是軟體原生動物,兩棲動物等生物,整個宇宙的形成與進化被擬人化,而在擬人化的過程中又被賦予哲學討論的意義,情愛的滄桑,歷史的茫茫以及命運的變化等都被鑲嵌了進去,它們是卡爾維諾最具可看性的作品!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瘋狂般的喜好,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的!原本即專攻科學的卡爾維諾,將他的物理學和微積分,生物學搬進了小說之中。
第四階段乃是60年代末期之後,他的思想接上了法國的結構與後結構主義,尤其是羅蘭巴特。《如果在冬夜,一個放人》,《看不見的城市》,《帕洛馬先生》等作品皆屬之。它們有許多都可以用羅蘭巴特的學說來加以詮釋。其中,最讓人喜愛,充滿了語意符號學奧義的乃是《看不見的城市》與《巴羅馬先生》。《看不見的城市》說的是城市,兩寓意的其實是人類文明的總體形相,《帕洛馬先生》則是一種自省,關切的是人世、時間、空間等一切的終極。在這兩本小書裏,想像和智慧凝結成深刻的歷史洞識,至少對個人而言,不曾讀過那麼耐咀嚼的文學作品。多年前從《看不見的城市》裏首次接觸卡爾維諾,或許別人不會相信,那本書的英文版個人竟反覆看了三次!
卡爾維諾的作品是好看至極的寓言,想像力游移且豐富,什麼樣的腦袋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他是公認的戰後義大利最傑出的小說作者。他的逝世,不但對義大利人,甚至對世界文壇都是一種震驚。他逝後,遺孀艾瑟(Esther Calvino)陸續將遺稿以及從前未曾結集的舊作陸續出版,九四年初新出的是五篇回憶文章組成的《到聖喬凡尼的路上》(The Road to San
Giovanni),聖喬凡尼是年幼時他父親農場的所在地。一個書評者在評論此書時,劈頭一開始就說:包括卡爾維諾在內的數名作家近年來未享長壽即逝世,留給義大利文學的空檔還未恢復。一個才情傑出的作家之死,是不可能恢復與彌補的缺憾。在近代文學裏故事講得好的多矣,形式創新者多矣,然而能將事務的關係、世界、命運、文明等請到深刻的卻如此稀少,許多作者可以被忘記,而卡爾維諾則註定是會被愈來愈記得的少數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