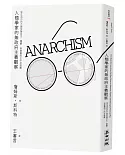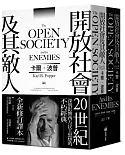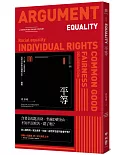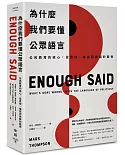更易了解的東方霸術
東西方的連貫性
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
這是馬基維利於公元一五一三年完成的《君王論》(The Prince)所闡述的政治原則,他大概想不到,往前推溯到一千三百多年前,中國歷史的三國時期,就有人與他抱持著相同的主張。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魏太祖曹操在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出這樣的一句話。
曹操與馬基維利生存的時代雖然相去有一千多年,但若是仔細觀察比較,就可以發現他們身處的整體環境是如何相似──同樣的烽煙滾滾,同樣的君暗政亂,同樣的天愁地暗。
有幸的是,他們都是抱持著完全熱情主義的「革命鬥士」,就像希臘羅馬神話中為人類盜火的普羅米修斯,高舉從太陽那裡點燃的火炬高喊:「現在,雖然脆弱和短命,但人類有了熊熊的火,並由此學得許多技能。」
兩人都經歷過一段晦暗無光的日子,也曾失意地過著隱居的生活,但不論如何受到何種現實的壓迫,他們從不忘記對政治的熱情,把一生的心思都放在征服更遠大的目標上;可卻又何其不幸,他們最後還是逃不過天神的譴罰,長久以來,兩人都遭受到極大幅度的誤解,除被形容成是玩弄權謀的人之外,無比豪情壯志換來的卻是一身罵名,他們的惡名昭彰,簡直與魔鬼等量齊觀,而應該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的事實則無情地遮蓋住,這是不公平的!可惜到了今天,我們依舊不能完全理解馬基維利,同樣地,也偏視了曹操。
馬基維利所著的《君王論》原文不過四十九頁,可四百多年以來,其中的思想受到世人的輕蔑與指責,更由於歷代的獨裁者或暴君,像是拿破崙、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推崇,所以「馬基維利主義」也被視為邪惡、陰險、狡詐的代名詞;這些自稱是馬基維利信徒的暴君,所掀起的一時浩劫,並不是馬基維利的錯,在我們單向遷怒馬基維利的同時,我們不該忽略,馬基維利在政治現實環境打滾後,被拋擲到遠離塵世的地方,仍然心繫國家的存亡興廢,念茲在茲的是拯救祖國免於分崩離析,人民脫離水深火熱的悲慘境遇。
而曹操也有許多人評論過他,像是陳壽、唐太宗、宋真宗、司馬光、辛棄疾、章太炎、胡適、毛澤東、魯迅等人都曾提出不同的見解,其中褒貶不一,若以時間來區分,唐代以前褒揚者多,宋代以後貶詆者眾,大體歸納起來,盛世時謹防他,亂世時則要抨擊他;曹操的真實形象,被扭曲得最徹底的是在元末明初之際,小說家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中,他被塑造成心術不正、偽善背信的奸雄形象,讀完整本小說可以清楚意識到,無不指向曹操遵奉「未達目的,不擇手段」人生哲學,而一句「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評語和南宋詩人陸游「邦命中興漢,天命大討曹」的詩句,更是把他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牢,從此難以翻身;但我們對於曹操「歌以詠志」的情懷,以及「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的積極作風,如何能夠視而不見?
政治的目的是為一時?還是千秋?自來眾說紛紜,各持己見的多有,但我們必須承認,在曹操與馬基維利那個紊亂的年代,若連一時都掌控不住,何來千秋可言?經過幾世紀的思想改革、洗滌之後,他們終於都獲得一個平反的機會,雖然事實本身不會為自己說話,但如果我們對曹操與馬基維利都存在好奇的想法,推敲起來,這兩個人在各方面竟是那麼地相似,相似到可以互相連貫。
時代造就他們必須化身成現實主義者,然而更進一步分析起來,兩者之間還是有所差別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馬基維利最後成為君王霸術的理論者,而曹操則是徹底的實踐者。
東西方的差異處
馬基維利出生在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亦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鼎盛時期,人們從教會的權威和集體社會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阿爾卑斯山以南的義大利半島,正經歷一場心智的洗禮,人們正以旺盛的好奇心,攬著古典文化的遺澤,重新發現凡俗世界的光榮,以至財富、權力、藝術、文字、思想和學術的發展一日千里,許多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都在那時候湧現出來,像是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但丁、薄伽丘等等,馬基維利在這樣生氣蓬勃的新城市社會中長大,使他後來的思想中含有很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為何東方從未發出類似文藝復興運動那樣的光芒?我們唯一可以審視的,便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這堪稱是中國古代學術最發達的時代,也是中國哲學史的奠基時代,出現了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家等流,有如百川匯海、大鳴大放,也各有其代表人物,可是除了儒、法、道的思想尚能流傳至今,其餘流派已經落入葉枯枝折的窘態,無法像文藝復興運動那般結實纍纍;其中最大的差異,是西方思想的躍進來自自我意識的覺醒,乃相當強烈的動力,而造成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普及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世守的王官分散到各諸侯國,官府所藏的典冊也就散到各處,打破學術由貴族獨占的局面,因此兩者之間的本質原就不同。
中國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都是處於一個完全封建的狀態,個人的價值幾乎不受重視,帝王以禮儀代替律法來統治廣大的人民,所以不論政權或朝代如何更替,演進的腳步顯得遲緩,甚或是不動及退縮;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因為古中國的地理環境較為特殊,北有茫茫的戈壁沙漠,西有巍巍的峻嶺高原,東南都是洶湧的大洋波濤,這是一個幾近隔絕的封閉狀態,與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等幾個古文明的發源地大不相同,中國文明是完全獨立發展的;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不堪一擊的,就像沉醉在鄭和下西洋的榮耀之中,卻不願正視歐洲大發現時代背後帶來的影響,極力讚美鄭和寶船隊的浩大,卻對巴托羅繆‧狄亞士的三桅帆船露出鄙夷及不屑一顧的神情,這都是相當負面的看法。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經歷過封建君主專制的歷史階段,可是,當西方封建專制的結構鬆動且氣息奄奄之時,中國還停留在「朝見長跪,夕見長跪」的狀態,當西方以相當快速的步伐在變遷的時候,中國仍舊在自己建構的世界中躑躅獨行,不肯覺悟。
我們只能說,中國人花在禮儀設定上的時間太多,而用在學習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而在一千多年前,曹操就看透問題的存在,他提出要以法家的思想為依據來統治國家,不過他卻被打擊成視禮教於蕩然的荒誕人物,真是令人扼腕!
個人提出這樣的論點,只是希望我們應該從東方的角度出發,盡可能以絕對開放的態度,去汲取西方的思想,並非停留在思想的主要目的是勸善懲惡的階段,不再當個孤傲卻支離的巨人,自絕於進步的挑戰之外,而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中,付出高昂的代價。
如何閱讀這本書
如何了解歷史的真實型態?十二世紀基督教思想家耶阿素(Joachim of
Fiore),利用分析歷史的資料再重新整合,繪出一幅<歷史之樹>,使人易於理解歷史體系,此樹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聖父(律法與懼怕的時代)、聖子(恩寵與信心的時代)、聖靈(愛與自由的時代),而樹幹旁邊衍生的樹枝,則是代表重要人物與事件,這幅畫雖然帶有神學結構的意味,但不失為從旁枝末節去窺究歷史進展的好方法,這是非單軌的循環式歷史觀。
要明瞭過去才能決定未來,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事情,包括那些在這個舞台上登台過的人物,是人類活動最主要的指標,藉著歷史,人們可以評價了解生活的一切,這是歷史有價值的一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受到戰爭引發災害的刺激,使他們重新反省日耳曼與歐洲文化的價值,他們所用的方法,就是從歷史的過程中去尋找他們要的答案。
我們不能回到曹操或馬基維利的時代,像科學家一樣觀察、研究他們,只能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生平事蹟與斷簡殘編中,盡量客觀又心平氣和的描述他們的信念、思想及感情;在閱讀曹操和馬基維利之時,必須秉持一個觀念,那就是不能站在現代的角度斷其是非,就如同不能以現今的道德觀念,去批判孝莊文皇后為何下嫁她的小叔多爾袞一樣。
通常,只要論及曹操和馬基維利這兩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時,重點無不擺放在是否還他們一個本來面貌的題目上,然個人粗淺認為,何需還他們兩人真面目?他們只是被模糊化而已,而歷史的真相可是從來都沒改變過的啊,了解他們的想法並獲得啟迪,遠比還他們真面目重要得多了;還他們一個本來的面目這樣的方式是激動的,我們必須很沉靜的去端看,才能省思。
德國史學家梅內克(F.Meinecke)說:自有《君王論》以來,西方政治學便挨上了致命的一刀,其傷口或許是永遠都難癒合的。雖然我們很難去了解他們的痛楚,但西方的問題一樣存在於東方,所以便採用適合東方思考模式來詮釋君王霸術;本書的設計是從兩人的生存背景談起,旨在將他們的思想與作為介紹出來,期望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對待他們,而不在以善惡的觀點去衡量,也不在拔高或誇大兩人的歷史定位;歷史事件沒有所謂的對錯,所以我們別把曹操當孔孟,而馬基維利寫的也不是《論語》,換句話說,假使我們不曾偏頗地看待韓非與《韓非子》,也不應該去斥責曹操和《君王論》。
本書以馬基維利的《君王論》與他的思想為基礎,曹操的作為呼應對照,用比較接近東方思考的格局來編寫,除了第一篇是獨立發展外,其後的幾篇都是理論與實踐雙頭並進,旨不在提供方法讓人學習,而是展現精神以供思索;思想的傳輸最忌諱僵硬的教條模式,唯有潛移默化的力量才是最顯著的,本書其中一則則的故事只是引人容易閱讀的手段,它所引申出來的道理才是精髓所在,如有覺得不妥之處,望各方先進見諒並不吝給予指正。
個人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搜尋資料,加以整理,並編寫完成,書中有理論分析,也有生動的歷史範例,涵蓋領導、決策、軍事、用人等面向,給想要成功的個人看,給企業經營者看,也給喜歡歷史的人看。
朝夕與書中的曹操和馬基維利相對,不由得對他們生出感情,恨不得把他們的思想全部耕耘出來,希望讀者能從字裡行間了解我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