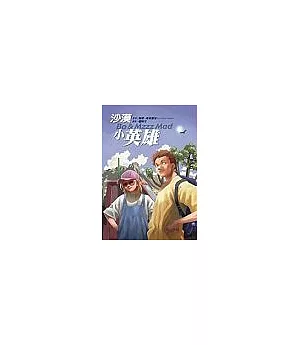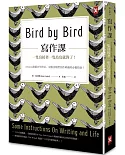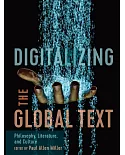如臭豆腐般迷人的
說弗萊謝曼之前,先忍不住要來說個小插曲。我先生從小就是逐臭族,他為臭豆腐全省吃透透,最後評語是有個經常推車子到家門口的老婆婆臭豆腐,是最香最臭最脆的。老婆婆很老了,賣臭豆腐是興趣,無關生計。後來先生長大出國去了,在國外心裡惦惦念念的,除了父母外,就是這位老婆婆的健康。每次回國,他就騎著車到處去找老婆婆的攤位,去看看她,也吃幾盤臭豆腐。後來老婆婆過世了,最傷心的當然是她唯一的兒子,但我們家老公也難過了好幾天。好吃的臭豆腐當然不會隨著老婆婆的遠去而失傳,但老公說,最香最臭最脆的臭豆腐卻再也沒有了。
香、臭、脆,是極品臭豆腐,用來形容弗萊謝曼的小說,卻也超級恰到好處。香,靠歲月熬泡出來的臭豆腐,多了股化學臭豆腐所沒有的香。弗萊謝曼今年已經八十幾歲了,他不但人生閱歷多采多姿,更擅長藉別人的經驗為經驗,將報上讀來、耳朵聽來千奇百怪的新聞奇譚化作小說主旨,寫出出神入化如《挨鞭童》(The Whipping Boy,智茂出版)、《沒有月亮的晚上》(Bandit’s
Moon,幼獅出版)這樣兼具歷史紀錄與流利好讀的少年小說來。
臭,弗萊謝曼在小說中角色的挑選真正與臭豆腐的臭有異曲同工之妙。海盜、痞子、流氓、搶匪、大盜,這些一般少年小說作家難得去碰選的人物,都曾一一個性十足的活躍在弗萊謝曼的作品中。每個故事中主角也許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是沒有人能在讀過他的故事後忘記像《豔陽下的鬼》(The Ghost in the Noonday
Sun,幼獅出版)裡的查喳船長、南瓜燈,或是《沒有月亮的晚上》那恐怖的瑪麗OO及盜亦有道的蛙金。這些角色使弗萊謝曼的文字散發一股牢牢吸引人的異香,讀者便如逐臭之夫一樣的追逐著這少年小說中的臭豆腐而去。
脆,弗萊謝曼的作品有長有短,完全視需要而定,做到增一字則太肥,減一字則太瘦的程度,讓讀者閱讀起來清脆有聲,餘味無窮。使弗萊謝曼一舉成名的《挨鞭童》,可能是所有紐伯瑞金牌作品中最簡短的一本;《沒有月亮的晚上》以及這本《沙漠小英雄》也一樣是篇幅短小、沒有冷場的動作派作品。
弗萊謝曼出生紐約布魯克林區,卻從小在加州最有海、有山、有沙漠的聖地牙哥長大。從小學五年級開始,弗萊謝曼就立志要當個魔術師,也從青少年時期就在魔術師俱樂部、表演團體出入演出。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聖地牙哥報社找到了工作,由於這份工作弗萊謝曼才發現自己原來很喜歡講故事,也有講故事的天分。
剛開始創作時,弗萊謝曼的對象並不是孩子。但在成為專業作家後,年幼的孩子不懂這個爸爸怎麼都不必像別人的爸爸一樣出門上班呢?為了讓孩子明白他的工作,弗萊謝曼決定提筆寫出一本他的孩子會懂的小說,免得孩子老是以為他是無業遊民。這一小小岔路,沒想到竟為弗萊謝曼彎出了一條嶄新的人生方向,也讓他以魔術師兼作家的雙重身分為兒童文學注入一股動人的魔法。
這本《沙漠小英雄》的故事發生在離聖地牙哥不算太遠的沙漠裡,我在聖地牙哥已經居住十年了,對於書中所有地名都倍覺親切,像「二十九棵棕櫚」、死亡谷、「短葉絲蘭」這幾個地方都很熟悉。在翻譯時我曾掙扎這樣不像地名的地名要不要照意義直翻,但想想,這樣的地名便是這附近沙漠的特色,捨棄了沙漠風味,這本書便少了許多丰采。因此即使讀者可能不太適應這樣的地名,但試著去想一下這地名暗示下的地方歷史、風情、環境、人文,便會發現這樣生動的一個名字所帶來的想像真是無止無盡、趣味無窮的。
從十幾年前第一次讀到弗萊謝曼的《挨鞭童》去找資料時,他就已經是個留著灰白大鬍子的老人了。我花了一陣子時間讀他之後,便盼著他繼續出新書。有時隔個幾年不見他新作品,心中就會想起老婆婆臭豆腐的故事,深怕現在已經八十多歲的這位老作家也要離開兒童文學界了,所幸的是至今弗萊謝曼一直還是精力充沛的在為少年小說耕耘。從《沒有月亮的晚上》到這本《沙漠小英雄》,再到2003年剛出版尚未翻成中文的《Disappearing
Act》,中間都不算相隔太久的時間,而且本本依然維持他一貫帶著江湖味的風格。他小說中的孩子幾乎都沒有父母,主角只有十出頭歲,不管流浪街頭還是被海盜騙上船,不管是跟萬惡不赦的流氓結成同夥,或是獨自一人一招半式闖江湖,這些孩子都得在沒有其他大人的諮商或幫助下,獨立靠著睿智、道德,勇往直前的去走他的人生路。
讀著他的書,相信讀者都會跟我一樣在心裡祝福這位作者長命百歲,越老越香、臭、脆。好看的少年小說當然不會隨著弗萊謝曼的遠去而失傳,但萬一有一天他走了,我會說,最香最臭最脆的少年小說也就再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