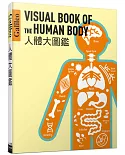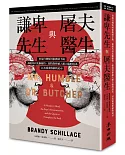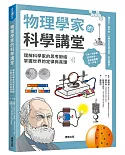許多人在還未熟稔後現代的語法操作之前,就早已經習慣引用「Anything Goes !」來表現後現代的嘲諷精神了,然而,費爾阿本德卻始終未曾被國內學界所熟悉。
許多人在談到當代以來社會科學界之轉折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述Kuhn的「典範」與「不可共量」,但是,卻少有人知道,早在一九五八年《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之前,費爾阿本德就已經提出詮釋觀察的語言會隨著理論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費爾阿本德,這位科學哲學界的壞孩子,使盡渾身解數試圖嘲諷一切自抬為無上綱領的科學聖說,力倡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無政府主義。在強調科技社會風險反思的今時,讀費爾阿本德是對於科學優先性所進行的一種知識論的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