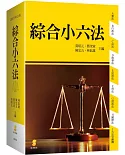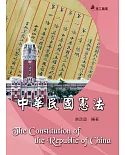序一:
口供主義‧罪疑唯重
柏楊──台北少數崇拜口供主義的司法官員,正在企圖用別人的血,灌溉「罪疑唯重」的野蠻文化。
我們家鄉有一句諺語說:「屈死不告狀!」簡單的一句話,道盡了中國人宿命的悲哀,一旦興起訴訟,猶如肥羊投入餓虎之口,禍福難料。民事案件往往家產蕩盡,刑事案件除了家產蕩盡之外,更加上伏屍刑場。法院是一個保障大人物利益的地方,哀哀小民是注定被草菅的對象。五千年來的訟獄,建立在口供主義之上,因為聖明的帝王,懷著大慈大悲的心腸,小民如果自己不承認犯罪,絕不處罰。所以,怎麼要小民自己承認犯罪,也就是怎麼樣能使小民「坦承不諱」或「自動招認」,遂成為執法官員最大的考驗,迫使他們不得不苦刑拷打──「苦刑拷打」是我們小民的語言,暴官酷吏的語言稱之為「幫助你喚回記憶」。白色恐怖時代,我被捕的第一天,曾問調查人員:「我犯了什麼罪?」他說:「台北街頭那麼多人,為什麼我們不逮捕別人,而逮捕你?你應該知道原因。」我說:「我不知道。」他微笑著說:「沒有關係,我會幫助你知道。」在他的幫助下,我果然知道了。於是,他寫下筆錄,我寫下自白書。筆錄與自白書,是口供主義的兩大支柱。一直到二十世紀,可憐的中國人,仍陷在口供主義的黑洞之中。一個冤枉的人被逮捕,只要暴官酷吏傳出訊息說:「他承認了!」大家的懷疑就會戛然停止。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犯罪,他既不瘋,也不呆,怎麼會承認可能置他於死的罪狀?直到我入獄之後,才知道你如果承認暴官酷吏所預設的罪狀,你就是一個合作的囚犯,你的伙食中,每天可能吃到一碗牛肉麵,然後雙方都皆大歡喜的把你送進監獄,或送到刑場;如果你不合作,他們只好幫助你和他們合作,政治犯固然如此,刑事犯尤其如此,沒有人能逃出災難。二十世紀來臨後,法律精神和立法條文,同時屏棄口供主義,改採證據主義。但是,醬缸文化威不可測,證據主義遂被醬成了美麗的條文,專作對外宣傳之用:「我們是科學辦案,證據第一!」但是腦子裡發酵的,仍是口供。為了天衣無縫,我自己的自白書,就被迫寫了七次;口供筆錄,調查員至少也自動寫了四次。直寫到吻合他們虛擬的實境為止。寫了這麼多,不是為我自己控訴,我已接受國家元首的公開道歉,和法院判決的冤獄賠償,而是要為台灣三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控訴!現在,他們在口供主義下,命在旦夕。一九九一年三月,台灣省台北縣汐止鎮,吳氏夫婦被砍殺身亡,警察不久就逮捕到真兇王文孝。王文孝在警察多方「幫助」下,承認他還有一個同謀,那就是他的弟弟王文忠。之後,王文忠在「幫助」下,供出了連王文孝都不認識的上述的蘇、莊、劉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又在同樣「幫助」下(用打火機燒下巴;倒吊灌尿水、辣椒水;以鐵鎚隔著電話簿捶打胸部;以電擊棒電擊下體,燒焦之後再為其擦上綠油精;脫光衣服坐在冰塊上,再用大型電風扇吹他;脫光衣服綁在椅子上,然後在水濕的地板上以電擊棒導電,讓被告背著椅子在地上跳等等),他們全部「自動自發」的寫下了自白書和完成了筆錄。他們從來沒有和王文孝對過質,王文孝也從不認識他們。一九九二年一月,王文孝被槍決,臨死前,他為這三個他從未謀面的孩子呼冤。他連自己的親弟弟都供出來,何況這三個從未謀面的年輕人?但是,大獄已成。一九九五年二月,最高法院對這三個孩子,各判兩個死刑。同月,檢查總長提出第一次非常上訴。三月,最高法院第一次駁回非常上訴。同月,檢查總長提出第二次非常上訴。四月,最高法院第二次駁回非常上訴。七月,檢查總長提出第三次非常上訴。八月,最高法院第三次駁回非常上訴。直到一九九九年九月,經歷再審申請遭駁回、辯護律師抗告數回合後,最高法院撤銷原裁定發回高等法院。今年(二○○○),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五月,最高法院突然一反過去的立場,裁定通過再審聲請。同月,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也突然一反過去的立場,對再審提出抗告,再審希望破滅。問題就在這裡,最高法院判決的合法性,不但遭到檢查總長的再三質疑,三度提出非常上訴,十年來,歷屆的法務部長馬英九、廖正豪、城仲模、葉金鳳,全都感到判決有瑕疵,而拒絕批准死刑的執行。而監察委員張德銘,也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最高法院判決的不當。現在,最高法院總算批准了再審的聲請,可是曾經提出三次非常上訴的檢察體系的檢察官,反而反對再審,提出抗告。匆匆幾個月過去了,抗告既沒有駁回,再審的裁定也沒有終止,這不但是一種諷刺、一種荒謬,而且還有一種陰氣森森的詭異。「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土石巨流,正在咆哮翻滾。使我們感覺到,這三個孩子命如游絲,勢將死在這種巨流之下。我認為,如果我們小民們傾盡了全力,還不能挽回一個明顯的疑獄,那就讓三個孩子死吧!因為他們是卑微的小人物。口供主義的幽靈,一直抓住國人的頭腦不放,我保證:將來同樣的悲劇,會不斷發生,發生在你我孩子們的身上,因為,我們也是卑微的小人物。這三個孩子,或許是真兇,或許不是真兇,我不敢確定,那是專家的事。但有一點卻是敢確定的:專家們的看法並不一致,甚至相反,而民間的輿論,大多數同情三個孩子,說明這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刑事案件,我們的老祖先,遠在二千年以前,就為這類事件,提出公平的裁決,尚書‧大禹謨:「罪疑唯輕」,對有爭議性的訴訟,應從輕處理。想不到二千年後的今天,就在台北,雖然疑點重重,卻仍然有人堅持非要索取那三個孩子的性命不可。我們傳統文化中,少有的優美部分,不但沒有發揚光大,反而日益墮落。幾年前,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被判無罪。有人向辯護律師提出質疑,律師說:「我從沒有說辛普森沒有犯罪,我只是說,我們沒有辛普森犯罪的證據。」我們同樣指出:「我們從沒有說這三個孩子沒有犯罪(僅受刑不能證明沒有犯罪),我們只是說,我們沒有這三個孩子犯罪的證據。」我們面對的是:台北少數崇拜口供主義的司法官員執法者,正在企圖用別人的血,灌溉「罪疑唯重」的野蠻文化,使它成為罪惡的磐石,使人忍不住酸鼻!二○○○、八、一八‧台北
序二:
期待改革司法 蘇建和
生在台灣,活在民主時代,憧憬人生至少也應在平凡樸實中度過吧!然而我卻是在失去自由、含冤莫白的人生中流逝青春,當司法踏著我清白的身體高喊它們是公正的,可曾真心想過因一時的草率,讓多少人受苦受累,其中的心碎是否多少能體會些。要改革司法從我這小小人物說出,可能很奇怪,但在我遭受司法的不公後,我更應說出改革司法是刻不容緩的事,真的不願再看到別人也受冤了,而走向黎明的朋友們也正為促進司法改革而努力著,我真的衷心感謝也好感動,社會各階層的正義人士們無畏風雨的為了心中的理念而辛勞著。或許有人並未能感受到這樣有什麼用,但我卻能清楚的感受到司法想進步,也正撼動著司法人的心,只要心不死,我深信公平正義的司法終將到來。屆滿九年的今天,自己冤屈雖還未能昭雪,但我還是會照顧好自己,堅持等待下去,想著家父與律師及大家的辛勞,願一切的辛苦與努力將能換得美好未來,再也見不到不公、不義之事,也願您們安康如意。
前言:
無辜的青年要回家 顧玉珍(台權會秘書長)
嗨,您好嗎?是的,這是寫給您的一封信。您就當它是意外飄落眼前的白色油桐花,刻意惹您駐足,留意音訊。時序進入西元二○○○年,相信您與我一樣,期待人類社會能向公義與幸福更邁進一些,然而,期許未來之餘,更希望終結一些過去發生、且仍在進行中的不幸與不公義。為此修書與您,邀您一起為三條遭逢死刑冤獄的年輕生命開拓一線生機,並為台灣終結一樁揚名國際的司法國恥。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死囚──這三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冤案,至今依然刺痛我們的良心與記憶──正是台灣司法不公義的不幸見證者(一般稱為「蘇案」)。一九九一年,蘇建和等三名年方十八的少年,因被警方指控涉及「汐止雙屍命案」而被起訴,自此,他們經歷台灣惡質司法體系的戕害,人權飽受侵奪,包括非法羈押、非法搜索、刑求逼供,乃至最後在違反證據法則之下,被羅織莫須有的搶劫強暴罪名,判處死刑。沒有證據,竟率爾殺人。「蘇案」所遭遇的司法暴行引起國內外各界極大的震驚,並激發一連串大規模的救援行動,至今未衰。唯恐誤判的死刑一旦執行,再也無法挽救。一九九五年,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多個民間社團組成「死囚平反行動大隊」,尋求為此案平反的機會。那些激越誠摯的救援呼聲,您必然還記得一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總部四度將此案列為緊急行動、在每年的全球年度報告中重申此案、一九九八年針對此案提出特別報告並發出全球呼籲、一九九九年總部主席Pierre
Same親筆「李登輝總統的公開信」,指出:「蘇案就是死刑可能造成不公義最好的例子。」─當時任職法務部長的馬英九明白表示不會簽下行刑命令,否則會「良心不安」。此後歷任法務部長(城仲模、廖正豪、葉金鳳)也都審慎地未簽決三人死刑。─檢察總長為此案提出三次非常上訴。─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認定高院、地院、警局處理本案有二十四點違失。─國內法學教授們召開緊急記者會,以為聲援。──數千民眾在公園街頭繫滿黃絲帶,並以集會遊行、接力靜坐的方式聲援。──多名作家親自探監,並於報端撰文聲援。這些只是聲援行動的一小部分,期間更有許多素負清譽者為其奔走呼籲,包括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天主教總主教狄剛、高俊明牧師、法律學者蔡墩銘、立委謝啟大、著名的公益人士孫越等人。當時李遠哲院長為平反運動做了清楚的說明:「聲援蘇建和案絕非寬容犯罪,而是保障無辜。」是社會各界的仗義熱血,讓他們暫免淪為槍下冤魂。然而,將近五年了,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這三個少年雖倖存下來,卻日夜分秒遊走於死亡的邊緣,忍受死刑與冤不得申的煎熬。「死不認錯的政府既不敢殺人,也不甘心放人,是打算把他們關一輩子,等到社會遺忘他們的存在。」歷經多次抗爭後,悲觀的學者忍不住下這樣的結語。算起來,他們身繫黑牢快九年了,三條人命、三個家庭遲遲等不到正義,反而是他們的苦難逼使司法面對改革的壓力,例如「刑事訴訟法」有關保障人權條款之修法。如今少年已在恐懼中成長為青年,青春早被黑牢與死亡吞噬,如果我們再坐視不理,無異於不義司法的共犯者。因此,各民間團體決議再次營救他們。一旦三人冤屈獲得平反,不只解救三條人命,對內更可重振法治正義,對外則端正台灣的人權形象。尤其正當廢止死刑在國際間蔚為潮流之時,我們只是卑微地要求:讓無辜者免於冤死的恐懼。這是一場良心之戰。所有了解此案的人都無法不關心或不作為,面對死亡與生命尊嚴的角力,誰能不動容?因此,我們寫這封信給您,邀您一同將關心化為具體行動:要求總統特赦。「特赦」是挽救司法的誤判,因為體認到任何人為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有缺失,而任何生命都不應淪為實驗的牲祭,因此特赦成為最後的救濟管道。他們三人若蒙特赦,也不過是遲來的正義──但終究是來了。讓舊時代的冤獄在新世代的期許中結束罷!生命不容誤判,不要再讓青年為不義的司法付出代價。更何況,如果定罪必須依據證據法則的話,那麼便不是他們犯了罪,而是司法對他們犯了罪。五年前,我們曾呼籲「讓孩子活著回家」,如今孩子已痛苦地長成青年,我們仍要高喊:「讓無辜的青年回家」。請將他們應有的生命及殘餘的青春還給他們,在油桐花開的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