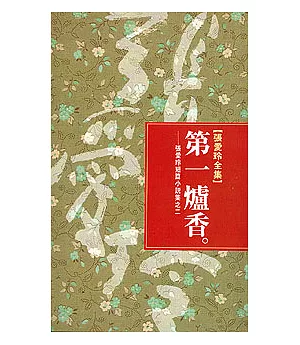第一腳踢下去,她低低的噯了一聲,從此就沒有聲音了。她不能不再狠狠的踢兩腳,怕她還活著。可是,繼續踢下去,他也怕。踢到後來,他的腿一陣陣的發軟發麻。再雙重的恐怖衝突下,他終於丟下她,往山下跑。身子就像是再夢魘中似的,騰雲駕霧,腳不點地,只看見月光裡一層層的石階,在眼前兔起鵠落。
跑了一大段路,他忽然停住了。黑山裡一個人也沒有-除了他和丹珠。兩個人隔了七八十碼遠,可是他恍惚,可以聽見她咻咻的艱難的呼吸聲,再這一剎那間,他與她心靈相通。他知道她沒有死。知道又怎麼樣?有這膽量再回去,結果了她?
他靜靜站著,不果兩三秒鍾,可是他以為是兩三個鐘頭。她又往下跑。這一次,他一停也不停,一直奔到了山下的汽車道,有車的地方。
家裡冷極了,白粉牆也凍得發了青。傅慶的房間裡沒有火爐,空氣冷得使人呼吸間鼻子發酸。然而窗子並沒有開,長久沒開了,房子裡聞得見灰塵與頭髮的油膩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