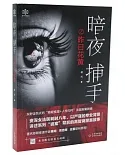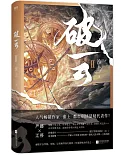本書是畢飛宇所著的一部長篇小說。書中講述:1976年的中國鄉村,曾經壓倒性的政治力量已經疲軟,古老的鄉村文明有了復蘇的跡象。高中畢業生端方回到了他的故鄉——畢飛宇的「王家庄」。他怎樣在家鄉立足?他如何直面命運?他又將經歷怎樣的愛情?平原涌大海,峰起潮落,青春祭日月,暗紅枯白。
畢飛宇,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着有中短篇小說近百篇。主要作品有《畢飛宇文集》四卷,《畢飛宇作品集》七卷,代表作有《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作品曾獲第一、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馮牧文學獎、第一屆中國小說學會獎、2012年台灣《中國時代》開卷好書文學獎、2010年法國《世界報》文學獎、2011年第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序
我的電腦上清晰地顯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遺憾,開工的日期我忘了寫了。但我是記得的,那時候很冷。我對「冷」很敏感,因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親的話說,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離開母體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間只隔了一張《人民日報》。按照接生婆的說法,她這樣做有兩樣好處: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長大了之后不怕冷。
經過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說我應該是一個不怕冷的人才對。事實上卻不是這樣,我怕冷。我怕冷是寫作帶來的后遺症。——在我職業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寫作的條件還很艱苦。因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點寫到凌晨兩點。在沒有任何取暖設備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極其給力的,家里頭都能夠結冰。我記憶最為深刻的是這樣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當我擱筆的時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為右手的手指實在動不起來了。——經歷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許是寒冷給我帶來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寫作狀態反而格外地好,都條件反射了。說句俏皮話,我一冷就「有才」。因為這個緣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選擇在1月或者2月開工。這個不會錯的。如此說來,《平原》的開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節前后。
我決定寫《平原》其實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東。
為什麼是在山東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東濰坊。2001年,孩子已經五歲了,我的太太決定回一趟山東,去看看她生父的墳。說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這是我第一次為親人上墳——我人生里有一個很大的缺憾,我沒有上墳的經驗。我在過去的訪談里交待過,我的父親其實是一個孤兒。他的來歷至今是一個黑洞。這里頭有時光的緣故,也有政治的緣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個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點,我不姓「畢」,究竟姓什麼,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親姓過一段時間的「陸」,四九之后,他接受了「有關部門」的「建議」,最終選擇了「畢」,就這麼的,我也姓了畢。——我這個「姓畢的」怎麼會有祖墳呢,我這個「姓畢的」哪里會有上墳的機會呢。
說完了這一切我終於可以說了,在上墳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並沒有做好足夠的精神准備。我太太是兩歲半喪的父,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蘇。這個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當時還不知道,「喪父」這件事從來就不會因為生父的離去而結終,相反,會因為生父的離去而開始。生活就是這樣,在某一個機緣出現之前,你其實「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這不是我們麻木,也不是我們愚蠢,是因為我們沒有身臨其境,是因為我們沒有設身處地。我再也不想回憶上墳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內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腦子里既是滿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躍。我對一個詞有了重新的認識,那就是關系,或者說,人物關系。我對「人物關系」這個13常的概念有了切膚的體會。哪怕這個關系你根本沒見過,但是,它在,被時光捆綁在時光里。
我的處女作發表於1991年。在隨后的很長時間里,就技術層面而言,我的主要興趣是語言實驗。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興奮點挪到了小說人物。山東之行讓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調整,我下一步的重點必然是人物關系。
我記不得我是在哪一天決定寫《平原》的了,但是,在山東。這一點確鑿無疑。《平原》是小說,就小說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沒有一點關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沒有一點關系。但是,隱含性的關系是有的。因為特殊的家世,我對「家族」、「血緣」、「世態」、「人情」,乃至於「哺乳」、「分娩」等話題一直抱有特殊的興趣。我曾經說過一句話,我「生下來就是一個小說家」,許多人對這句話是誤解的。以為我狂。我有什麼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個人都幸福,可實際情況又不是這樣。我的家族里的許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許多人的人生都有無法彌補的缺憾。——我願意把這種「無法彌補」看做命運給我的特殊饋贈。生活是有恩於我的。
在《平原》發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訪問和演講大多圍繞着「世態人情」,我的許多談話都是從這里展開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認為我不尊重文學的「想象力」。扯什麼淡呢,沒有想象力還寫什麼小說呢。我想說的是,一個負責任的寫作者不願意信口雌黃,開口閉口都是永遠正確的空頭理論。——他的言談往往會伴隨着他的實踐,寫到哪里,他就說到哪里。在不同的寫作階段,他的言論會有不同的側重,就這麼簡單。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復復地嘮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執意要問,你寫《平原》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麼?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好回答。我寫作的時候腦子並不那麼清晰,這是我喜愛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狀態。但我會懸置一些念頭。這些懸置的念頭是牧羊犬,它領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沒有方向。每一頭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總體上又能夠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則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經說了第一條了,為了表達的清晰度,我願意再把兩條牧羊犬牽出來,讓它們叫兩聲。
一、人物關系
還是用「國貨」來做例子吧。如果我們把《三國》、《水滸》、《紅樓夢》放在一起,我們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關系:《三國》與《水滸》里的人物所構成的是「公共關系」,劍指家國天下與山河人民;而《紅樓夢》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則是「私人關系」,我願意把私人關系說得更形象一點,叫做「屋檐下的關系」,這里有人生的符咒與密碼,「我見過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國文學向來有它的「潛規則」,——公共關系的「格局」和「價值」大於屋檐下的關系。公共關系是宏偉的,詩史的,大氣的,正統的,康庄的,屋檐下的關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關系的一個「補充」。
可我信不過公共關系。保守一點說,在小說的世界里,我信不過公共關系。說不上因為什麼,我就是信不過。我一直缺少一種理論能力來充分地表達我的這種信不過。我不懂古玩,在高人的指點下,我最近知道了一個概念,叫「包漿」。我想我終於找到一種合適的表達方式了。「包漿」在物體的最表層,它不是本質。可是,吊詭的是,行家們恰恰就是依靠這個表層來斷定本質的,甚至於,這個表層才是本質。是真,還是假,行家們「一眼」就「有數」了。在我看來,相對於哲學,小說的對象就是表層,揭示本質那是哲學家的事。但是,小說的意義就在於,它所描繪的表象可以反應本質,直至抵達本質。
我喜歡屋檐下的人物關系。在屋檐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真貨的「包漿」,印證出本原的質地。而到了公共關系里頭,無論人物的「做工」有多好,他的「包漿」始終透露出仿品的痕跡,他的光澤不那麼安寧,有「冒充」的吃力,有「冒充」的過猶不及。
當然,「包漿說」是我的一點淺見,上不了台面的。這和我的趣味有關,這和我的個人身世有關。我尊重熱衷於公共關系的作品,事實上,我同樣是「公共關系類」小說的熱心讀者。我只是對審美的「潛規則」不滿意。——公共關系和屋檐下的關系是等值的;處理公共關系和處理屋檐下關系的美學意義是等值的。不等值的只是寫作者的能力和格局。
《平原》里的事情大部分在屋檐的下面,我要面對是親人與親人。批評家張莉女士曾告訴我,多年之后,《平原》的讀者根本不需要通過時代背景的交待就可以直接進入小說(大意)。這不是一句贊美的話,而是她閱讀后的感受。這句話讓我極度欣慰。
二、文化形態
說《平原》是很難避開《玉米》的。它們有先后和銜接的關系,它們擁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它們還有近似的美學追求,它們的語言類屬一個系統。《平原》和《玉米》的敘述語氣幾乎一模一樣,和《推拿》不同,與《青衣》迥異。
問題來了,既然《平原》和《玉米》那麼相似,你還寫個什麼勁呢?你沿着《玉米》的調調,把《玉穗》、《玉苗》、《玉葉》一路寫完了不就完了?
不是這樣的。《平原》和《玉米》其實有質的區別。這個區別在文化形態。
《玉米》梳理的是中國鄉村「文革」的轉折關頭(林彪事件所發生的1971年)。這轉折是「文革」內部的轉折,中國不是變好了,而是更壞。「文革」正在細化,在滲入日常,在滲入婚喪嫁娶和柴米油鹽。
可1976年的中國鄉村是不一樣的。這正是《平原》所渴望呈現的。在1976年的中國鄉村,紅色恐怖早已經松動了,壓倒性的政治力量其實很疲軟了。伴隨着三次不同尋常的葬禮,一些常規的、古老的鄉村情感和鄉村人際業已呈現,古老而又愚昧的鄉村文明有了死灰復燃的跡象。用我父親的話說,人們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像解放前」了。那是亂世的景象。然而,這亂世太獨特了。它不是兵荒馬亂的那種亂。它很靜,是死氣沉沉的亂,了無生息。人們不再關注外部,即使替換了領袖,「上面」還想熱鬧,可人們的熱情實在已經耗干了。沒有人還真的相信什麼。人們想起了「過日子」,不是生活,是混。沒有眼淚,沒有悲傷。活一天是一天。
我不知道人類歷史上還有沒有類似的歷史時刻,整整一個民族成了巨大的植物人。他失去了動作能力,內心在活動,凌亂,生動,是遙遠的故往,像史前。奇怪的是,「家」的概念卻在復活,人似乎又可以自私了。——我不想放過它。
關於《平原》和《玉米》的區別,我還想補充一點,《玉米》在風格上是寫實的,它的美學特征是現實的,然而,它一點都不「寫實」。我的生活並沒有為我提供「寫實依據」,它是想象的。《平原》則不同,《平原》的落腳點在1976年。1976年,我已經是一個12歲的少年。因為我的父親是中學教師,我很早就和中學生、知青們一起廝混。我實際上要比同年代的孩子早熟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原》里主人公端方、三丫、興隆、佩全的生活和我同步,——《平原》是離我最近的一本書,它就是從我的現實人生里生長出來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頂端,分出了五個岔。
端方是《平原》的主人公,結構性的人物。也就是所謂的「男一號」。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我對所謂的「男一號」和「女一號」沒什麼興趣。為了小說的結構,我們必須有「男一號」和「女一號」,但是,真正令我着迷的,反而是圍繞在「一號」周邊的那些配角。以我對小說的膚淺的認識,我覺得,小說的廣度往往是由「一號」帶來的,小說的深度則取決於「二號」、「三號」和「四號」。而不是相反。
我甚至認為,「一號」其實是不用去「寫」的,把周邊的次要人物寫好了,「一號」也就自然而然地出來了。
在這里我想談談幾個次要人物。
我想說的第一個人物是「老魚叉」。「老魚叉」是《平原》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人物,也是我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個人物(抱歉,賣瓜了)。1949年之前,「老魚叉」是一個革命者。許多時候,我們容易把革命者和理想主義者混同起來,而事實上,許多革命者是最沒有理想、最沒有定見、最動搖的那部分人。他們是被風吹走的人。他們革命,不是因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阿Q正傳》描寫過革命者的革命,有一句話魯迅說得特別地深刻:「於是一同去。」革命者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於是」,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就是「一同去」。
在中國的鄉村,作為農民革命的勝利者,「革命者」和「勝利者」都為數甚眾。但許多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國農民的愚昧和善良」。這是一對古怪的文化組合,也是一對古怪的心理組合。中國農民的行動力大多是由這個夢幻般的組合提供能量的。這是一個值得許多作家和學者面對的一個大問題。可以說,愚昧和善良是中國農民的兩面,它是動態的,哪一面會呈現出來,帶有極大的隨機性和偶然性。通常,它們相伴而行。我不是一個中國農民問題的專家,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中國農民是全人類最缺少愛的龐大集體,從來沒有一個組織和機構真正愛過中國的農民。
無論如何,描寫「革命者」和「勝利者」是《平原》的分內事。在此我承認,「老魚叉」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這個原型就是我同班同學的父親。他住在「前地主」寬大的大瓦房里,那是他的戰利品,他還成功地繼承了「前地主」的一位小老婆。他的不幸在於,從我認識他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停地自殺。因為他總是夢見「前地主」來找他。1974年,他成功了。他把自己吊死在了大瓦房的屋梁上。
理性一點說,在中國的鄉村,「老魚叉」沒有普遍意義。他的內心和他的行為更沒有普遍性。但是,這件事對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見過「老魚叉」的屍體。這具屍體並不恐怖,但是,圍繞着這具屍體所散發出來的言論卻陰森恐怖,「前地主」的鬼魂似乎一天也沒有離散過。它在飄盪。它是「變色貓」,白天是白貓,夜晚是黑貓。我願意把「老魚叉」的死看做「勝利者」的良心未泯,它是后來的后怕、后補的后悔,然而,上升不到反思與救贖的高度。因為「變色貓」游盪的身影,我寫「老魚叉」的時候特別地膽怯,一到這個部分我就惶惶不可終日。眼睛尖的讀者也許能夠讀得出來。
我想說的第二個人物是「混世魔王」。一個知青。我寫這個人物是糾結的。從個人情感上來說,我對知青有好感。我的家一直是知青俱樂部,我的許多小學老師就是知青,他們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當我面對「混世魔王」的時候,我的心情卻有些復雜。
如何面對知青?我決定把這個話題說得簡潔一點。問題的關鍵是角度。我出生在鄉村,是村子里的人。換句話說,無論我個人和知青的關系如何,在看待知青這個問題上,我不可能選擇「知青作家」的角度,相反,我的角度是村子里的,是農民的。這也許是我和知青作家最大的差異。我不擁有真理,但我擁有角度。我想我不能也不該偏離我的角度。即使有一天,未來證明了我的角度有問題,我也願意把《平原》放在這里,成為未來這個話題的一個小小的補充。
我最不想說和我不得不說的這個人是老顧。他是一個被遣送到鄉村的「右派」。我寫這個人不只是糾結,我簡直就是和自己過意不去。——我的父親就是一個被遣送到鄉村的「右派」。
長期以來,無論是早起的「傷痕文學」,還是后來的「右派文學」,包括再后來的「反思文學」,在中國的當代小說當中,「右派」這個形象其實已經有了他的基本模式,概括起來說,——他是被侮辱的,也是被損害的,他在政治上代表了最終「正確」的那一方,他是早覺者,他是悲情的文化英雄。
因為家庭的緣故,我從小就認識許許多多的「右派」。當然了,他們和我的父親一樣,都是「小右派」。在我的文學青年時代,我讀過大量的「右派作家」和有關「右派」的小說,我的總體感覺是,我的前輩們偏於控訴了,或者說,偏於抒情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時間過去了這麼久,不能說這不是一種遺憾。現如今,「右派」作家年事已高,大部分都歇筆了。如果他們還在寫,他們會做些什麼呢?
「右派」是集權的對抗者。「右派形象」也是文學作品當中集權的對抗者。他們是可敬的。我的問題是,當歷史提供了反思機遇的時候,這里頭該不該有豁免者?有沒有人可以永久地屹立在絕對正確的那一方?我的回答是不。《平原》的反思包涵了「右派」,這並不容易。一方面有我能力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我感情上的局限。在寫老顧這個人物的時候,我是沉痛的。我至今都沒有讓我的父親讀《平原》,我們從來沒有聊過這個話題。我是回避了。——面對老顧,我從骨子里感受到一個小說家的艱難。許多時候,你明確地知道「該」往哪里寫,但是,你下不去筆。這樣的反復和猶豫會讓你傷神不已。
《平原》的第一稿是33萬字,最后出版的時候是25萬。我在第三稿刪掉了8萬字。這8萬字有一部分是關於鄉村的風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時候,我不願意《平原》呈現出「鄉土小說」的風貌,它過於「優美」,有小資的惡俗,我果斷地把它們刪除了;另外的一個部分就是關於老顧。我要承認,我「跳出來」說了太多。這個部分我刪掉的大概也有4萬字。
為了預防自己反悔,把刪除的部分再貼上去,我沒有保留刪除掉的那8萬字。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這是讓我最為后悔的一件事。我的直覺是,有關老顧的那4萬字,我這輩子可能再也寫不出來了,那個語境不存在了。借助於老顧,我對馬克思《巴黎手稿》有很長很長的「讀后感」,我只記得我寫得很亢奮,但是,《巴黎手稿》我基本上已經忘光了。沒有受過良好哲學訓練的人就這樣,他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哲學讀者,讀也讀了,忘就忘了。
我感興趣的其實還是「異化」這個問題。這是一個老話題了。上世紀80年代讀大學的朋友一定還記得,那個時代有過一次「異化問題」的社會大討論。「異化」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費爾巴哈提出來的,他討論的是人與上帝的關系,上帝最終使人變成了「非人」。黑格爾接手了這個話題,他借助於「辯證法」——這個雷霆萬鈞的邏輯方法,進一步探討了人類的「異化」。馬克思,作為一個是革命的鼓動家,在號召「全世界無產者」革命之前,他分析了「商品」,揭示了「剝削」;他同時也探索了「異化」,他的「辯證法」是這樣的:「大機器生產』』與「工人階級」是「對立的統一」,這個「對立統一」的結果是人的「異化」——人變成了機器。
——我其實並沒有能力討論這樣宏大的哲學問題。讓我對「異化』』問題產生興趣的是我大學三年級的一次閱讀。一個小冊子,白色封面,紅色書名。作者是「高層」的一位「秀才」。他的論述是這樣的:中國是農業社會,還沒有進入馬克思所談及的「大機器生產」,所以,中國社會不存在「異化」問題。
讀完這個小冊子我非常生氣,一個年輕的、讀中文的大學生,他沒有很好的哲學素養,他尚未深入地社會了解,他沒有縝密的邏輯能力,可他不是白痴。你不能這樣愚弄我。——這是什麼邏輯?——這哪里還是討論問題?這是權力借助於「理論」這粒偉哥在暴奸。
我寫老顧,說到底,不是寫「右派」,寫的是「理論」或「信仰」面前中國知識分子的「異化」。
也許我還要簡單地談一談第四個人物,三丫。我打算把這一段話獻給今天的年輕人。三丫的悲劇來自於血統論。血統論,多麼陌生的一個詞啊。我想說的是,血統論是這個世界上最邪惡的事情,最起碼,是最邪惡的事情之一。
說到這里我特別想說一點題外話。很長時間以來,我的腦袋上一直有一頂不錯的帽子,「寫女性最好的中國作家」。這個評價是善意的,積極的。但是,在現實層面,它有意無意地遮蓋了一些東西。我不會為此糾結,可我依然要說,我的文學世界委實要比幾個女性形象開闊得多。
《平原》大致上寫了三年半。在現在為止,《平原》是我整個寫作生涯中運氣最好的一部。它從來沒有被打斷過。我在平原上「一口氣」奔跑了三年半,這簡直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在今天,當我追憶起《平原》的寫作時,我幾乎想不起具體的寫作細節來了,就是「一口氣」的事情。當然,它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我有很長時間適應不了離開《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端着茶杯來到了書房,坐下來,點煙,然后,把電腦打開了。啪啪啪,不停地點鼠標。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意識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來之后我愣了一下。這個感覺讓我傷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顧茫茫。我只是疊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張椅子。我也「異化」了。我記得那個時間段里頭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記者采訪我,她讓我談談「寫完后的感受」,我是這樣告訴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們來到了海邊,她上船了,我卻留在了岸上。」
老實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文學上擁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我最大的才華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靜的。當我的心靜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發生了。
事情發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靜的。那里頭有我的驕傲。
這也許是《平原》的第四個版本了,這個版本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由於種種原因,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合作比較晚。可是,在短短的幾年當中,我見識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職業水准和敬業精神,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厚愛。
對了,我還要感謝一個人,《平原》這個書名是《收獲》雜志社的程永新幫我取的。我電腦里的書名叫《長篇小說》,小說寫了三年半,我居然忘了起名字,說起來像個笑話。感謝程永新。他為這個書名真是煞費了苦心。這個書名好。
2012年3月1日於南京龍江
經過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說我應該是一個不怕冷的人才對。事實上卻不是這樣,我怕冷。我怕冷是寫作帶來的后遺症。——在我職業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寫作的條件還很艱苦。因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點寫到凌晨兩點。在沒有任何取暖設備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極其給力的,家里頭都能夠結冰。我記憶最為深刻的是這樣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當我擱筆的時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為右手的手指實在動不起來了。——經歷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許是寒冷給我帶來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寫作狀態反而格外地好,都條件反射了。說句俏皮話,我一冷就「有才」。因為這個緣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選擇在1月或者2月開工。這個不會錯的。如此說來,《平原》的開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節前后。
我決定寫《平原》其實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東。
為什麼是在山東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東濰坊。2001年,孩子已經五歲了,我的太太決定回一趟山東,去看看她生父的墳。說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這是我第一次為親人上墳——我人生里有一個很大的缺憾,我沒有上墳的經驗。我在過去的訪談里交待過,我的父親其實是一個孤兒。他的來歷至今是一個黑洞。這里頭有時光的緣故,也有政治的緣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個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點,我不姓「畢」,究竟姓什麼,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親姓過一段時間的「陸」,四九之后,他接受了「有關部門」的「建議」,最終選擇了「畢」,就這麼的,我也姓了畢。——我這個「姓畢的」怎麼會有祖墳呢,我這個「姓畢的」哪里會有上墳的機會呢。
說完了這一切我終於可以說了,在上墳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並沒有做好足夠的精神准備。我太太是兩歲半喪的父,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蘇。這個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當時還不知道,「喪父」這件事從來就不會因為生父的離去而結終,相反,會因為生父的離去而開始。生活就是這樣,在某一個機緣出現之前,你其實「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這不是我們麻木,也不是我們愚蠢,是因為我們沒有身臨其境,是因為我們沒有設身處地。我再也不想回憶上墳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內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腦子里既是滿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躍。我對一個詞有了重新的認識,那就是關系,或者說,人物關系。我對「人物關系」這個13常的概念有了切膚的體會。哪怕這個關系你根本沒見過,但是,它在,被時光捆綁在時光里。
我的處女作發表於1991年。在隨后的很長時間里,就技術層面而言,我的主要興趣是語言實驗。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興奮點挪到了小說人物。山東之行讓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調整,我下一步的重點必然是人物關系。
我記不得我是在哪一天決定寫《平原》的了,但是,在山東。這一點確鑿無疑。《平原》是小說,就小說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沒有一點關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沒有一點關系。但是,隱含性的關系是有的。因為特殊的家世,我對「家族」、「血緣」、「世態」、「人情」,乃至於「哺乳」、「分娩」等話題一直抱有特殊的興趣。我曾經說過一句話,我「生下來就是一個小說家」,許多人對這句話是誤解的。以為我狂。我有什麼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個人都幸福,可實際情況又不是這樣。我的家族里的許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許多人的人生都有無法彌補的缺憾。——我願意把這種「無法彌補」看做命運給我的特殊饋贈。生活是有恩於我的。
在《平原》發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訪問和演講大多圍繞着「世態人情」,我的許多談話都是從這里展開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認為我不尊重文學的「想象力」。扯什麼淡呢,沒有想象力還寫什麼小說呢。我想說的是,一個負責任的寫作者不願意信口雌黃,開口閉口都是永遠正確的空頭理論。——他的言談往往會伴隨着他的實踐,寫到哪里,他就說到哪里。在不同的寫作階段,他的言論會有不同的側重,就這麼簡單。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復復地嘮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執意要問,你寫《平原》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麼?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好回答。我寫作的時候腦子並不那麼清晰,這是我喜愛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狀態。但我會懸置一些念頭。這些懸置的念頭是牧羊犬,它領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沒有方向。每一頭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總體上又能夠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則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經說了第一條了,為了表達的清晰度,我願意再把兩條牧羊犬牽出來,讓它們叫兩聲。
一、人物關系
還是用「國貨」來做例子吧。如果我們把《三國》、《水滸》、《紅樓夢》放在一起,我們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關系:《三國》與《水滸》里的人物所構成的是「公共關系」,劍指家國天下與山河人民;而《紅樓夢》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則是「私人關系」,我願意把私人關系說得更形象一點,叫做「屋檐下的關系」,這里有人生的符咒與密碼,「我見過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國文學向來有它的「潛規則」,——公共關系的「格局」和「價值」大於屋檐下的關系。公共關系是宏偉的,詩史的,大氣的,正統的,康庄的,屋檐下的關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關系的一個「補充」。
可我信不過公共關系。保守一點說,在小說的世界里,我信不過公共關系。說不上因為什麼,我就是信不過。我一直缺少一種理論能力來充分地表達我的這種信不過。我不懂古玩,在高人的指點下,我最近知道了一個概念,叫「包漿」。我想我終於找到一種合適的表達方式了。「包漿」在物體的最表層,它不是本質。可是,吊詭的是,行家們恰恰就是依靠這個表層來斷定本質的,甚至於,這個表層才是本質。是真,還是假,行家們「一眼」就「有數」了。在我看來,相對於哲學,小說的對象就是表層,揭示本質那是哲學家的事。但是,小說的意義就在於,它所描繪的表象可以反應本質,直至抵達本質。
我喜歡屋檐下的人物關系。在屋檐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真貨的「包漿」,印證出本原的質地。而到了公共關系里頭,無論人物的「做工」有多好,他的「包漿」始終透露出仿品的痕跡,他的光澤不那麼安寧,有「冒充」的吃力,有「冒充」的過猶不及。
當然,「包漿說」是我的一點淺見,上不了台面的。這和我的趣味有關,這和我的個人身世有關。我尊重熱衷於公共關系的作品,事實上,我同樣是「公共關系類」小說的熱心讀者。我只是對審美的「潛規則」不滿意。——公共關系和屋檐下的關系是等值的;處理公共關系和處理屋檐下關系的美學意義是等值的。不等值的只是寫作者的能力和格局。
《平原》里的事情大部分在屋檐的下面,我要面對是親人與親人。批評家張莉女士曾告訴我,多年之后,《平原》的讀者根本不需要通過時代背景的交待就可以直接進入小說(大意)。這不是一句贊美的話,而是她閱讀后的感受。這句話讓我極度欣慰。
二、文化形態
說《平原》是很難避開《玉米》的。它們有先后和銜接的關系,它們擁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它們還有近似的美學追求,它們的語言類屬一個系統。《平原》和《玉米》的敘述語氣幾乎一模一樣,和《推拿》不同,與《青衣》迥異。
問題來了,既然《平原》和《玉米》那麼相似,你還寫個什麼勁呢?你沿着《玉米》的調調,把《玉穗》、《玉苗》、《玉葉》一路寫完了不就完了?
不是這樣的。《平原》和《玉米》其實有質的區別。這個區別在文化形態。
《玉米》梳理的是中國鄉村「文革」的轉折關頭(林彪事件所發生的1971年)。這轉折是「文革」內部的轉折,中國不是變好了,而是更壞。「文革」正在細化,在滲入日常,在滲入婚喪嫁娶和柴米油鹽。
可1976年的中國鄉村是不一樣的。這正是《平原》所渴望呈現的。在1976年的中國鄉村,紅色恐怖早已經松動了,壓倒性的政治力量其實很疲軟了。伴隨着三次不同尋常的葬禮,一些常規的、古老的鄉村情感和鄉村人際業已呈現,古老而又愚昧的鄉村文明有了死灰復燃的跡象。用我父親的話說,人們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像解放前」了。那是亂世的景象。然而,這亂世太獨特了。它不是兵荒馬亂的那種亂。它很靜,是死氣沉沉的亂,了無生息。人們不再關注外部,即使替換了領袖,「上面」還想熱鬧,可人們的熱情實在已經耗干了。沒有人還真的相信什麼。人們想起了「過日子」,不是生活,是混。沒有眼淚,沒有悲傷。活一天是一天。
我不知道人類歷史上還有沒有類似的歷史時刻,整整一個民族成了巨大的植物人。他失去了動作能力,內心在活動,凌亂,生動,是遙遠的故往,像史前。奇怪的是,「家」的概念卻在復活,人似乎又可以自私了。——我不想放過它。
關於《平原》和《玉米》的區別,我還想補充一點,《玉米》在風格上是寫實的,它的美學特征是現實的,然而,它一點都不「寫實」。我的生活並沒有為我提供「寫實依據」,它是想象的。《平原》則不同,《平原》的落腳點在1976年。1976年,我已經是一個12歲的少年。因為我的父親是中學教師,我很早就和中學生、知青們一起廝混。我實際上要比同年代的孩子早熟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原》里主人公端方、三丫、興隆、佩全的生活和我同步,——《平原》是離我最近的一本書,它就是從我的現實人生里生長出來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頂端,分出了五個岔。
端方是《平原》的主人公,結構性的人物。也就是所謂的「男一號」。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我對所謂的「男一號」和「女一號」沒什麼興趣。為了小說的結構,我們必須有「男一號」和「女一號」,但是,真正令我着迷的,反而是圍繞在「一號」周邊的那些配角。以我對小說的膚淺的認識,我覺得,小說的廣度往往是由「一號」帶來的,小說的深度則取決於「二號」、「三號」和「四號」。而不是相反。
我甚至認為,「一號」其實是不用去「寫」的,把周邊的次要人物寫好了,「一號」也就自然而然地出來了。
在這里我想談談幾個次要人物。
我想說的第一個人物是「老魚叉」。「老魚叉」是《平原》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人物,也是我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個人物(抱歉,賣瓜了)。1949年之前,「老魚叉」是一個革命者。許多時候,我們容易把革命者和理想主義者混同起來,而事實上,許多革命者是最沒有理想、最沒有定見、最動搖的那部分人。他們是被風吹走的人。他們革命,不是因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阿Q正傳》描寫過革命者的革命,有一句話魯迅說得特別地深刻:「於是一同去。」革命者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於是」,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就是「一同去」。
在中國的鄉村,作為農民革命的勝利者,「革命者」和「勝利者」都為數甚眾。但許多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國農民的愚昧和善良」。這是一對古怪的文化組合,也是一對古怪的心理組合。中國農民的行動力大多是由這個夢幻般的組合提供能量的。這是一個值得許多作家和學者面對的一個大問題。可以說,愚昧和善良是中國農民的兩面,它是動態的,哪一面會呈現出來,帶有極大的隨機性和偶然性。通常,它們相伴而行。我不是一個中國農民問題的專家,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中國農民是全人類最缺少愛的龐大集體,從來沒有一個組織和機構真正愛過中國的農民。
無論如何,描寫「革命者」和「勝利者」是《平原》的分內事。在此我承認,「老魚叉」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這個原型就是我同班同學的父親。他住在「前地主」寬大的大瓦房里,那是他的戰利品,他還成功地繼承了「前地主」的一位小老婆。他的不幸在於,從我認識他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停地自殺。因為他總是夢見「前地主」來找他。1974年,他成功了。他把自己吊死在了大瓦房的屋梁上。
理性一點說,在中國的鄉村,「老魚叉」沒有普遍意義。他的內心和他的行為更沒有普遍性。但是,這件事對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見過「老魚叉」的屍體。這具屍體並不恐怖,但是,圍繞着這具屍體所散發出來的言論卻陰森恐怖,「前地主」的鬼魂似乎一天也沒有離散過。它在飄盪。它是「變色貓」,白天是白貓,夜晚是黑貓。我願意把「老魚叉」的死看做「勝利者」的良心未泯,它是后來的后怕、后補的后悔,然而,上升不到反思與救贖的高度。因為「變色貓」游盪的身影,我寫「老魚叉」的時候特別地膽怯,一到這個部分我就惶惶不可終日。眼睛尖的讀者也許能夠讀得出來。
我想說的第二個人物是「混世魔王」。一個知青。我寫這個人物是糾結的。從個人情感上來說,我對知青有好感。我的家一直是知青俱樂部,我的許多小學老師就是知青,他們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當我面對「混世魔王」的時候,我的心情卻有些復雜。
如何面對知青?我決定把這個話題說得簡潔一點。問題的關鍵是角度。我出生在鄉村,是村子里的人。換句話說,無論我個人和知青的關系如何,在看待知青這個問題上,我不可能選擇「知青作家」的角度,相反,我的角度是村子里的,是農民的。這也許是我和知青作家最大的差異。我不擁有真理,但我擁有角度。我想我不能也不該偏離我的角度。即使有一天,未來證明了我的角度有問題,我也願意把《平原》放在這里,成為未來這個話題的一個小小的補充。
我最不想說和我不得不說的這個人是老顧。他是一個被遣送到鄉村的「右派」。我寫這個人不只是糾結,我簡直就是和自己過意不去。——我的父親就是一個被遣送到鄉村的「右派」。
長期以來,無論是早起的「傷痕文學」,還是后來的「右派文學」,包括再后來的「反思文學」,在中國的當代小說當中,「右派」這個形象其實已經有了他的基本模式,概括起來說,——他是被侮辱的,也是被損害的,他在政治上代表了最終「正確」的那一方,他是早覺者,他是悲情的文化英雄。
因為家庭的緣故,我從小就認識許許多多的「右派」。當然了,他們和我的父親一樣,都是「小右派」。在我的文學青年時代,我讀過大量的「右派作家」和有關「右派」的小說,我的總體感覺是,我的前輩們偏於控訴了,或者說,偏於抒情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時間過去了這麼久,不能說這不是一種遺憾。現如今,「右派」作家年事已高,大部分都歇筆了。如果他們還在寫,他們會做些什麼呢?
「右派」是集權的對抗者。「右派形象」也是文學作品當中集權的對抗者。他們是可敬的。我的問題是,當歷史提供了反思機遇的時候,這里頭該不該有豁免者?有沒有人可以永久地屹立在絕對正確的那一方?我的回答是不。《平原》的反思包涵了「右派」,這並不容易。一方面有我能力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我感情上的局限。在寫老顧這個人物的時候,我是沉痛的。我至今都沒有讓我的父親讀《平原》,我們從來沒有聊過這個話題。我是回避了。——面對老顧,我從骨子里感受到一個小說家的艱難。許多時候,你明確地知道「該」往哪里寫,但是,你下不去筆。這樣的反復和猶豫會讓你傷神不已。
《平原》的第一稿是33萬字,最后出版的時候是25萬。我在第三稿刪掉了8萬字。這8萬字有一部分是關於鄉村的風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時候,我不願意《平原》呈現出「鄉土小說」的風貌,它過於「優美」,有小資的惡俗,我果斷地把它們刪除了;另外的一個部分就是關於老顧。我要承認,我「跳出來」說了太多。這個部分我刪掉的大概也有4萬字。
為了預防自己反悔,把刪除的部分再貼上去,我沒有保留刪除掉的那8萬字。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這是讓我最為后悔的一件事。我的直覺是,有關老顧的那4萬字,我這輩子可能再也寫不出來了,那個語境不存在了。借助於老顧,我對馬克思《巴黎手稿》有很長很長的「讀后感」,我只記得我寫得很亢奮,但是,《巴黎手稿》我基本上已經忘光了。沒有受過良好哲學訓練的人就這樣,他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哲學讀者,讀也讀了,忘就忘了。
我感興趣的其實還是「異化」這個問題。這是一個老話題了。上世紀80年代讀大學的朋友一定還記得,那個時代有過一次「異化問題」的社會大討論。「異化」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費爾巴哈提出來的,他討論的是人與上帝的關系,上帝最終使人變成了「非人」。黑格爾接手了這個話題,他借助於「辯證法」——這個雷霆萬鈞的邏輯方法,進一步探討了人類的「異化」。馬克思,作為一個是革命的鼓動家,在號召「全世界無產者」革命之前,他分析了「商品」,揭示了「剝削」;他同時也探索了「異化」,他的「辯證法」是這樣的:「大機器生產』』與「工人階級」是「對立的統一」,這個「對立統一」的結果是人的「異化」——人變成了機器。
——我其實並沒有能力討論這樣宏大的哲學問題。讓我對「異化』』問題產生興趣的是我大學三年級的一次閱讀。一個小冊子,白色封面,紅色書名。作者是「高層」的一位「秀才」。他的論述是這樣的:中國是農業社會,還沒有進入馬克思所談及的「大機器生產」,所以,中國社會不存在「異化」問題。
讀完這個小冊子我非常生氣,一個年輕的、讀中文的大學生,他沒有很好的哲學素養,他尚未深入地社會了解,他沒有縝密的邏輯能力,可他不是白痴。你不能這樣愚弄我。——這是什麼邏輯?——這哪里還是討論問題?這是權力借助於「理論」這粒偉哥在暴奸。
我寫老顧,說到底,不是寫「右派」,寫的是「理論」或「信仰」面前中國知識分子的「異化」。
也許我還要簡單地談一談第四個人物,三丫。我打算把這一段話獻給今天的年輕人。三丫的悲劇來自於血統論。血統論,多麼陌生的一個詞啊。我想說的是,血統論是這個世界上最邪惡的事情,最起碼,是最邪惡的事情之一。
說到這里我特別想說一點題外話。很長時間以來,我的腦袋上一直有一頂不錯的帽子,「寫女性最好的中國作家」。這個評價是善意的,積極的。但是,在現實層面,它有意無意地遮蓋了一些東西。我不會為此糾結,可我依然要說,我的文學世界委實要比幾個女性形象開闊得多。
《平原》大致上寫了三年半。在現在為止,《平原》是我整個寫作生涯中運氣最好的一部。它從來沒有被打斷過。我在平原上「一口氣」奔跑了三年半,這簡直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在今天,當我追憶起《平原》的寫作時,我幾乎想不起具體的寫作細節來了,就是「一口氣」的事情。當然,它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我有很長時間適應不了離開《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端着茶杯來到了書房,坐下來,點煙,然后,把電腦打開了。啪啪啪,不停地點鼠標。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意識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來之后我愣了一下。這個感覺讓我傷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顧茫茫。我只是疊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張椅子。我也「異化」了。我記得那個時間段里頭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記者采訪我,她讓我談談「寫完后的感受」,我是這樣告訴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們來到了海邊,她上船了,我卻留在了岸上。」
老實說,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文學上擁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我最大的才華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靜的。當我的心靜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發生了。
事情發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靜的。那里頭有我的驕傲。
這也許是《平原》的第四個版本了,這個版本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由於種種原因,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合作比較晚。可是,在短短的幾年當中,我見識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職業水准和敬業精神,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厚愛。
對了,我還要感謝一個人,《平原》這個書名是《收獲》雜志社的程永新幫我取的。我電腦里的書名叫《長篇小說》,小說寫了三年半,我居然忘了起名字,說起來像個笑話。感謝程永新。他為這個書名真是煞費了苦心。這個書名好。
2012年3月1日於南京龍江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