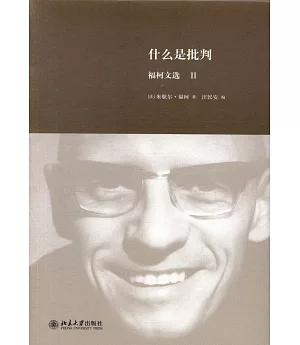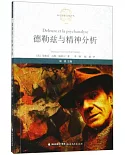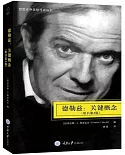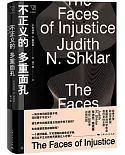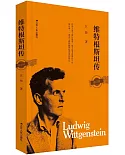福柯的思想的力量和影響是令人驚訝的,同時也將是永恆的。
—愛德華·賽義德
福柯養成了一種十分優雅,有時甚至過分優雅的文風,他覺得自己肩負着維護法語語言規范的使命。
—莫里斯·布朗肖
福柯的方法既帶有極端的科學辨別力,又保持有對「科學」的極端的距離;這是對我們的知識傳統的*一次沖擊。
—羅蘭·巴特
米歇爾·福柯的 《詞與物》 就是關於不成熟的科學的——主要論述的是「生活、勞動和語言」。他談到一個時代的生物學、經濟學和哲學,談到自然史,分析了它們之前的財富和普遍語法。他對我們當代的人文科學進行了新的批判。該書在所有層面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伊恩·哈金
如果福柯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這是因為他出於歷史之外的原因而利用了歷史:就像尼采所言,因為人們希望一個時代將要來臨,就反對這個時代,於是對這個時代產生影響。
—吉爾·德勒茲
福柯的文章寫得非常漂亮,其文本本身的運動變化就是對所述命題的絕好闡述。一方面,螺旋上升的結構頗具威力,但它不是那種巍峨的建築,而是游移蜿蜒,回環往復,沒有起源(也沒有巨變),不斷地展開,越來越儼然;另一方面,縫隙中流淌着一股力量,滲透於社會、精神以至身體織成的整個孔狀大網,無往而不至地調節着權力技術。
—讓·鮑德里亞
福柯是20世紀重要的思想家,世界影響力大,在中國擁躉眾多。福柯提出了著名的權力分析視角、譜系學研究方法和考古學方法,在對瘋癲、性、規訓的深入分析中,以極大的創造性揭示了主體、權力、知識之間的復雜三角關系,對20世紀整個人文學科研究產生了極其深刻而又廣泛的影響,甚至已經出現了一門全新的福柯研究。
福柯的著作某種程度上是當代人文研究的經典著作。無論是文學研究、藝術、法律研究、政治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甚至建築設計學,都深深受到了福柯相關學說和分析的啟發。影響范圍廣。
結集文章自六十年代的文學研究到生前的最后一期訪談,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現福柯的思想全貌。
內容簡介結集的文章主題是關於批判,批判是在哲學周圍不斷成形、擴展、再生的,它指向一種未來哲學,或者暗示著取代所有哲學的可能。對福柯來說,批判的重要性在於:試圖弄清在何種條件下,可以使啟蒙這個問題——即權力、真理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問題——適用於任何歷史時刻。
福柯(1926—1984)是20世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當代學院中的地位無人能及。福柯試圖向人們表明,現代主體是如何在歷史過程中逐漸獲得今日的形象的。對現代主體所作的譜系學探究,使得西方的歷史和文化道路以一種我們不熟悉但又是令人驚異的方式鋪展開來。他的著作也由此對哲學、社會學、史學、文學、政治學、法學和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且改變了這些學科的既定面貌。
目錄
編者前言:如何塑造主體/III
對活人的治理/1
主體性和真理/11
為貞潔而戰/23
自我技術/49
主體和權力/105
論倫理學的譜系學:研究進展一覽/139
安全的危險/191
自我書寫/219
自我關注的倫理學是一種自由實踐/247
何謂直言?/285
說真話的勇氣/373
「我想知道這關涉到什麽」:福柯的*後一次訪談/413
對活人的治理/1
主體性和真理/11
為貞潔而戰/23
自我技術/49
主體和權力/105
論倫理學的譜系學:研究進展一覽/139
安全的危險/191
自我書寫/219
自我關注的倫理學是一種自由實踐/247
何謂直言?/285
說真話的勇氣/373
「我想知道這關涉到什麽」:福柯的*後一次訪談/413
序
如何塑造主體
汪民安
福柯廣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詞與物》和《規訓與懲罰》講述的歷史時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九世紀的現代時期。但是這些歷史的主角不一樣。《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講述的是瘋癲(瘋人)的歷史;《詞與物》講述的是人文科學的歷史;《規訓與懲罰》講述的是懲罰和監獄的歷史。這三個不相關的主題在同一個歷史維度內平行展開。為什麼要講述這些從未被人講過的沉默的歷史?就是為了探索一種「現代主體的譜系學」。因為,正是在瘋癲史、懲罰史和人文科學的歷史中,今天日漸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體形象緩緩浮現。福柯以權力理論聞名於世,但是,他「研究的總的主題,不是權力,而是主體」 。[1]見本套書《主體與權力》一文.即,主體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歷史上到底出現了多少種權力技術和知識來塑造主體?有多少種模式來塑造主體?歐洲兩千多年的文化發明了哪些權力技術和權力/知識,從而塑造出今天的主體和主體經驗?福柯的著作,就是對歷史中各種塑造主體的權力/知識模式的考究。總的來說,這樣的問題可以歸之於尼采式的道德譜系學的范疇,即現代人如何被塑造成型。但是,福柯無疑比尼采探討的領域更為寬廣、具體和細致。
由於福柯探討的是主體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體相關聯,只有在鍛造主體的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福柯的權力和權力/知識。權力/知識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對子:知識被權力生產出來,隨即它又產生權力功能,從而進一步鞏固了權力。知識和權力構成管理和控制的兩位一體,對主體進行塑造成形。就權力/知識而言,福柯有時候將主體塑造的重心放在權力方面,有時候又放在知識方面。如果說,《詞與物》主要考察知識是如何塑造人,或者說,人是如何進入到知識的視野中,並成為知識的主體和客體,從而誕生了一門有關人的科學的;那麼,《規訓與懲罰》則主要討論的是權力是怎樣對人進行塑造和生產的:在此,人是如何被各種各樣的權力規訓機制所捕獲、鍛造和生產?而《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則是知識和權力的合為一體從而對瘋癲進行捕獲:權力制造出關於瘋癲的知識,這種知識進一步加劇和鞏固了對瘋人的禁閉。這是福柯的權力/知識對主體的塑造。
無論是權力對主體的塑造還是知識對主體的塑造,它們的歷史經歷都以一種巴什拉爾所倡導的斷裂方式進行(這種斷裂在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閱讀那里也能看)。在《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理性(人)對瘋癲的理解和處置不斷地出現斷裂: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同瘋癲進行愉快的嬉戲;在古典時期,理性對瘋癲進行譴責和禁閉;在現代時期,理性對瘋癲進行治療和感化。同樣,在《規訓與懲罰》中,古典時期的懲罰是鎮壓和暴力,現代時期的懲罰是規訓和矯正;古典時期的懲罰意象是斷頭台,現代時期的懲罰意象是環形監獄。在《詞與物》中,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是「相似」,古典時期的知識型是「再現」,而現代知識型的標志是「人的誕生」。盡管瘋癲、懲罰和知識型這三個主題迥異,但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它們同時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並且彼此之間遙相呼應:正是在這個時刻,在《詞與物》中,人進入到科學的視野中,作為勞動的、活着的、說話的人被政治經濟學、生物學和語文學所發現和捕捉:人既是知識的主體,也是知識的客體。一種現代的知識型出現了,一種關於人的新觀念出現了,人道主義也就此出現了;那麼,在此刻,懲罰就不得不變得更溫和,歐洲野蠻的斷頭台就不得不退出舞台,更為人道的監獄就一定會誕生;在此刻,對瘋人的嚴酷禁閉也遭到了譴責,更為「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現了,瘋癲不再被視作是需要懲罰的罪惡,而被看做是需要療救的疾病;在此刻,無論是罪犯還是瘋人,都重新被一種人道主義的目光所打量,同時也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方式所處置。顯然,《詞與物》是《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規訓與懲罰》的認識論前提。
無論是對待瘋癲還是對待罪犯,現在不再是壓制和消滅,而是改造和矯正。權力不是在抹去一種主體,而是創造出一種主體。對主體的考察,存在着多種多樣的方式:在經濟學中,主體被置放在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中;在語言學中,主體被置放在表意關系中;而福柯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將主體置放於權力關系中。主體不僅受到經濟和符號的支配,它還受到權力的支配。對權力的考察當然不是從福柯開始,但是,在福柯這里,一種新權力支配模式出現了,它針對的是人們熟悉的權力壓抑模式。壓抑模式幾乎是大多數政治理論的出發點:在馬克思及其龐大的左翼傳統那里,是階級之間的壓制;在洛克開創的自由主義傳統那里,是政府對民眾的壓制;在弗洛伊德,以及試圖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的馬爾庫塞和賴希那里,是文明對性的壓制;甚至在尼采的信徒德勒茲那里,也是社會編碼對欲望機器的壓制。事實上,統治—壓抑模式是諸多的政治理論長期信奉的原理,它的主要表現就是司法模式 —— 政治—法律就是一個統治和壓制的主導機器。因此,20世紀以來各種反壓制的口號就是解放,就是對統治、政權和法律的義無反顧的顛覆。而福柯的權力理論,就是同形形色色的壓抑模式針鋒相對,用他的說法,就是要在政治理論中砍掉法律的頭顱。這種對政治—法律壓抑模式的質疑,其根本信念就是,權力不是令人窒息的壓制和抹殺,而是產出、矯正和造就。權力在制造。
在《性史》第一卷《認知意志》中,福柯直接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壓制模式:在性的領域,壓制模式取得了廣泛的共識,但福柯還是挑釁性地指出,性與其說是被壓制,不如說是被權力所造就和生產:與其說權力在到處追逐和捕獲性,不如說權力在到處滋生和產出性。一旦將權力同壓制性的政治 — 法律進行剝離,或者說,一旦在政治法律之外談論權力,那麼,個體就不僅僅只是被政治和法律的目光所緊緊地盯住,進而成為一個法律主體;相反,他還受制於各種各樣的遍布於社會毛細血管中的權力的鑄造。個體不僅僅被法律塑形,而且被權力塑形。因此,福柯的政治理論,絕對不會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傳統中出沒。實際上,福柯認為政治理論長期以來高估了國家的功能。國家,尤其是現代國家,實際上是並不那麼重要的一種神秘抽象。在他這里,只有充斥着各種權力配置的具體細微的社會機制 —— 他的歷史視野中,幾乎沒有統治性的國家和政府,只有無窮無盡的規訓和治理;幾乎沒有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巨大壓迫,只有遍布在社會中的無所不在的權力矯正;幾乎沒有兩個階級你死我活抗爭的宏大敘事,只有四處涌現的權力及其如影隨形的抵抗。無計其數的細微的權力關系,取代了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普遍性的抽象政治配方。對這些微末的而又無處不在的權力關系的耐心解剖,毫無疑問構成了福柯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這是福柯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的分析。這些分析占據了他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同時,這也是福柯整個譜系學構造中的兩個部分。《詞與物》和《臨床醫學的誕生》討論的是知識對人的建構,《規訓與懲罰》和《古典時代的瘋癲史》關注的是權力對人的建構。不過,對於福柯來說,他的譜系研究不只是這兩個領域,「譜系研究有三個領域。第一,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真理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為知識主體;第二,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權力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為作用於他人的行動主體;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倫理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為道德代理人。」顯然,到此為止,福柯還沒有探討道德主體,怎樣建構為道德主體?什麼是倫理?「你與自身應該保持的那種關系,即自我關系,我稱之為倫理學,它決定了個人應該如何把自己構建成為自身行動的道德主體。」[1] 見本套書《論倫理學的譜系學:研究進展一覽》一文 這種倫理學,正是福柯最后幾年要探討的主題。
在最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福柯轉向了倫理問題,轉向了基督教和古代。為什麼轉向古代?福柯的一切研究只是為了探討現在 —— 這一點,他從康德關於啟蒙的論述中找到了共鳴 —— 他對過去的強烈興趣,只是因為過去是現在的源頭。他試圖從現在一點點地往前逆推:現在的這些經驗是怎樣從過去轉化而來?這就是他的譜系學方法論:從現在往前逆向回溯。在對1 7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作了分析后,他發現,今天的歷史,今天的主體經驗,或許並不僅僅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的產物。因此,他不能將自己限定在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的探討中。對現代社會的這些分析,毫無疑問只是今天經驗的一部分解釋。它並不能說明一切。這正是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差異所在。事實上,十七八世紀的現代社會,以及現代社會涌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權力機制,到底來自何方?他抱着巨大的好奇心以他所特有的譜系學方式一直往前逆推,事實上,越到后來,他越推到了歷史的深處,直至晚年抵達了希臘和希伯來文化這兩大源頭。
這兩大源頭,已經被反復窮盡了。福柯在這里能夠說出什麼新意?不像尼采和海德格爾那樣,他並不以語文學見長。但是,他有他明確的問題框架,將這個問題框架套到古代身上的時候,古代就以完全的不同的面貌出現 —— 幾乎同所有的既定的哲學面貌迥異。福柯要討論的是主體的構型,因此,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之所以受到關注,只是因為它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塑造主體。只不過是,這種主體塑形在現代和古代判然有別。我們看到了,17世紀以來的現代主體,主要是受到權力的支配和塑造。但是,在古代和基督教文化中,權力所寄生的機制並沒有大量產生,只是從17世紀以來,福柯筆下的學校、醫院、軍營、工廠以及它們的集大成者監獄才會大規模地涌現,所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發明和配置(這也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的探討)。同樣,也只是在文藝復興之后的現代社會,語文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等關於人的科學,才在兩個多世紀的漫長歷程中逐漸形成。在古代,並不存在這如此之繁多而精巧的權力機制的鍛造,也不存在現代社會如此之煩瑣的知識型和人文科學的建構,那麼,主體的塑形應該從什麼地方着手?正是在古代,福柯發現了道德主體的建構模式 —— 這也是他的整個譜系學構造中的第三種主體建構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自我技術:在古代,既然沒有過多的外在的權力機制來改變自己,那麼,更加顯而易見的是自我來改變自我。這就是福柯意義上的自我技術:「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1]見本套書《自我技術》一文.通過這樣的自我技術,一種道德主體也因此而成形。
這就是古代社會塑造主體的方式。在古代社會,人們自己來改造自己,雖然這並不意味着不存在外在權力的支配技術(事實上,城邦有它的法律);同樣,現代社會充斥着權力支配技術,但並不意味不存在自我技術(波德萊爾筆下的浪盪子就保有一種狂熱的自我崇拜)。這兩種技術經常結合在一起,相互應用。有時候,權力的支配技術只有借助於自我技術才能發揮作用。不僅如此,這兩種技術也同時貫穿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並在不斷地改變自己的面孔。古代的自我技術在現代社會有什麼樣的表現方式?反過來也可以問,現代的支配技術,是如何在古代醞釀的?重要的是,權力的支配技術和自我的支配技術是否有一個結合?這些問題非常復雜,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非常圖式化地說,如果在70年代,福柯探討的是現代社會怎樣通過權力機制來塑造主體,那麼,在這之后,他着力探討的是古代社會是通過怎樣的自我技術來塑造主體,即人們是怎樣自我改變自我的?自我改變自我的目的何在?技術何在?影響何在?也就是說,在古代存在一種怎樣的自我文化?從希臘到基督教時期,這種自我技術和自我文化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這就是福柯晚年要探討的問題。
汪民安
福柯廣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詞與物》和《規訓與懲罰》講述的歷史時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九世紀的現代時期。但是這些歷史的主角不一樣。《古典時代的瘋癲史》講述的是瘋癲(瘋人)的歷史;《詞與物》講述的是人文科學的歷史;《規訓與懲罰》講述的是懲罰和監獄的歷史。這三個不相關的主題在同一個歷史維度內平行展開。為什麼要講述這些從未被人講過的沉默的歷史?就是為了探索一種「現代主體的譜系學」。因為,正是在瘋癲史、懲罰史和人文科學的歷史中,今天日漸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體形象緩緩浮現。福柯以權力理論聞名於世,但是,他「研究的總的主題,不是權力,而是主體」 。[1]見本套書《主體與權力》一文.即,主體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歷史上到底出現了多少種權力技術和知識來塑造主體?有多少種模式來塑造主體?歐洲兩千多年的文化發明了哪些權力技術和權力/知識,從而塑造出今天的主體和主體經驗?福柯的著作,就是對歷史中各種塑造主體的權力/知識模式的考究。總的來說,這樣的問題可以歸之於尼采式的道德譜系學的范疇,即現代人如何被塑造成型。但是,福柯無疑比尼采探討的領域更為寬廣、具體和細致。
由於福柯探討的是主體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體相關聯,只有在鍛造主體的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福柯的權力和權力/知識。權力/知識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對子:知識被權力生產出來,隨即它又產生權力功能,從而進一步鞏固了權力。知識和權力構成管理和控制的兩位一體,對主體進行塑造成形。就權力/知識而言,福柯有時候將主體塑造的重心放在權力方面,有時候又放在知識方面。如果說,《詞與物》主要考察知識是如何塑造人,或者說,人是如何進入到知識的視野中,並成為知識的主體和客體,從而誕生了一門有關人的科學的;那麼,《規訓與懲罰》則主要討論的是權力是怎樣對人進行塑造和生產的:在此,人是如何被各種各樣的權力規訓機制所捕獲、鍛造和生產?而《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則是知識和權力的合為一體從而對瘋癲進行捕獲:權力制造出關於瘋癲的知識,這種知識進一步加劇和鞏固了對瘋人的禁閉。這是福柯的權力/知識對主體的塑造。
無論是權力對主體的塑造還是知識對主體的塑造,它們的歷史經歷都以一種巴什拉爾所倡導的斷裂方式進行(這種斷裂在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閱讀那里也能看)。在《古典時代的瘋癲史》中,理性(人)對瘋癲的理解和處置不斷地出現斷裂: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同瘋癲進行愉快的嬉戲;在古典時期,理性對瘋癲進行譴責和禁閉;在現代時期,理性對瘋癲進行治療和感化。同樣,在《規訓與懲罰》中,古典時期的懲罰是鎮壓和暴力,現代時期的懲罰是規訓和矯正;古典時期的懲罰意象是斷頭台,現代時期的懲罰意象是環形監獄。在《詞與物》中,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是「相似」,古典時期的知識型是「再現」,而現代知識型的標志是「人的誕生」。盡管瘋癲、懲罰和知識型這三個主題迥異,但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它們同時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並且彼此之間遙相呼應:正是在這個時刻,在《詞與物》中,人進入到科學的視野中,作為勞動的、活着的、說話的人被政治經濟學、生物學和語文學所發現和捕捉:人既是知識的主體,也是知識的客體。一種現代的知識型出現了,一種關於人的新觀念出現了,人道主義也就此出現了;那麼,在此刻,懲罰就不得不變得更溫和,歐洲野蠻的斷頭台就不得不退出舞台,更為人道的監獄就一定會誕生;在此刻,對瘋人的嚴酷禁閉也遭到了譴責,更為「慈善」的精神病院出現了,瘋癲不再被視作是需要懲罰的罪惡,而被看做是需要療救的疾病;在此刻,無論是罪犯還是瘋人,都重新被一種人道主義的目光所打量,同時也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方式所處置。顯然,《詞與物》是《古典時代的瘋癲史》和《規訓與懲罰》的認識論前提。
無論是對待瘋癲還是對待罪犯,現在不再是壓制和消滅,而是改造和矯正。權力不是在抹去一種主體,而是創造出一種主體。對主體的考察,存在着多種多樣的方式:在經濟學中,主體被置放在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中;在語言學中,主體被置放在表意關系中;而福柯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將主體置放於權力關系中。主體不僅受到經濟和符號的支配,它還受到權力的支配。對權力的考察當然不是從福柯開始,但是,在福柯這里,一種新權力支配模式出現了,它針對的是人們熟悉的權力壓抑模式。壓抑模式幾乎是大多數政治理論的出發點:在馬克思及其龐大的左翼傳統那里,是階級之間的壓制;在洛克開創的自由主義傳統那里,是政府對民眾的壓制;在弗洛伊德,以及試圖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的馬爾庫塞和賴希那里,是文明對性的壓制;甚至在尼采的信徒德勒茲那里,也是社會編碼對欲望機器的壓制。事實上,統治—壓抑模式是諸多的政治理論長期信奉的原理,它的主要表現就是司法模式 —— 政治—法律就是一個統治和壓制的主導機器。因此,20世紀以來各種反壓制的口號就是解放,就是對統治、政權和法律的義無反顧的顛覆。而福柯的權力理論,就是同形形色色的壓抑模式針鋒相對,用他的說法,就是要在政治理論中砍掉法律的頭顱。這種對政治—法律壓抑模式的質疑,其根本信念就是,權力不是令人窒息的壓制和抹殺,而是產出、矯正和造就。權力在制造。
在《性史》第一卷《認知意志》中,福柯直接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壓制模式:在性的領域,壓制模式取得了廣泛的共識,但福柯還是挑釁性地指出,性與其說是被壓制,不如說是被權力所造就和生產:與其說權力在到處追逐和捕獲性,不如說權力在到處滋生和產出性。一旦將權力同壓制性的政治 — 法律進行剝離,或者說,一旦在政治法律之外談論權力,那麼,個體就不僅僅只是被政治和法律的目光所緊緊地盯住,進而成為一個法律主體;相反,他還受制於各種各樣的遍布於社會毛細血管中的權力的鑄造。個體不僅僅被法律塑形,而且被權力塑形。因此,福柯的政治理論,絕對不會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傳統中出沒。實際上,福柯認為政治理論長期以來高估了國家的功能。國家,尤其是現代國家,實際上是並不那麼重要的一種神秘抽象。在他這里,只有充斥着各種權力配置的具體細微的社會機制 —— 他的歷史視野中,幾乎沒有統治性的國家和政府,只有無窮無盡的規訓和治理;幾乎沒有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巨大壓迫,只有遍布在社會中的無所不在的權力矯正;幾乎沒有兩個階級你死我活抗爭的宏大敘事,只有四處涌現的權力及其如影隨形的抵抗。無計其數的細微的權力關系,取代了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普遍性的抽象政治配方。對這些微末的而又無處不在的權力關系的耐心解剖,毫無疑問構成了福柯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這是福柯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的分析。這些分析占據了他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同時,這也是福柯整個譜系學構造中的兩個部分。《詞與物》和《臨床醫學的誕生》討論的是知識對人的建構,《規訓與懲罰》和《古典時代的瘋癲史》關注的是權力對人的建構。不過,對於福柯來說,他的譜系研究不只是這兩個領域,「譜系研究有三個領域。第一,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真理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為知識主體;第二,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權力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為作用於他人的行動主體;我們自身的歷史本體論與倫理相關,通過它,我們將自己建構為道德代理人。」顯然,到此為止,福柯還沒有探討道德主體,怎樣建構為道德主體?什麼是倫理?「你與自身應該保持的那種關系,即自我關系,我稱之為倫理學,它決定了個人應該如何把自己構建成為自身行動的道德主體。」[1] 見本套書《論倫理學的譜系學:研究進展一覽》一文 這種倫理學,正是福柯最后幾年要探討的主題。
在最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福柯轉向了倫理問題,轉向了基督教和古代。為什麼轉向古代?福柯的一切研究只是為了探討現在 —— 這一點,他從康德關於啟蒙的論述中找到了共鳴 —— 他對過去的強烈興趣,只是因為過去是現在的源頭。他試圖從現在一點點地往前逆推:現在的這些經驗是怎樣從過去轉化而來?這就是他的譜系學方法論:從現在往前逆向回溯。在對1 7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作了分析后,他發現,今天的歷史,今天的主體經驗,或許並不僅僅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的產物。因此,他不能將自己限定在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現代社會的探討中。對現代社會的這些分析,毫無疑問只是今天經驗的一部分解釋。它並不能說明一切。這正是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差異所在。事實上,十七八世紀的現代社會,以及現代社會涌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權力機制,到底來自何方?他抱着巨大的好奇心以他所特有的譜系學方式一直往前逆推,事實上,越到后來,他越推到了歷史的深處,直至晚年抵達了希臘和希伯來文化這兩大源頭。
這兩大源頭,已經被反復窮盡了。福柯在這里能夠說出什麼新意?不像尼采和海德格爾那樣,他並不以語文學見長。但是,他有他明確的問題框架,將這個問題框架套到古代身上的時候,古代就以完全的不同的面貌出現 —— 幾乎同所有的既定的哲學面貌迥異。福柯要討論的是主體的構型,因此,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之所以受到關注,只是因為它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塑造主體。只不過是,這種主體塑形在現代和古代判然有別。我們看到了,17世紀以來的現代主體,主要是受到權力的支配和塑造。但是,在古代和基督教文化中,權力所寄生的機制並沒有大量產生,只是從17世紀以來,福柯筆下的學校、醫院、軍營、工廠以及它們的集大成者監獄才會大規模地涌現,所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發明和配置(這也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的探討)。同樣,也只是在文藝復興之后的現代社會,語文學、生物學、政治經濟學等關於人的科學,才在兩個多世紀的漫長歷程中逐漸形成。在古代,並不存在這如此之繁多而精巧的權力機制的鍛造,也不存在現代社會如此之煩瑣的知識型和人文科學的建構,那麼,主體的塑形應該從什麼地方着手?正是在古代,福柯發現了道德主體的建構模式 —— 這也是他的整個譜系學構造中的第三種主體建構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自我技術:在古代,既然沒有過多的外在的權力機制來改變自己,那麼,更加顯而易見的是自我來改變自我。這就是福柯意義上的自我技術:「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1]見本套書《自我技術》一文.通過這樣的自我技術,一種道德主體也因此而成形。
這就是古代社會塑造主體的方式。在古代社會,人們自己來改造自己,雖然這並不意味着不存在外在權力的支配技術(事實上,城邦有它的法律);同樣,現代社會充斥着權力支配技術,但並不意味不存在自我技術(波德萊爾筆下的浪盪子就保有一種狂熱的自我崇拜)。這兩種技術經常結合在一起,相互應用。有時候,權力的支配技術只有借助於自我技術才能發揮作用。不僅如此,這兩種技術也同時貫穿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並在不斷地改變自己的面孔。古代的自我技術在現代社會有什麼樣的表現方式?反過來也可以問,現代的支配技術,是如何在古代醞釀的?重要的是,權力的支配技術和自我的支配技術是否有一個結合?這些問題非常復雜,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非常圖式化地說,如果在70年代,福柯探討的是現代社會怎樣通過權力機制來塑造主體,那麼,在這之后,他着力探討的是古代社會是通過怎樣的自我技術來塑造主體,即人們是怎樣自我改變自我的?自我改變自我的目的何在?技術何在?影響何在?也就是說,在古代存在一種怎樣的自我文化?從希臘到基督教時期,這種自我技術和自我文化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這就是福柯晚年要探討的問題。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