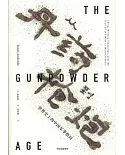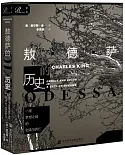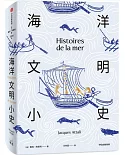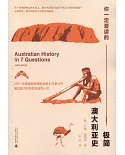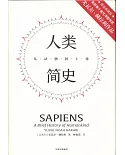德國有心結,一提到猶太人,德國人的腎上腺素水平就會猛增。
君特•格拉斯說,「有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慘痛回憶,德國就應該永遠分裂。」
倘若說人類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應對」的話,那麼德國人總體而言可謂應對自如。戰后德國人曾經「無力哀悼」,然而如今,對國家罪行的內疚轉化成一種美德,對比某些國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為一種優越感的標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麥克阿瑟所說,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個十二歲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這麼說:「日本近代史上沒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廣島和長崎原爆造成的沖擊,日本人在談論戰爭罪時,感到有資格反戈一擊,指責「你們也好不到哪里去」。於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復一年地參拜供奉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員會把教科書里有礙愛國自豪的史實一概閹割干凈。
二戰結束七十年來,當正義的一方歡呼勝利,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危險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表面看來,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徹底反省,日本對侵略責任的抵死不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歷史的陰影下,關於奧斯維辛、廣島、南京這幾個煉獄之所,關於歷史的勝者審判和歷史的紀念泛濫,以及為了實現「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兩個看似迥異的國度,實則都充滿了難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帶。走訪歷史的曖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話語之下的潛台詞,同時作者也不忘一再追問:究竟該由來償還,這罪孽的報應?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1951— ),生於荷蘭海牙,先后在荷蘭和日本就學,曾於萊頓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和歷史,后專注於研究日本。現任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民主、人權與新聞Paul R.Williams教授,為《紐約時報書評》《紐約客》《金融時報》等多家重要媒體撰寫評論。作品涉獵廣泛,最新著作有《零年:1945》《阿姆斯特丹 的謀殺案》等。
目錄
導讀 國家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徐賁
前言
序:敵人們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對西方之戰
第二章 廢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奧斯維辛
第四章 廣島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歷史站上審判席
第七章 教科書風波
第八章 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個正常國家
第十章 兩座正常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別廢墟
注釋
鳴謝
前言
序:敵人們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對西方之戰
第二章 廢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奧斯維辛
第四章 廣島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歷史站上審判席
第七章 教科書風波
第八章 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個正常國家
第十章 兩座正常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別廢墟
注釋
鳴謝
序
敵人們
1991年夏,即兩德統一后第二年,我因為要給一本雜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當地一份報紙里留意到一則告示,說猶太社區中心將舉辦一場講座,演講人是心理學家瑪格麗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講座的題目叫「緬懷的努力:對於無法哀悼的心理學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納粹時期。我本以為講堂最多只會坐一半人,卻發現聽眾不少,且多是年輕人,穿着很隨意,乍看更像是來聽搖滾音樂會的。長長的隊伍一直排到馬路盡頭。對此,我其實不應感到意外。德國人對於戰爭的記憶不僅僅在電視、廣播、社區會堂、學校和博物館里上演着,更是積極地開展圍繞戰爭的檢視、分析和反復剖析。人們有時能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國人的記憶就像一條巨大的舌頭,一遍遍地舔舐,找出那顆隱隱作痛的壞牙。
一些日本人對此困惑不解。一位年邁的德國外交官曾語氣悲涼地向我回憶道,曾有位日本同事告訴他,德國人對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誠懇勁兒,必然會導致喪失德國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輕得多的后生跟我講述了訪問東京時的見聞,說他在啤酒館里聽到日本人唱德軍進行曲時驚得目瞪口呆。我無意誇大這些反差。不是每個日本人都有歷史健忘症,也有不少德國人想要忘記過去,正如有德國人巴不得能在啤酒館里聽到這些老歌再度唱響一樣。然而,我無法想象日本也會有米切利希這樣的人,在東京市中心開辦講座,探討為何「無法哀悼」,還能吸引到這麼多人。日本也沒有一名政客像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遺址下跪的維利•勃蘭特那樣,雙膝跪地,為歷史罪行進行道歉。
所有這一切表明,日本人和德國人之間在對戰爭的看法上存在一道鴻溝——我們這里姑且暫時拋開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之間的區別。問題在於,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德國人的集體記憶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因為文化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不是在戰后歷史,或戰時歷史當中才找得到?或許德國人更有理由哀悼過去?借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話來講,這是不是因為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國人則屬於基督教的「罪文化」?
這些問題有效給出了我的探討范圍。由於引起我興趣的是這些至今仍在德國和日本觸發最激烈爭議的部分,許多著名歷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軍對陣朱可夫將軍(Zhukov)麾下坦克部隊的諾門罕戰役(Nomon han)具有重大的軍事意義,同樣重要的還有英帕爾戰役(Imphal)和諾曼底登陸,但我對這些一概沒有提及。以日本為例,我強調的是侵華戰爭和廣島原爆,這是因為這兩件事相較於其他事件,已經以高度符號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無獨有偶,在談到德國時我着重寫到了排猶,因為是它在(聯邦)德國人的集體記憶上留下了最為敏感的傷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潛艇戰,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在着手寫作本書的時候,我還無法預知之后發生的事將為我的敘事提供一種越來越戲劇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戰結束,接着是德國統一,再接着是海灣戰爭,
最后,1993年的日本大選一舉打破了保守派自民黨的政治壟斷。我決定從海灣戰爭開始寫起,那時我正好身在德國和日本,況且那幾個星期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上一次世界大戰留給兩國的創傷和記憶,甚至連越戰也無法與之相比——盡管兩國都並未受邀參戰。日本和德國的憲法均禁止兩國卷入戰爭,這一安排引發了激烈爭論:他們能不能獲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們自己有沒有自信參與到今后的武裝沖突中來?如今,在我寫作本書的同時,德國飛行員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邏,而日本自衛隊亦在柬埔寨嘗試進行維和,盡管他們還是沒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
我們所處時代有許多陳腔濫調,其中之一是兩個昔日的軸心國輸掉了戰爭,但贏得了和平。許多人忌憚日本和德國的實力。歐洲人害怕德國人占據主導地位。部分美國人已經將日美經濟矛盾形容為一場戰爭。但是如果說其他國家的人對德日兩國的力量寢食難安的話,那麼許多德國人和日本人也一樣。倘若說這兩個民族在戰后依然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身上都殘留着對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國正式統一一事並未在1990年為期一周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引發多少喧囂或喜慶。書展每年都會關注一個特定國家的文學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為書展的一個環節,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之間進行了一場公開討論。兩人都在戰爭期間長大成人,也就是說,都在學校里被灌輸了軍國主義宣傳。他們也因此成為了反法西斯事業的文學倡導者,盡管大江不同於格拉斯,迄今還沒怎麼就政治發過聲。不論如何,他倆都是堅定不移的自由主義者(全書中的「自由主義者」都取美國通行的意義)。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格拉斯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哀嘆德國統一。他說,有了奧斯維辛,德國應該永遠分裂。一個統一的德國對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種危險。大江鄭重其事地點點頭,補充說日本也是個巨大威脅。他說,日本人從未正視過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個種族主義國家。
格拉斯回應說,沒錯,但德國也一樣,在這點上無出其右者,所以德國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實上,德國更糟,不然對波蘭人、土耳其人和外國人的普遍仇視又作何解釋呢?啊,那日本人歧視韓國人和阿伊努人(Ainus)不也一樣麼?所以不對,日本才是最壞的,大江說道。
這一連串細數德國人和日本人不是的「雙簧」進行了有好一會兒,接着對話陷入冷場。兩人都琢磨着還能再說什麼。冷場變成了讓人不快的死寂,人們調整坐姿,等待散場。但緊接着,兩人的思想恰到好處地擦出了火花,他們終於達成一致意見。
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還是大江提出來的,總之有人說到三菱株式會社和戴姆勒—奔馳公司宣布達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關系」。新聞記者戲言其為戴姆勒—三菱軸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嚴肅,口徑一致地稱一段危險的友誼才剛剛開始。隨后格拉斯從椅子里起身,給大江來了個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雖然不太習慣這套,卻也盡力地予以回禮。
1991年夏,即兩德統一后第二年,我因為要給一本雜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當地一份報紙里留意到一則告示,說猶太社區中心將舉辦一場講座,演講人是心理學家瑪格麗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講座的題目叫「緬懷的努力:對於無法哀悼的心理學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納粹時期。我本以為講堂最多只會坐一半人,卻發現聽眾不少,且多是年輕人,穿着很隨意,乍看更像是來聽搖滾音樂會的。長長的隊伍一直排到馬路盡頭。對此,我其實不應感到意外。德國人對於戰爭的記憶不僅僅在電視、廣播、社區會堂、學校和博物館里上演着,更是積極地開展圍繞戰爭的檢視、分析和反復剖析。人們有時能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國人的記憶就像一條巨大的舌頭,一遍遍地舔舐,找出那顆隱隱作痛的壞牙。
一些日本人對此困惑不解。一位年邁的德國外交官曾語氣悲涼地向我回憶道,曾有位日本同事告訴他,德國人對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誠懇勁兒,必然會導致喪失德國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輕得多的后生跟我講述了訪問東京時的見聞,說他在啤酒館里聽到日本人唱德軍進行曲時驚得目瞪口呆。我無意誇大這些反差。不是每個日本人都有歷史健忘症,也有不少德國人想要忘記過去,正如有德國人巴不得能在啤酒館里聽到這些老歌再度唱響一樣。然而,我無法想象日本也會有米切利希這樣的人,在東京市中心開辦講座,探討為何「無法哀悼」,還能吸引到這麼多人。日本也沒有一名政客像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遺址下跪的維利•勃蘭特那樣,雙膝跪地,為歷史罪行進行道歉。
所有這一切表明,日本人和德國人之間在對戰爭的看法上存在一道鴻溝——我們這里姑且暫時拋開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之間的區別。問題在於,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德國人的集體記憶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因為文化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不是在戰后歷史,或戰時歷史當中才找得到?或許德國人更有理由哀悼過去?借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話來講,這是不是因為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國人則屬於基督教的「罪文化」?
這些問題有效給出了我的探討范圍。由於引起我興趣的是這些至今仍在德國和日本觸發最激烈爭議的部分,許多著名歷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軍對陣朱可夫將軍(Zhukov)麾下坦克部隊的諾門罕戰役(Nomon han)具有重大的軍事意義,同樣重要的還有英帕爾戰役(Imphal)和諾曼底登陸,但我對這些一概沒有提及。以日本為例,我強調的是侵華戰爭和廣島原爆,這是因為這兩件事相較於其他事件,已經以高度符號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無獨有偶,在談到德國時我着重寫到了排猶,因為是它在(聯邦)德國人的集體記憶上留下了最為敏感的傷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潛艇戰,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在着手寫作本書的時候,我還無法預知之后發生的事將為我的敘事提供一種越來越戲劇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戰結束,接着是德國統一,再接着是海灣戰爭,
最后,1993年的日本大選一舉打破了保守派自民黨的政治壟斷。我決定從海灣戰爭開始寫起,那時我正好身在德國和日本,況且那幾個星期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上一次世界大戰留給兩國的創傷和記憶,甚至連越戰也無法與之相比——盡管兩國都並未受邀參戰。日本和德國的憲法均禁止兩國卷入戰爭,這一安排引發了激烈爭論:他們能不能獲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們自己有沒有自信參與到今后的武裝沖突中來?如今,在我寫作本書的同時,德國飛行員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邏,而日本自衛隊亦在柬埔寨嘗試進行維和,盡管他們還是沒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
我們所處時代有許多陳腔濫調,其中之一是兩個昔日的軸心國輸掉了戰爭,但贏得了和平。許多人忌憚日本和德國的實力。歐洲人害怕德國人占據主導地位。部分美國人已經將日美經濟矛盾形容為一場戰爭。但是如果說其他國家的人對德日兩國的力量寢食難安的話,那麼許多德國人和日本人也一樣。倘若說這兩個民族在戰后依然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身上都殘留着對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國正式統一一事並未在1990年為期一周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引發多少喧囂或喜慶。書展每年都會關注一個特定國家的文學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為書展的一個環節,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之間進行了一場公開討論。兩人都在戰爭期間長大成人,也就是說,都在學校里被灌輸了軍國主義宣傳。他們也因此成為了反法西斯事業的文學倡導者,盡管大江不同於格拉斯,迄今還沒怎麼就政治發過聲。不論如何,他倆都是堅定不移的自由主義者(全書中的「自由主義者」都取美國通行的意義)。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格拉斯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哀嘆德國統一。他說,有了奧斯維辛,德國應該永遠分裂。一個統一的德國對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種危險。大江鄭重其事地點點頭,補充說日本也是個巨大威脅。他說,日本人從未正視過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個種族主義國家。
格拉斯回應說,沒錯,但德國也一樣,在這點上無出其右者,所以德國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實上,德國更糟,不然對波蘭人、土耳其人和外國人的普遍仇視又作何解釋呢?啊,那日本人歧視韓國人和阿伊努人(Ainus)不也一樣麼?所以不對,日本才是最壞的,大江說道。
這一連串細數德國人和日本人不是的「雙簧」進行了有好一會兒,接着對話陷入冷場。兩人都琢磨着還能再說什麼。冷場變成了讓人不快的死寂,人們調整坐姿,等待散場。但緊接着,兩人的思想恰到好處地擦出了火花,他們終於達成一致意見。
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還是大江提出來的,總之有人說到三菱株式會社和戴姆勒—奔馳公司宣布達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關系」。新聞記者戲言其為戴姆勒—三菱軸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嚴肅,口徑一致地稱一段危險的友誼才剛剛開始。隨后格拉斯從椅子里起身,給大江來了個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雖然不太習慣這套,卻也盡力地予以回禮。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