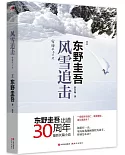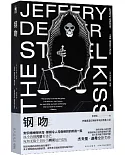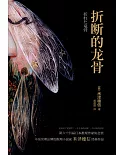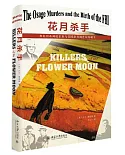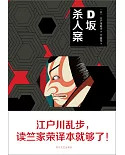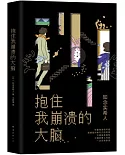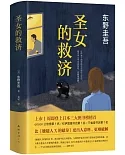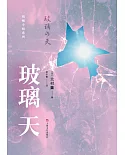「我們有兩種記憶,小記憶與大記憶。我們用小記憶來記住小事情,用大記憶來忘記大事情。」——《德國小鎮》。再過十天,英國在歐洲的權力命運即將確定,在這草木皆兵的一刻,駐波恩英國大使館里一個卑微的德裔檔案管理員,卻突然人間蒸發,館內的相關機密文件也無端消失。結束同盟國瓜分占領的德國,民族意識抬頭,新納粹主義蠢蠢欲動,排英的情緒日益高漲。置身水火之境的英國遂秘密指派精干人員特納尋找真相。然而調查過程中,特納面臨的最大阻礙竟是自己人?!而一個檔案管理員的失蹤及其攜帶的秘密,是否就牽動着整個歐洲的未來?
約翰•勒卡雷,原名大衛•康威爾(David
Cornwell)。1931年生於英國。18歲便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后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之后於伊頓公學教授法文與德文。1959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同時開始寫作。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柏林諜影》一舉成名,知名小說家格林如此盛贊:「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間諜小說!」從此奠定文壇大師地位。迄今共著書22部,有3部入選美國推理作家協會「十佳間諜小說」,4部入選「百佳犯罪推理小說」,獲獎無數,是這個領域當之無愧的王者。
勒卡雷是塑造人物的大師,筆下的特工主角喬治•史邁利已成為英國文學史上與福爾摩斯相媲美的經典形象。此外,因其作品具備深沉的道德關懷、生動的人性刻畫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被評論界稱為「在世最好的英語小說家之一」。
勒卡雷既是「冷戰時代的小說家」,也是當代一流的國際觀察家,富有想象力的社會歷史學者。曾是阿拉法特的座上賓,小布什的批評者,至今仍以他清醒的洞見對當今世界發揮着影響力。
獲獎記錄:1963年,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CWA)金匕首獎。1964年,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1965年,愛德加獎。1977年,CWA金匕首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1984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MWA)大師獎。1988年,CWA鑽石匕首獎(終身成就獎),意大利MalapartePrize2005年,CWA50年最佳金匕首獎。
目錄
自序
前言獵人與獵物
梅多斯先生與科克先生
「我可以在話筒里聽到人群的尖叫聲……」
阿倫•特納
12月的續約
約翰•岡特
記憶人
萊爾
珍妮•帕吉特
罪惡的星期四
布拉德菲爾德家的「文化」
柯尼希斯溫特
「利奧就在那里•在二等座。」
巴不得被當成豬
星期四之子
光榮洞
「徹頭徹尾的假貨」
普蘭什科
尾聲
前言獵人與獵物
梅多斯先生與科克先生
「我可以在話筒里聽到人群的尖叫聲……」
阿倫•特納
12月的續約
約翰•岡特
記憶人
萊爾
珍妮•帕吉特
罪惡的星期四
布拉德菲爾德家的「文化」
柯尼希斯溫特
「利奧就在那里•在二等座。」
巴不得被當成豬
星期四之子
光榮洞
「徹頭徹尾的假貨」
普蘭什科
尾聲
序
我對《德國小鎮》這書一向懷有惡感,也想不出能為它說些什麼好話,直到我開始想起它的三個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觀。他們是:前難民黑廷、尖刻的實用主義英國外交官布拉德菲爾德、有驅迫感和不快樂的調查員阿倫•特納(我私底下把這個角色編派給自己)。想起他們,我才不得不勉為其難承認:這小說畢竟已達成我當初想達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為的,是個礙眼物。
我厭惡這小說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擬寫的是一部近似諷刺英國政治風格的黑色喜劇,但出來的結果卻廣被認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納(西德第一任總理)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標准看都算不上太可愛。希特勒時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納本人的幕后操盤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納粹歧視猶太人的《紐倫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黨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協助納粹把法國猶太人從巴黎運到集中營,熱情洋溢的佐格爾曼(Zogelmann)之前還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高干,而這也不過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報界、軍界、工業界、科學界和教育界里,納粹的舊人俯拾皆是。他們之所以被留下來,若不是因為沒有犯過合該清算的大罪,就是因為被認為是西德戰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時候則是出於北約盟國舊事不重提的默契,聽任他們的檔案塵封在某個人的抽屜里。
對我這樣從兒時起就着迷於德國文化與歷史的英國年輕人來說,60年代初期的波恩確實是個鬼影陰森的地方。有時候,這城市的街道給人的感覺是匆匆鋪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給稍事掩埋,就像是貝爾森(Belsen)集中營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齊漂亮,下面覆蓋着無辜死難者的喑啞痛苦。如果你仔細觀察,波恩的怪異隨處可見:從那些年過五十的人緊綳的臉上(「媽媽,戰爭時你在做什麼?」),從一棟你突然認出的未拆除的納粹建築,從德國官員或國會議員不經意脫口而出的一句納粹用語。很多時候,呼吁忘掉過去的口號就像波恩正忙着遺忘納粹的口號一樣刺耳。在德國,「克服過去」一語是會發出軍隊調動時的鏗鏗聲的。德國人就像英國人一樣,說話總是帶有自己的調調。
因為當時是英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我常常得坐在德國國會的二樓外交官旁聽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發言稿,耳里聽着一通通乏味的發言,我會聽任思緒游走,飄過牆壁地板,飄到坐在我幾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陰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麼樣的集體記憶(有光榮的、有悲哀的、有恥辱的)構成他們的人生經驗的。他們一個個走向講台時,我打量他們漠然的面孔和自覺的舉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暢所欲言,他們會說出什麼樣的話來?
因為是英國人,因為或多或少都吃過德國國家主義耀武揚威的苦頭,所以我們當時仍然疑惑:他們現在是誰了?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他們有可能會在這個世紀里發動第三次戰爭嗎?
這種疑惑依然纏繞着我們,於今為甚。大眾報刊會把這種疑慮大聲說出來,而我們的智囊團或領導人則會在白廳(Whitehall,英國的政府部會)那些秘密會議室里靜悄悄地把它說出來。
但也不總是那麼靜悄悄。幾個月前,一個焦慮的德國了望者團體才在契克斯(Chequers,英國首相的鄉間別墅)集會,討論這個超難搞的德國問題(后來他們中的一個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過這樣的集會)。他們的問題大略如此:統一的德國將會在歐共體里取得超強的地位,到時她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能信任她嗎?她會怎樣利用自己的力量?
會議的結論並不特別高明,而它們反映出的英國人性格就像德國人性格一樣多。奇異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經過冷戰多個回合的交鋒和我們(出於深信德國不可能統一)反復重申支持一個統一的德國之后,我們也在問自己同一組浮誇的問題,盡管用語稍有不同。德國統一的話,地會裂開來嗎?我們這樣問彼此。巨大的過去會沖破紙一樣薄的表面嗎?德國的經濟奇跡還能忍受得了戰敗的緊身衣多久,繼續惟北約之命是從?
而我們給自己的回答總是一樣:只要他們繼續富有,他們就會忍耐;只要德國錢繼續淹腳踝,只要德國人能繼續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膚曬成古銅色,我們就沒什麼好害怕的。
然而,當我們把免稅威士忌繼續灌進他們喉嚨,聆聽他們對德國問題的獨白和宣示永遠親英的承諾時,我們卻總是像盤旋的鷹隼一樣,搜尋德國人第一個背信的征兆。他們會偷偷摸摸背着我們去跟俄國人做交易嗎?他們會答應用一個不結盟的德國來交換一個統一的德國嗎?他們不是沒有試過這樣做,只是每一次都沒有充分的決心罷了。阿登納與戴高樂之間的眉來眼去是一個弱化英美對德國鉗制的陰謀嗎?英國第一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失敗后,我親耳聽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英國首相)說:「戴高樂想要的東西跟我們一樣,卻不想讓我們有份。」而每一次,當有極右派的政治集團冒出來(不管是出現在巴伐利亞州、石荷州或任何一個反猶主義或泛日耳曼主義的溫床),我們就會馬上發電報向倫敦報告,評估事情對當前的德國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回想起來,那時我們都簡單得可以。
但別忘了,那時候的外交官都是業余出身。他們不是政治家,不是受過訓練的分析家或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或律師或歷史學家。他們大部分都是劍橋、牛津的文科畢業生,被當成專家派駐各地的大使館,而他們往往會擇錯固執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而我們駐波恩的大使館和我們駐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館沒什麼兩樣:是一座對其駐在國深深不信任的英國要塞。它的風格和偏見跟從前英國鄉下人對城市的敵視沒兩樣。總之,那是一個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國人繼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者自居的心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個較謙卑和較務實的角色,以爭取德國支持我們加入歐共體。讓事情更復雜化的是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和我們以四強身份對德國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監管。那時我們大使館最佳的德國專家是一個曾被關在寇地茲堡戰俘營(時位於東德)而后逃出的戰俘。我們的參贊(參贊處是大使館的政治部門)是勛章多多的皇家海軍前潛艇艇長。我們很多本地雇員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大戰前逃離德國,然后像黑廷一樣,在戰后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回到德國。我經歷的兩位大使都曾任職於莫斯科,秘密參與過制定冷戰對策的最內部會議。因此,當時大使館的氣氛就像這小說里描繪的:在尼布龍[1]薄霧的濡濕重量下,每個人都神經兮兮,充滿怨氣。
要在這個世界里抽出一根線頭,把它編織成一個故事,事實證明是極度困難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發展只是困難之一。理論上,我想寫的是一個過去纏繞着現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們對一個我們前不久才打敗的國家的日益依賴,而且要能道出我們對一種悶燒在富裕表面下的國家主義激情可能復活的焦慮。但這種復活會以何種形式出現呢?我當然不相信納粹會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來,不相信它的老守護者會戲劇性地重新得勢。我毋寧相信,如果威脅存在的話,它是存在於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現形式會是一個以憤懣的老板與小布爾喬亞為骨干的群眾運動——類似於布爾熱在法國領導的那一個。我也察覺到失意的德國年輕人的深深不滿,他們開始把怒氣的矛頭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對北約的俯首帖耳。今天還有人記得紅色丹尼(Danny the Red,1968年巴黎五月學運的領導人)嗎?
我對這些潮流最后會演變成什麼樣子的臆測,現已明白是錯的。但我有一點卻是猜對了:會有一個學生運動把無力的怒火撥向德國建制——哪怕它后來發展出巴德-邁因霍夫團伙(Baader-Meinhof,1970年代的西德恐怖集團)這種極端的形式——而且會得到德國知識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對的另一點是,這股力量本質上是不關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種模糊、未完成的無政府主義修辭,沒有明確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動本身。
但不管怎樣,我本來就沒有預期自己的預測是對的。我想提供的是一個有啟發性的夢魘,而非精確的預言。我想講的是一個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寫得是好是壞,我寫出來的也正是個政治鬼故事。
這鬼故事里的鬼當然就是利奧•黑廷。阿倫•特納是他的招魂師,而勞利•布拉德菲爾德則是倒霉的鬼屋主人。這三個角色在現實中都是沒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盡管在我任職大使館的時代,德國各地有幾十個類似黑廷的人,繼續在他們小小一間的。
前管制委員會的辦公室里——哪怕占領已經結束了許久——以別的名義發揮功能。也沒有戴綠帽的布拉德菲爾德這樣的人指揮過我們的參贊處;或有過一個來自倫敦的阿倫•特納,把我們的生活撕成碎片。至於旁觀這一切的那個慵懶、聰明的同性戀者萊爾,當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
但雲格爾先生卻是活過的。他是真實的,盡管其名字與長相你在本書任何地方都不會找到。雲格爾先生是我們大使館里的兩個打雜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們今天還有這樣的人員嗎?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賭還有。雲格爾先生在大使館一樓有一個辦公室,他的工作是為你的汽車申請一塊外交官車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優惠機票,還可以私底下幫你買到打折和免稅的新收音機、電視機、洗碗機、荷蘭啤酒或蘇格蘭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憐兮兮的吹風機當然更不在話下。
雲格爾先生年老,頭發柔軟光潔,和藹,耐性過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聲使喚,也幾乎不皺一下眉頭。有別於所有人的猜想,我個人深信雲格爾先生從未在幫我們的忙中撈油水。他會熱心助人,只是因為急於討好別人。所以我就偷了雲格爾先生的吹風機,還有一點點他與雇主的關系,放到利奧•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奧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雲格爾先生是不是曉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過,十五年前我倒是相當意外地在科隆機場重遇他。
他比我記得的樣子老更多了,皺巴巴的皮膚不再粗糙,變得嬰兒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廳里角落上的桌子邊,一邊細口喝啤酒,一邊看着現代世界運轉,樣子就像已經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終於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輕輕一握,輕輕喊出我的名字。他身邊沒有行李,甚至沒有人人必備的德國手提箱。他穿着費爾島(FairIsle)花樣的開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補丁,大概是多年前從他某本郵購目錄上購買的。他看起來英國味十足。
「你要去哪兒旅行,雲格爾先生?」我問他。
沒有要去哪兒,他微笑着回答說。他說他幾乎每星期六都會來這里。有時星期天也會來。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經過世。顯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來這里收集寫小說的材料啰?」我開玩笑地問他。不是,先生,我不寫小說;他帶着另一個微笑回答說。「但你一整天坐在這里,又不看書,你是要干些什麼呢,雲格爾先生?」我不解地說,「難道你是間諜不成?」這時,他舉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聲。「聽着。」他說,臉上仍然掛着微笑。
於是我默不作聲,露出一張洗耳恭聽的臉。接着你猜我聽到什麼來着?我聽到有一個男聲用幾種語言廣播說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請在某某登機口登機。
「那是我兒子。」他說,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難忘。我這才明白,他舉起的手指是指着廣播喇叭的。
本書的初稿寫成於維也納。在那里,我得到着名納粹搜捕者維森塔爾(SimonWiesenthal)之助,把壞蛋角色卡費爾德的齷齪老底給拼湊了出來。我住的是已故指揮家卡拉揚(Karajan)的公寓。這純屬巧合。剛開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門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似的,會自動打開。我后來才知道,之所以有這種設計,是因為那位大指揮家演出完畢時常常脾氣暴躁,沒耐心去開門。
在維也納,我也有機會聽到原汁原味的反猶主義語言,它們讓我更知道應該怎樣描寫那些波恩老納粹的嘴臉。「如果你想研究這種疾病,」維森塔爾建議說,「你就得住在沼澤里。」他指的沼澤是維也納。回到英國時,我的小說仍然沒有完成,而有好幾次,我覺得自己離把它寫完只有一步之遙。那是我生命中的離婚時期,而這事對我和我那可憐忠實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經驗。這書阻礙了我,而我也阻礙了這本書。我反復想:我去過那麼多地方,干嗎要費事去描述一個我想象出來的呢?如果你想讓阿倫•特納向你解釋,大概你應該想象一下我或你自己:我們看過那麼多,感受過那麼多,卻又抗拒每一個我們得自感官的合理結論。
然后有一天,我極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國制手提箱里裝着好幾磅重的小說書稿。我住進雷馬根(Remagen)一個可以俯瞰萊茵河的飯店房間。記得雷馬根那座大橋嗎?你們有必要記得嗎?但這大橋卻見證過美軍和德軍之間最激烈的一場戰事,而盟軍就是從它渡過萊茵河的。
我在雷馬根得到一個親切小天使的幫助,把小說寫竣殺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計划要寫的那部書。但我本來要寫的那部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我厭惡這小說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擬寫的是一部近似諷刺英國政治風格的黑色喜劇,但出來的結果卻廣被認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納(西德第一任總理)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標准看都算不上太可愛。希特勒時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納本人的幕后操盤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納粹歧視猶太人的《紐倫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黨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協助納粹把法國猶太人從巴黎運到集中營,熱情洋溢的佐格爾曼(Zogelmann)之前還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高干,而這也不過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報界、軍界、工業界、科學界和教育界里,納粹的舊人俯拾皆是。他們之所以被留下來,若不是因為沒有犯過合該清算的大罪,就是因為被認為是西德戰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時候則是出於北約盟國舊事不重提的默契,聽任他們的檔案塵封在某個人的抽屜里。
對我這樣從兒時起就着迷於德國文化與歷史的英國年輕人來說,60年代初期的波恩確實是個鬼影陰森的地方。有時候,這城市的街道給人的感覺是匆匆鋪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給稍事掩埋,就像是貝爾森(Belsen)集中營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齊漂亮,下面覆蓋着無辜死難者的喑啞痛苦。如果你仔細觀察,波恩的怪異隨處可見:從那些年過五十的人緊綳的臉上(「媽媽,戰爭時你在做什麼?」),從一棟你突然認出的未拆除的納粹建築,從德國官員或國會議員不經意脫口而出的一句納粹用語。很多時候,呼吁忘掉過去的口號就像波恩正忙着遺忘納粹的口號一樣刺耳。在德國,「克服過去」一語是會發出軍隊調動時的鏗鏗聲的。德國人就像英國人一樣,說話總是帶有自己的調調。
因為當時是英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我常常得坐在德國國會的二樓外交官旁聽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發言稿,耳里聽着一通通乏味的發言,我會聽任思緒游走,飄過牆壁地板,飄到坐在我幾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陰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麼樣的集體記憶(有光榮的、有悲哀的、有恥辱的)構成他們的人生經驗的。他們一個個走向講台時,我打量他們漠然的面孔和自覺的舉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暢所欲言,他們會說出什麼樣的話來?
因為是英國人,因為或多或少都吃過德國國家主義耀武揚威的苦頭,所以我們當時仍然疑惑:他們現在是誰了?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他們有可能會在這個世紀里發動第三次戰爭嗎?
這種疑惑依然纏繞着我們,於今為甚。大眾報刊會把這種疑慮大聲說出來,而我們的智囊團或領導人則會在白廳(Whitehall,英國的政府部會)那些秘密會議室里靜悄悄地把它說出來。
但也不總是那麼靜悄悄。幾個月前,一個焦慮的德國了望者團體才在契克斯(Chequers,英國首相的鄉間別墅)集會,討論這個超難搞的德國問題(后來他們中的一個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過這樣的集會)。他們的問題大略如此:統一的德國將會在歐共體里取得超強的地位,到時她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能信任她嗎?她會怎樣利用自己的力量?
會議的結論並不特別高明,而它們反映出的英國人性格就像德國人性格一樣多。奇異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經過冷戰多個回合的交鋒和我們(出於深信德國不可能統一)反復重申支持一個統一的德國之后,我們也在問自己同一組浮誇的問題,盡管用語稍有不同。德國統一的話,地會裂開來嗎?我們這樣問彼此。巨大的過去會沖破紙一樣薄的表面嗎?德國的經濟奇跡還能忍受得了戰敗的緊身衣多久,繼續惟北約之命是從?
而我們給自己的回答總是一樣:只要他們繼續富有,他們就會忍耐;只要德國錢繼續淹腳踝,只要德國人能繼續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膚曬成古銅色,我們就沒什麼好害怕的。
然而,當我們把免稅威士忌繼續灌進他們喉嚨,聆聽他們對德國問題的獨白和宣示永遠親英的承諾時,我們卻總是像盤旋的鷹隼一樣,搜尋德國人第一個背信的征兆。他們會偷偷摸摸背着我們去跟俄國人做交易嗎?他們會答應用一個不結盟的德國來交換一個統一的德國嗎?他們不是沒有試過這樣做,只是每一次都沒有充分的決心罷了。阿登納與戴高樂之間的眉來眼去是一個弱化英美對德國鉗制的陰謀嗎?英國第一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失敗后,我親耳聽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英國首相)說:「戴高樂想要的東西跟我們一樣,卻不想讓我們有份。」而每一次,當有極右派的政治集團冒出來(不管是出現在巴伐利亞州、石荷州或任何一個反猶主義或泛日耳曼主義的溫床),我們就會馬上發電報向倫敦報告,評估事情對當前的德國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回想起來,那時我們都簡單得可以。
但別忘了,那時候的外交官都是業余出身。他們不是政治家,不是受過訓練的分析家或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或律師或歷史學家。他們大部分都是劍橋、牛津的文科畢業生,被當成專家派駐各地的大使館,而他們往往會擇錯固執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而我們駐波恩的大使館和我們駐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館沒什麼兩樣:是一座對其駐在國深深不信任的英國要塞。它的風格和偏見跟從前英國鄉下人對城市的敵視沒兩樣。總之,那是一個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國人繼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者自居的心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個較謙卑和較務實的角色,以爭取德國支持我們加入歐共體。讓事情更復雜化的是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和我們以四強身份對德國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監管。那時我們大使館最佳的德國專家是一個曾被關在寇地茲堡戰俘營(時位於東德)而后逃出的戰俘。我們的參贊(參贊處是大使館的政治部門)是勛章多多的皇家海軍前潛艇艇長。我們很多本地雇員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大戰前逃離德國,然后像黑廷一樣,在戰后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回到德國。我經歷的兩位大使都曾任職於莫斯科,秘密參與過制定冷戰對策的最內部會議。因此,當時大使館的氣氛就像這小說里描繪的:在尼布龍[1]薄霧的濡濕重量下,每個人都神經兮兮,充滿怨氣。
要在這個世界里抽出一根線頭,把它編織成一個故事,事實證明是極度困難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發展只是困難之一。理論上,我想寫的是一個過去纏繞着現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們對一個我們前不久才打敗的國家的日益依賴,而且要能道出我們對一種悶燒在富裕表面下的國家主義激情可能復活的焦慮。但這種復活會以何種形式出現呢?我當然不相信納粹會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來,不相信它的老守護者會戲劇性地重新得勢。我毋寧相信,如果威脅存在的話,它是存在於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現形式會是一個以憤懣的老板與小布爾喬亞為骨干的群眾運動——類似於布爾熱在法國領導的那一個。我也察覺到失意的德國年輕人的深深不滿,他們開始把怒氣的矛頭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對北約的俯首帖耳。今天還有人記得紅色丹尼(Danny the Red,1968年巴黎五月學運的領導人)嗎?
我對這些潮流最后會演變成什麼樣子的臆測,現已明白是錯的。但我有一點卻是猜對了:會有一個學生運動把無力的怒火撥向德國建制——哪怕它后來發展出巴德-邁因霍夫團伙(Baader-Meinhof,1970年代的西德恐怖集團)這種極端的形式——而且會得到德國知識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對的另一點是,這股力量本質上是不關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種模糊、未完成的無政府主義修辭,沒有明確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動本身。
但不管怎樣,我本來就沒有預期自己的預測是對的。我想提供的是一個有啟發性的夢魘,而非精確的預言。我想講的是一個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寫得是好是壞,我寫出來的也正是個政治鬼故事。
這鬼故事里的鬼當然就是利奧•黑廷。阿倫•特納是他的招魂師,而勞利•布拉德菲爾德則是倒霉的鬼屋主人。這三個角色在現實中都是沒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盡管在我任職大使館的時代,德國各地有幾十個類似黑廷的人,繼續在他們小小一間的。
前管制委員會的辦公室里——哪怕占領已經結束了許久——以別的名義發揮功能。也沒有戴綠帽的布拉德菲爾德這樣的人指揮過我們的參贊處;或有過一個來自倫敦的阿倫•特納,把我們的生活撕成碎片。至於旁觀這一切的那個慵懶、聰明的同性戀者萊爾,當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
但雲格爾先生卻是活過的。他是真實的,盡管其名字與長相你在本書任何地方都不會找到。雲格爾先生是我們大使館里的兩個打雜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們今天還有這樣的人員嗎?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賭還有。雲格爾先生在大使館一樓有一個辦公室,他的工作是為你的汽車申請一塊外交官車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優惠機票,還可以私底下幫你買到打折和免稅的新收音機、電視機、洗碗機、荷蘭啤酒或蘇格蘭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憐兮兮的吹風機當然更不在話下。
雲格爾先生年老,頭發柔軟光潔,和藹,耐性過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聲使喚,也幾乎不皺一下眉頭。有別於所有人的猜想,我個人深信雲格爾先生從未在幫我們的忙中撈油水。他會熱心助人,只是因為急於討好別人。所以我就偷了雲格爾先生的吹風機,還有一點點他與雇主的關系,放到利奧•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奧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雲格爾先生是不是曉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過,十五年前我倒是相當意外地在科隆機場重遇他。
他比我記得的樣子老更多了,皺巴巴的皮膚不再粗糙,變得嬰兒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廳里角落上的桌子邊,一邊細口喝啤酒,一邊看着現代世界運轉,樣子就像已經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終於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輕輕一握,輕輕喊出我的名字。他身邊沒有行李,甚至沒有人人必備的德國手提箱。他穿着費爾島(FairIsle)花樣的開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補丁,大概是多年前從他某本郵購目錄上購買的。他看起來英國味十足。
「你要去哪兒旅行,雲格爾先生?」我問他。
沒有要去哪兒,他微笑着回答說。他說他幾乎每星期六都會來這里。有時星期天也會來。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經過世。顯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來這里收集寫小說的材料啰?」我開玩笑地問他。不是,先生,我不寫小說;他帶着另一個微笑回答說。「但你一整天坐在這里,又不看書,你是要干些什麼呢,雲格爾先生?」我不解地說,「難道你是間諜不成?」這時,他舉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聲。「聽着。」他說,臉上仍然掛着微笑。
於是我默不作聲,露出一張洗耳恭聽的臉。接着你猜我聽到什麼來着?我聽到有一個男聲用幾種語言廣播說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請在某某登機口登機。
「那是我兒子。」他說,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難忘。我這才明白,他舉起的手指是指着廣播喇叭的。
本書的初稿寫成於維也納。在那里,我得到着名納粹搜捕者維森塔爾(SimonWiesenthal)之助,把壞蛋角色卡費爾德的齷齪老底給拼湊了出來。我住的是已故指揮家卡拉揚(Karajan)的公寓。這純屬巧合。剛開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門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似的,會自動打開。我后來才知道,之所以有這種設計,是因為那位大指揮家演出完畢時常常脾氣暴躁,沒耐心去開門。
在維也納,我也有機會聽到原汁原味的反猶主義語言,它們讓我更知道應該怎樣描寫那些波恩老納粹的嘴臉。「如果你想研究這種疾病,」維森塔爾建議說,「你就得住在沼澤里。」他指的沼澤是維也納。回到英國時,我的小說仍然沒有完成,而有好幾次,我覺得自己離把它寫完只有一步之遙。那是我生命中的離婚時期,而這事對我和我那可憐忠實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經驗。這書阻礙了我,而我也阻礙了這本書。我反復想:我去過那麼多地方,干嗎要費事去描述一個我想象出來的呢?如果你想讓阿倫•特納向你解釋,大概你應該想象一下我或你自己:我們看過那麼多,感受過那麼多,卻又抗拒每一個我們得自感官的合理結論。
然后有一天,我極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國制手提箱里裝着好幾磅重的小說書稿。我住進雷馬根(Remagen)一個可以俯瞰萊茵河的飯店房間。記得雷馬根那座大橋嗎?你們有必要記得嗎?但這大橋卻見證過美軍和德軍之間最激烈的一場戰事,而盟軍就是從它渡過萊茵河的。
我在雷馬根得到一個親切小天使的幫助,把小說寫竣殺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計划要寫的那部書。但我本來要寫的那部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