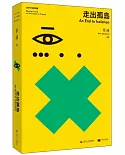回首琴史,一九二五實在是平淡的一年。春夏之際,在北京,琴壇祭酒楊時百開雕《藏琴錄》,作為他的皇皇巨著《琴學叢書》之一種;知情者卻透露,楊時百打算將收藏的珍貴古琴賣給一位大官僚,這正是他應邀而寫的說明書。在上海,大富商、大收藏家及琴人周慶雲,似乎整年都沉浸在與文友往還、唱和的樂趣之中,卻無心再現五年前召集晨風廬琴會的榮光。重陽節前三天,長沙南薰琴社的彭祉卿為接待來自北京的同門李伯仁,約集多位琴友會琴于岳麓山。雖稱盛集,也不過是知音之間的酬唱,無關大局;座中的青年查阜西還籍籍無名,崢嶸未露。琴壇寂寞,意外的是,這年十月下旬,文苑重地《晨報副鐫》卻發生了一場關于古琴的論爭,交手雙方竟是兩位留洋的現代知識分子,且同為著名的文學團體新月社的成員︰作家陳西瀅、考古學家李濟。
陳西瀅、李濟的論爭文字恰為本書的起首兩篇,似乎有著特殊的意義。同樣是留洋,陳西瀅西化程度較深,他的態度,本質上是以西方文化觀念為標準,質疑古琴的藝術價值;而李濟少小學琴,曾一度師從楊時百的老師黃勉之,後來又寫過學術分量很足的古琴論文,在海外所學雖是異域的研究方法,歸來研究的對象卻不離本土,對古琴自然多一份理解之同情。差不多同一代人,經歷相似而情懷各異,本不足奇。但就在他們辯駁的時代,正規而系統的西方音樂教育模式才開始在中國推廣,而數十年間,卻已勢不可擋地成為音樂主流,中國人的欣賞習慣與藝術觀念也日益向西方傾斜,在許多場合,也許陳西瀅的觀點更能引起共鳴;這一過程中,傳統的民族音樂也經歷了被弱化、迎接挑戰和建立起符合本民族藝術特征的理論的蛻變,如今李濟的認知若廣為人知,恐怕亦不乏認同者。陳、李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無論是保守或激進、留洋或留守,都有一種用新眼光反思、梳理傳統的意識,差別只在態度與立場。古琴作為“國故”,當然在“整理”之列,如何整理,卻需要長期的探索。因此,報章邊角的爭論雖在一時,卻多少折射了幾十年現實的文化背景。而這本小集子,輯錄的僅是白話文寫就的零散隨筆(論文與文言作品、已收入古琴專著及譯自外文的概不在考慮之列),大半作品仍然具備這一整理、審視的姿態,不能不說是時代使然。
本書輯錄文章的年限是民國,卻有一個小小的例外——最末一篇《國樂的經驗》,發表于新中國肇始將近一周年的光景。知堂的文章當然絕佳,硬要以此為破例之由亦無不可,但仍需說明的是,這篇短文,事情是舊的,“經驗”是舊的,氣息也是舊的,更妙者竟與陳、李的話題遙相呼應。知堂大約不會喜歡陳西瀅這些“大人先生”,談起古琴倒有幾分契合,不同者知堂不動聲色,而陳西瀅富于英倫隨筆的瀟灑派頭。古琴在主流文化中素來倍受尊崇,近代以降卻如此時運不濟。小集子以陳西瀅始,以知堂終,其間的曲折山水、幽明襟抱,豈不令人感慨遙深。再過得幾年,鄧拓寫《听琴記》,已全然是另一番筆墨了。故知堂的文章雖略過時限,于體例亦未嘗多違也。
本書文凡十一篇,記述人事,論說琴樂,出入今昔,參差可喜。由于散落各處,絕大多數未為古琴愛好者及研究者所知。前些年出版的《二十世紀古琴文論目錄》可謂搜羅宏富,于之亦付闕如。此次整理時,除徑直校正某些明顯的錯訛,以“□”代替個別無法辨識的字詞,調整少量標點,其余都遵從當時的遣詞、標點習慣,以求不失歷史文獻的本來面貌。全書以發表時間為序排次,並于每篇末注明原刊(書)刊名及期號,或將有助于進一步的核查與探究。而十位作者中的六人,悉數由最初發表時所署的字號、筆名改為今日讀者較為熟悉的通行名字(“西瀅”改為“陳西瀅”,“李濟之”改為“李濟”,“栩齋”改為“莊劍丞”,“勾芒”改為“辛豐年”,“凡鳥”改為“李恩績”,“持光”改為“周作人”),文末不再一一注明。
十位作者中,如今在世的,可能只有年近九旬的辛豐年一人了,寫《古琴》一文時才二十出頭,可能正是他沉迷于西樂後又“發現”了古琴,發奮自學的年歲。前些年將這篇文章挖掘出來重新發表,問他想不想補充說點什麼,他寫道︰“文字是幼稚別扭的,但從中或許可以看出當時當地文藝青年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的文風語匯,放到今天,便可作為一種‘骨董’來看看了,當然是不值幾文的‘骨董’。至于文中的議論,當然也是膚淺的,不值方家一笑。不過年青人那種想說便說的天真,也使今日之我羨慕不已。其中有些看法,至今也並無改變,所以也不去修改了。”如果每位作者時隔多年都有機會重新審視數十年前的己作,又會作何感想呢?一個多甲子過去,人事代謝,往來古今,琴苑一角的剪影定格在這本小冊子里,留待後輩,次第登臨。
辛卯冬至前三日凌晨于滬上建德路口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