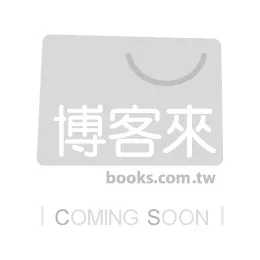本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原題《敘述「文革」》,出版社改題為《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據說當時叢書學術委員會主任季羨林教授聽到此書是重新解讀「文革」便有些質疑,后來經過其他編委解釋才知並非(至少不會全是)「新左派」重新評論「文革」。在這本書里,我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嘗試借用一種現代文學理論(普洛普的結構主義方法)來解讀具體復雜的中國文學及文化現象;二是嘗試從文學角度討論「文化大革命」如何成為一種被閱讀乃至再讀的「文本」。拙作出版后有不少批評,缺陷疏漏當然不少。本想借這次出版《講稿》的機會,將研究范圍擴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說」(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為生病,這個重寫計划也暫時沒有完成。期待日后還有再版續寫的機會。
但這一卷《重讀「文革」》,還是對《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訂增刪。一方面是文字修訂,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內容……
最近十年常越界電視,有網友觀眾批評我常常在討論現實問題時提到「文革」,「為什麼老是念念不忘呢?」這是他們的疑問。說實話,也是我自己的疑問。我想,於私,是個人記憶。至今仍會在夢中見到父親在電子管收音機前聽九評、北京女紅衛兵抄家時親切的目光:「別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街上群眾歡呼剪人褲腿、下鄉火車啟動時的哭聲混合東方紅樂曲聲、下放干部告訴驚訝的村民「尼克松要來了,毛主席決定,這一次不殺他」 ……
怎麼辦呢?生死在這個時代,偏偏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羨慕那些腦子也能和軀體及生活方式一起與時俱進的人們,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進維也納一個城堡,做夢卻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機,山崖旁路很窄……
-

文學批評的應許與期許
$465 -

宋代文學論考
$45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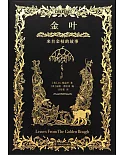
金葉:來自金枝的故事
$355 -

元好問與中國詩歌傳統研究
$417 -

剪刀與女房東
$251 -

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
$3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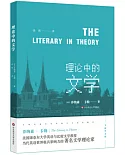
理論中的文學
$25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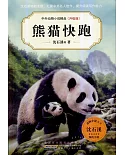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熊貓快跑
$115 -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
$171 -

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論叢(第一輯)
$355 -

文學思想研究與文學語言觀透視
$29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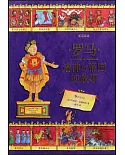
圖話經典:羅馬諸神與帝國的故事
$3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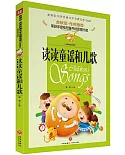
讀讀童謠和兒歌
$8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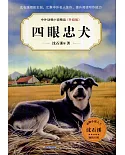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四眼忠犬
$1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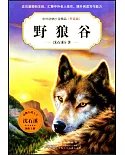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野狼谷
$115 -

詩的時光書.2:月亮以上的愛情(插圖珍藏本)
$251 -

朗誦中國
$396 -

小說的方法
$180 -

中國文學史(圖文版)
$208 -

中國文學史概要(圖文版)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