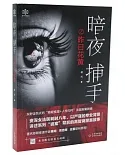★先鋒已死 青年當立 不懂文學的人嚴禁翻閱
繼馬原、余華、格非、孫甘露之後,扛起先鋒文學大旗
曹文軒北大中文系教授作序推薦
這個青年很有點想法,很有點肆意,很有點理想,又有點“目中無人”。
本書是80後一代在這個浮躁的社會背景下對青春的自我審視,其打破時間、空間或邏輯關系制約的敘事方法,表現出這一代人內心世界的焦慮。社會與他們之間有著巨大的價值觀差異,父母與他們有著時代的鴻溝,甚至生活在在同齡人中,也很難找到存在感!
這是一部時下罕見的報有純粹文學理想的試驗型先鋒小說,它有異于常規小說按時間順序依次直線前進的敘事方法,而是隨著人的意識活動,通過自由聯想來營造出一個奇幻迷離的世界。
同時這也是在文學稀缺時代令人產生敬意的寫作,繼馬原、余華、格非、孫甘露等人的先鋒寫作之後,新生代以勇氣和闖勁重拾了這一傳統。
王銳愚,1988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士。自幼早慧,嗜好讀書。少年時開始批判各種偽“經典”、“名著”,不拘文法。現為穿梭于現實與虛幻中的先鋒作家。
序
前不久剛接觸到一部成長小說研究的論著,現在又為一部成長小說寫序。似乎大家都覺得我很適台寫“成長”。許是我同孩子們接觸更多些,也有不少八零後的青年朋友,我看著他們成長,也感受著他們成長。殊不知,一代與另一代的成長,最難書寫。
我筆下的孩子們在成長中更多的是歡樂,而王銳愚寫下的成長里,卻用到了非常多的疼痛。也許他正在成長,正在同青春的痕跡掙扎。也許對成長,他有比我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在他看來,成長,必然是個疼痛的詞。
寫了這部作品的作者,是一個執著而有教養的男孩——也許,他更願意我稱他為青年。這個青年,對人生有著超出他同代人的見解,他對文學的體悟更是遙遙領先的,這也許是因為天資,也許是因為勤奮,也許是因為家教。這個青年很有點想法,很有點肆意,很有點理想,又有點“目中無人”。在作品里——如果這部作品與他有關的話,他、他們擺著自己滿意的表情,听著喧囂的歌,穿過心底的長街短巷,在路過的拐角,三三兩兩哼唱著(我們的小世界)。
他也營造了一個小世界,讓我,或是我們這些忙于生計的大人們都有些困惑的小世界。他在這個世界中,並沒有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美滿地生活,而是罩上堅硬的外殼,倔強地四處撞壁。當然,他們會果斷地認為我們這些大人太過于世故、陳舊,早已沒了夢想。他們才是見過夢想被現實壓碎了翅膀的人。他在文字里秉著一口傲氣,跌跌撞撞尋找出口的樣子,讓我不禁想到一個特別有姿態的詞拗。
拗,是創作的拗。不走常規的敘述模式,非耍拗起來走。拗可是一門學問。要抬著下巴別著臉頰走得漂亮了,得選對方式。尋常道場里這麼走著,肯定要被行注目禮的。但若是跳著街舞,就算走上一路,非但沒有非議,還會連獲贊嘆。因為街舞的拗,是有含義的拗,不是平白無故為了扭曲而來的扭曲。舞者知道為什麼這時候要折起關節,音樂起了哪個鼓點時要倒地旋轉,這是設計好的,也是流露出的。愛跳街舞的人不少,跳得精巧,不讓人覺得只是玩花樣的卻不多。這和拗著寫作的原理一樣,拗著,得拗得有道理,有感情。銳愚的文字里有執念,固執地要將世界分為兩半的執念。固執地要從青春的爪牙中掙脫的執念。固執地要在自己的世界中格斗的執念。閉著眼(目青),拒絕與迎台相互糾纏。這種執念,不但樸拙地生長在他的身上,也蔓延在這個陽光與浮躁同在的年紀里。這是年輕人的樸拙,我們年輕時也曾有過,似乎一屏氣凝神,一種奔騰就能沖滿血管。時光過得久了,這種激情也淡去了。銳愚的這份拗,雖然粗糙、樸拙了些,倒也是年輕的拗,充滿男性熱血的拗。
寫小說的人的世界,可以很大,浩瀚到千百年間,宇宙萬物。卻也很微小,微小得只能放進自己,甚至只能容下一雙看世界的眼(目青)。作者的小世界里,那雙眼(目青)透過懵懂的認知模糊地看著虛偽的世界,憤怒地認為,“踐踏即擁有,丑惡即正義,庸俗即存在。”堅硬的想象,扭轉的目光,是銳愚透過筆下的男男女女們呈現出的文字的拗,精神的拗,青春的拗。
拗著來來去去,好像是他們特有的習性。寫作的時候拗,生活的時候也拗,以嬉笑怒罵的姿態生活,內里都藏著一個戰斗者。這個戰斗者可以扭轉瞳孔,看見隱藏的秘密,執拗地斜著下巴,手里藏著無可探知的力量,面對自己鋪設的荊棘,沖撞著前行。
我們那代人,成長的日子時常磕磕絆絆,卻也歡騰。磕絆的多是物質,歡騰的都是精神。而如今的孩子們,不太有物質的苦惱,更多的卻是精神的疼痛。我記得我們年輕的時候,穿件藍背心就覺得自己特別有朝氣。那種朝氣是帶著些傻愣愣的笑,是一揮手便呼朋喚友、成群結隊的熱鬧,是群文學青年擁擠在走廊燈下、教室後排,埋首讀書,書寫理想的真摯。而當我們為孩子們創造了不再磕絆的生活時,他們卻被困在家里、困在學校、困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越來越快的節奏,讓他們沒有機會慢慢地成長、慢慢地感受時光的流逝、慢慢想像文字里的風景。現代化的時代,也是想象被簡化了的時代。孩子們在越來越薄弱的想象里,夢想不再純粹,精神漸漸孤獨。他們不在文字里言說孤獨,而文字中的倔強與堅硬卻都是孤獨。那份孤獨,是這一代的孤獨。他們靠著那股拗,自己消化,自己解脫。寫作是紀念成長的好辦法。她以明亮或惆悵的模樣,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們,在我們的青春里,也在他們的青春里。
不過,寫小說,並非一蹴而就的事。什麼是小說,怎樣寫才能稱為創作,這確實是個言難盡的問題。並不是碼出幾十萬字來便可以昂首踱步地炫耀自己的小說才能。小說需要技巧,需要質地。小說,是個玄奇的作為,卻又是個實在的作為。這個年紀的孩子,更喜歡將它變得玄奇,似乎越玄奇越好。比起實在,玄奇更難以把握,一不留神,變成徒有其表的艱澀就難以言說了。我這樣表述,並非強調文學的專業性。銳愚那種無心炫技的表述,也許更有原始的生命力。文章的質地,是無法隨意拈來的。只有謙遜的閱讀與鑒賞、仔細的思考與咀嚼,才會在積澱中構建出優雅的厚重的質地。銳愚的文章,情感是有了,功夫也下了(要知道,碼上幾十萬的字也是個體力活),想必他對自己也有著獨特的認識,而文學的質地,還需要再潛心琢磨。內外兼修下的作品,才能有成為經典的可能。
這份琢磨,是平和的、深邃的,也是漫長的。不管寫作什麼樣的作品,不管計算著怎樣表達,關鍵是作者必須有顆沉澱的心。文字可以激情豪邁,斑斕瑰麗,但飛揚的眉眼背後,是生活的磨練。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張揚個性也非巧做心思迎合市場,而是騰出一片心底,沉靜地真實地去感受、洗滌、思考,然後才是目光成熟的書寫。銳愚是懂這個道理的人。這樣的人,在年輕寫作者中也許並不多。
從叫板生活到回味苦難,銳愚和他們這代青年的成長還有漫長的時光要度過。要耐得住寂寞,享受得了寂寞,才可以繼續言說人生。不僅是銳愚,這是每一個作者都該銘記的道理。
在文學的路上,但願我們總能看到銳愚的身影。
曹文軒 2011年5月7日
我筆下的孩子們在成長中更多的是歡樂,而王銳愚寫下的成長里,卻用到了非常多的疼痛。也許他正在成長,正在同青春的痕跡掙扎。也許對成長,他有比我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在他看來,成長,必然是個疼痛的詞。
寫了這部作品的作者,是一個執著而有教養的男孩——也許,他更願意我稱他為青年。這個青年,對人生有著超出他同代人的見解,他對文學的體悟更是遙遙領先的,這也許是因為天資,也許是因為勤奮,也許是因為家教。這個青年很有點想法,很有點肆意,很有點理想,又有點“目中無人”。在作品里——如果這部作品與他有關的話,他、他們擺著自己滿意的表情,听著喧囂的歌,穿過心底的長街短巷,在路過的拐角,三三兩兩哼唱著(我們的小世界)。
他也營造了一個小世界,讓我,或是我們這些忙于生計的大人們都有些困惑的小世界。他在這個世界中,並沒有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美滿地生活,而是罩上堅硬的外殼,倔強地四處撞壁。當然,他們會果斷地認為我們這些大人太過于世故、陳舊,早已沒了夢想。他們才是見過夢想被現實壓碎了翅膀的人。他在文字里秉著一口傲氣,跌跌撞撞尋找出口的樣子,讓我不禁想到一個特別有姿態的詞拗。
拗,是創作的拗。不走常規的敘述模式,非耍拗起來走。拗可是一門學問。要抬著下巴別著臉頰走得漂亮了,得選對方式。尋常道場里這麼走著,肯定要被行注目禮的。但若是跳著街舞,就算走上一路,非但沒有非議,還會連獲贊嘆。因為街舞的拗,是有含義的拗,不是平白無故為了扭曲而來的扭曲。舞者知道為什麼這時候要折起關節,音樂起了哪個鼓點時要倒地旋轉,這是設計好的,也是流露出的。愛跳街舞的人不少,跳得精巧,不讓人覺得只是玩花樣的卻不多。這和拗著寫作的原理一樣,拗著,得拗得有道理,有感情。銳愚的文字里有執念,固執地要將世界分為兩半的執念。固執地要從青春的爪牙中掙脫的執念。固執地要在自己的世界中格斗的執念。閉著眼(目青),拒絕與迎台相互糾纏。這種執念,不但樸拙地生長在他的身上,也蔓延在這個陽光與浮躁同在的年紀里。這是年輕人的樸拙,我們年輕時也曾有過,似乎一屏氣凝神,一種奔騰就能沖滿血管。時光過得久了,這種激情也淡去了。銳愚的這份拗,雖然粗糙、樸拙了些,倒也是年輕的拗,充滿男性熱血的拗。
寫小說的人的世界,可以很大,浩瀚到千百年間,宇宙萬物。卻也很微小,微小得只能放進自己,甚至只能容下一雙看世界的眼(目青)。作者的小世界里,那雙眼(目青)透過懵懂的認知模糊地看著虛偽的世界,憤怒地認為,“踐踏即擁有,丑惡即正義,庸俗即存在。”堅硬的想象,扭轉的目光,是銳愚透過筆下的男男女女們呈現出的文字的拗,精神的拗,青春的拗。
拗著來來去去,好像是他們特有的習性。寫作的時候拗,生活的時候也拗,以嬉笑怒罵的姿態生活,內里都藏著一個戰斗者。這個戰斗者可以扭轉瞳孔,看見隱藏的秘密,執拗地斜著下巴,手里藏著無可探知的力量,面對自己鋪設的荊棘,沖撞著前行。
我們那代人,成長的日子時常磕磕絆絆,卻也歡騰。磕絆的多是物質,歡騰的都是精神。而如今的孩子們,不太有物質的苦惱,更多的卻是精神的疼痛。我記得我們年輕的時候,穿件藍背心就覺得自己特別有朝氣。那種朝氣是帶著些傻愣愣的笑,是一揮手便呼朋喚友、成群結隊的熱鬧,是群文學青年擁擠在走廊燈下、教室後排,埋首讀書,書寫理想的真摯。而當我們為孩子們創造了不再磕絆的生活時,他們卻被困在家里、困在學校、困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越來越快的節奏,讓他們沒有機會慢慢地成長、慢慢地感受時光的流逝、慢慢想像文字里的風景。現代化的時代,也是想象被簡化了的時代。孩子們在越來越薄弱的想象里,夢想不再純粹,精神漸漸孤獨。他們不在文字里言說孤獨,而文字中的倔強與堅硬卻都是孤獨。那份孤獨,是這一代的孤獨。他們靠著那股拗,自己消化,自己解脫。寫作是紀念成長的好辦法。她以明亮或惆悵的模樣,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們,在我們的青春里,也在他們的青春里。
不過,寫小說,並非一蹴而就的事。什麼是小說,怎樣寫才能稱為創作,這確實是個言難盡的問題。並不是碼出幾十萬字來便可以昂首踱步地炫耀自己的小說才能。小說需要技巧,需要質地。小說,是個玄奇的作為,卻又是個實在的作為。這個年紀的孩子,更喜歡將它變得玄奇,似乎越玄奇越好。比起實在,玄奇更難以把握,一不留神,變成徒有其表的艱澀就難以言說了。我這樣表述,並非強調文學的專業性。銳愚那種無心炫技的表述,也許更有原始的生命力。文章的質地,是無法隨意拈來的。只有謙遜的閱讀與鑒賞、仔細的思考與咀嚼,才會在積澱中構建出優雅的厚重的質地。銳愚的文章,情感是有了,功夫也下了(要知道,碼上幾十萬的字也是個體力活),想必他對自己也有著獨特的認識,而文學的質地,還需要再潛心琢磨。內外兼修下的作品,才能有成為經典的可能。
這份琢磨,是平和的、深邃的,也是漫長的。不管寫作什麼樣的作品,不管計算著怎樣表達,關鍵是作者必須有顆沉澱的心。文字可以激情豪邁,斑斕瑰麗,但飛揚的眉眼背後,是生活的磨練。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張揚個性也非巧做心思迎合市場,而是騰出一片心底,沉靜地真實地去感受、洗滌、思考,然後才是目光成熟的書寫。銳愚是懂這個道理的人。這樣的人,在年輕寫作者中也許並不多。
從叫板生活到回味苦難,銳愚和他們這代青年的成長還有漫長的時光要度過。要耐得住寂寞,享受得了寂寞,才可以繼續言說人生。不僅是銳愚,這是每一個作者都該銘記的道理。
在文學的路上,但願我們總能看到銳愚的身影。
曹文軒 2011年5月7日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