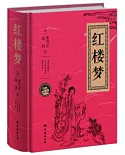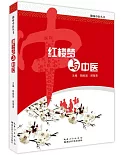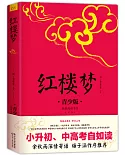一部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除第一、二卷為詩歌、散文的創作和第七、八、九卷的書信、日記外,其余五卷的研究著作中關于紅樓夢的就佔了三卷,可見分量之重。本文選編了作者從1921—1981年間,幾乎貫穿于他學術活動全過程的一小部分著作。對紅學的回眸和重新起航提供借鑒。
當我們的腳步跨進新世紀門檻的時候,作者相信每個人都會情不自禁也對于親歷的二十世紀作一番回顧,不管是就個人的經歷、學術的歷程甚或社會的歷史,無不如此。就中,單從紅學來講,在這過去不久的一百年間,不但歷久不衰,且早已成了國際性的顯學,這真是一個“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學術領域。也就因此,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回眸,即使是短短瞬間的回眸。
在這一百年間,紅學研究的文章和專著,其數量之多,用“汗牛充棟”來形容,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過分的。其間,具有真知卓識而足以超越前賢、啟迪後學的著述也不勝枚舉,所以,要對上個世紀的紅學作全面回眸,對于腹笥貧乏的作者輩來講,那真的只能是望洋興嘆了。這雖然不能看作“挾太山以超北海”,卻也絕對不是“為長者折枝”。怎麼辦?那就只能就個人感知所及,拉雜寫點感想,自然屬于回眸範圍的感想。
二十世紀的紅學大體經歷了三個明顯的發展階段。起初,是以蔡元培、王際真等為代表的索隱階段。他們出于民族革命的要求,以索隱為手段,顯幽鉤微出排滿反清的民族大義,此即所謂“舊紅學”。洋博士的胡適,在白話文學的熱潮中,卻以固有的考證方法去追尋《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並進而提出了創作緣起的自傳說,于是便有了新紅學的興起。與此同時,王國維以西方的悲劇理論來衡論《紅樓夢》的思想文學意義,這實在開了紅學理論評論的先河;俞平伯則以其深厚的文學涵養,著重從鑒賞的角度對《紅樓夢》的文本進行了細致人微的賞析,從而完成了紅學鑒賞的開山之作。在此之後,就是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了,雖然經歷了一九五四年的紅學論爭和“文化大革命”的短暫平靜,但卻遮擋不住諸家蜂起、群雋爭秀的繁榮局面,因而形成了一個名家輩出、新說並起的時代。正是這個時代,有點讓人邁上了紅學的山陰古道,確實令人目不暇接,不要說細致回眸,早已經目迷五色了。
反思二十世紀的紅學史,有許多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現象。索隱派的蔡元培既已被胡適譏為猜笨謎,以確鑿的史料證明索隱派的荒謬,索隱派似乎應該壽終正寢了,但是不,在以後的相當時期里,乃至今天,索隱卻時隱時現,有時甚至相當活躍,索皇族內爭、索顯宦穢事、索曹家家史,簡直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首創文學評論的王國維,大概由于他的過早離世,後人來不及進行駁難,且由他開啟的這一學術道路,繼起者大加發揚,新觀點、新方法的不斷引入,從而對《紅樓夢》做出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評價。而對胡適,則由于其政治態度的向背,在奠定了新紅學的基石之後,則經受了嚴厲的批判,可是一旦時過境遷,特別是近年以來,胡適的考證紅學重又獲得了推崇,即使早已同他劃清了學術界線的學界精英,也一往情深地續接了學術前緣,而不少紅學新進,更將考證方法運用到文本的勾索,所得成果真是淋灕盡致。俞平伯偏于鑒賞的紅學研究,雖曾一度受到指責,卻也並未改變他對《紅樓夢》繼續作出獨出心裁的鑒賞評析。回顧這一段紅學史,總會令人想到︰學術發展的歷程大概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不會是直線式的,它也總是曲折前進的,不管是層層疊升式還是迂回曲折式,或者竟是新陳代謝式,不斷催生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術,但它總是不斷發展前進的,而且新舊之間也並不就是截然不同、涇渭分明的。對此,人們可以比作後人踏著前人的肩膀前進,也可以說成是否定之否定,都離不開繼承與創新這一總題目的。
如今,不但王國維早已沉人了寧靜的昆明湖,胡適也猝然倒在了他為之馳騁一生的學術講壇之上,連俞平伯也于十六年前的一九九○年安然長眠了。現在所留給我們的只是他們在孜孜(石乞)(石乞)中所取得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既是供我們作學術回眸的景點,更足以開拓我們的學術視野,並進而由此孕育新的學術新見,將其視作良好的學術種子和豐腴土壤是毫無疑義的。而這就有必要選印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了。
俞平伯曾自言,在《紅樓夢研究》印行的二十七年之前,他有過一本《紅樓夢辨》,由于新材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他有一些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才有《紅樓夢研究》的誕生,這自然可以看作後者是對前者的修訂版,不過,這已經是一九五○年的事了。到俞平伯去世的一九九○年,時間又過去了四十個年頭,其間他又有大量《紅樓夢》研究著作問世,其中自然也發生過不少見解的變化,這是可以意料並值得人們注意和研究的。所以,在選印他的代表作《紅樓夢研究》的時候,我們不應忽視其在此之後特別是晚年的著作。
“文革”結束後,俞平伯已經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雖然幾經滄桑,但對他所摯愛的紅學卻仍不能忘情,仍然關注著、思考著紅學動態和研究狀況,情不自禁地發而為文,這就是《樂知兒語說(紅樓)》、《舊時月色》和《索隱與自傳說閑評》等篇什的出現。只不過,他的年事畢竟已高,似乎已經力不從心,因而從他的這些文章中,我們雖然依舊能夠感受到他思維的細密和見解的卓絕,學術的智慧之光不時地閃耀,但這些卻只蘊含在他那一則則、一段段的文學隨筆之中了,再想閱讀他早年那些分析周全、論述完整的洋洋大文已經不可能了。
俞平伯晚年的幾篇文章,產生于思想復蘇、學術復蘇的大時代,同時也是他個人紅學研究復蘇的新時期,其中有些是對舊時觀點的重述,有些是對新見解的表露,這都可看作他紅學研究的最後訂定。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有︰他以為續書有不少地方脫離了曹雪芹的構想原意,黛、釵的悲劇命運應該是黛先死、釵後嫁,他還以為索隱和自傳說有殊途同歸的趨勢等等,所有這些都能給予我們不少新的啟迪。
一部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除第一、二卷的詩歌、散文創作和第七、八、九卷的書信、日記外,其余五卷的研究著作中關于《紅樓夢》的就佔了三卷,可見分量之重,而且從時間段上看,始于一九二一年、止于一九八一年,幾乎貫穿于他學術活動的全過程。而這里所能印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願這一小部分著作能夠給予人們在紅學同眸和重新起航方面稍有貢獻。
目錄
前言/魏同賢
自序
論續書底不可能
辨後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
高鶚續書底依據
後四十回底批評
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
作者底態度
紅樓夢底風格
紅樓夢地點問題底商討
八十回後的紅樓夢
論秦可卿之死
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
前八十回紅樓夢原稿殘缺的情形
後三十回的紅樓夢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
紅樓夢正名
紅樓夢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
附錄
自序
論續書底不可能
辨後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
高鶚續書底依據
後四十回底批評
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
作者底態度
紅樓夢底風格
紅樓夢地點問題底商討
八十回後的紅樓夢
論秦可卿之死
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
前八十回紅樓夢原稿殘缺的情形
後三十回的紅樓夢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
紅樓夢正名
紅樓夢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
附錄
序
一九二一年四月到七月之間,我和顧頡剛先生通信討論《紅樓夢》,興致很好。得到頡剛底鼓勵,于次年二月至七月間陸續把這些材料整理寫了出來,共三卷七卜篇,名日《紅樓夢辨》,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經過了二十七個年頭,這書並未再版,現在有些人偶爾要找這書,很不容易,連我自己也只剩得一本了。
這樣說起來,這書底運道似乎很壞,卻也不必盡然。它底絕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著呢,因出版不久,我就發覺了若干的錯誤,假如讓它再版三版下去,豈非謬種流傳,如何是好。所以在《修正紅樓夢的一個楔子》一文末尾說,(見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雜拌》一一一頁)“破笤帚可以擲在壁角落里完事。文字流布人間的,其擲卻不如此的易易,奈何。”
讀者當然要問,錯誤在什麼地方?話說來很長,大約可分兩部分,(一)本來的錯誤;(二)因發見新材料而證明出來的錯誤。各舉一事為例。第一個例︰如中卷第八篇《紅樓夢年表》曹雪芹底生卒年月必須改正不成問題,但原來的編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底生平跟書中賈家的事情攪在一起,未免體例太差。《紅樓夢》至多,足自傳性質的小說,不能把它徑作為作者的傳記行狀看啊。第二個例︰我在有正戚本評注中發見有所謂“後三十回的紅樓夢”,卻想不到這就是散佚的原稿,誤認為較早的續書。那時候材料實在不夠,我的看法或者可以原諒的,不過無論如何後來發見兩個脂硯齋評本,已把我的錯誤給證明了。
錯誤當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談何容易。我抱這個心願已二十多年了。最簡單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邊,而且所謂脂硯齋評本也還沒有經過整理,至于《紅樓夢》本身底疑問,使我每每發生誤解的,更無從說起。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胡涂。別的小說底研究,不發生什麼學,而談《紅樓夢》的便有個諢名叫“紅學”。雖文人游戲之談卻也非全出偶然,這兒自然不暇細談,姑舉最習見的一條以明其余。
《紅樓夢》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麼一回事?依脂硯齋甲戌本之文,書名五個︰《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人名也是五個︰空空道人改名為情僧,(道士忽變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吳玉峰,曹雪芹,脂硯齋。(脂硯齋評書者,非作者,不過上邊那些名字,書上本不說他們是作者。)一部書為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嗎?還確實有其人?就算我們假定,甚至于我們證明都是曹雪芹底筆名,他又為什麼要頑這“一氣化三清”底把戲呢?我們當然可以說他文人狡獪,但這解釋,您能覺得圓滿而愜意嗎?從這一點看,可知《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凡夫,望洋興嘆,從何處去下筆呢!下筆之後假如還要修正,那就將不勝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為佳。
最後,我也沒機會去修改這《紅樓夢辨》,因它始終沒得到再版底機會哩。
現在好了,光景變得很樂觀。我得到友人文懷沙先生熱情的鼓勵。近來又借得脂硯齋庚辰評本石頭記。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這書修正後重新付刊。除根本的難題懸著,由于我底力薄,暫不能解決外,在我真可謂因緣具足非常僥幸了。我就把舊書三卷,有的全刪,有的略改,並為上中兩卷。其下卷有一篇是一九四八發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後三十回的紅樓夢》篇名雖同舊書,卻完全改寫過,所以也算他新篇。共得三卷十六篇。原名《紅樓夢辨》,辨者辨偽之意,現改名《紅樓夢研究》,取其較通行,非敢輒當研究之名,我底《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
一九五○年十二月,俞平伯序于北京。
這樣說起來,這書底運道似乎很壞,卻也不必盡然。它底絕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著呢,因出版不久,我就發覺了若干的錯誤,假如讓它再版三版下去,豈非謬種流傳,如何是好。所以在《修正紅樓夢的一個楔子》一文末尾說,(見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雜拌》一一一頁)“破笤帚可以擲在壁角落里完事。文字流布人間的,其擲卻不如此的易易,奈何。”
讀者當然要問,錯誤在什麼地方?話說來很長,大約可分兩部分,(一)本來的錯誤;(二)因發見新材料而證明出來的錯誤。各舉一事為例。第一個例︰如中卷第八篇《紅樓夢年表》曹雪芹底生卒年月必須改正不成問題,但原來的編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底生平跟書中賈家的事情攪在一起,未免體例太差。《紅樓夢》至多,足自傳性質的小說,不能把它徑作為作者的傳記行狀看啊。第二個例︰我在有正戚本評注中發見有所謂“後三十回的紅樓夢”,卻想不到這就是散佚的原稿,誤認為較早的續書。那時候材料實在不夠,我的看法或者可以原諒的,不過無論如何後來發見兩個脂硯齋評本,已把我的錯誤給證明了。
錯誤當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談何容易。我抱這個心願已二十多年了。最簡單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邊,而且所謂脂硯齋評本也還沒有經過整理,至于《紅樓夢》本身底疑問,使我每每發生誤解的,更無從說起。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胡涂。別的小說底研究,不發生什麼學,而談《紅樓夢》的便有個諢名叫“紅學”。雖文人游戲之談卻也非全出偶然,這兒自然不暇細談,姑舉最習見的一條以明其余。
《紅樓夢》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麼一回事?依脂硯齋甲戌本之文,書名五個︰《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人名也是五個︰空空道人改名為情僧,(道士忽變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吳玉峰,曹雪芹,脂硯齋。(脂硯齋評書者,非作者,不過上邊那些名字,書上本不說他們是作者。)一部書為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嗎?還確實有其人?就算我們假定,甚至于我們證明都是曹雪芹底筆名,他又為什麼要頑這“一氣化三清”底把戲呢?我們當然可以說他文人狡獪,但這解釋,您能覺得圓滿而愜意嗎?從這一點看,可知《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凡夫,望洋興嘆,從何處去下筆呢!下筆之後假如還要修正,那就將不勝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為佳。
最後,我也沒機會去修改這《紅樓夢辨》,因它始終沒得到再版底機會哩。
現在好了,光景變得很樂觀。我得到友人文懷沙先生熱情的鼓勵。近來又借得脂硯齋庚辰評本石頭記。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這書修正後重新付刊。除根本的難題懸著,由于我底力薄,暫不能解決外,在我真可謂因緣具足非常僥幸了。我就把舊書三卷,有的全刪,有的略改,並為上中兩卷。其下卷有一篇是一九四八發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後三十回的紅樓夢》篇名雖同舊書,卻完全改寫過,所以也算他新篇。共得三卷十六篇。原名《紅樓夢辨》,辨者辨偽之意,現改名《紅樓夢研究》,取其較通行,非敢輒當研究之名,我底《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
一九五○年十二月,俞平伯序于北京。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