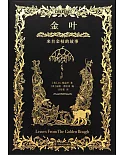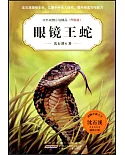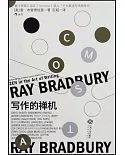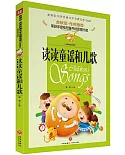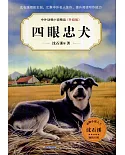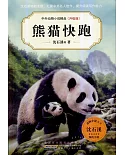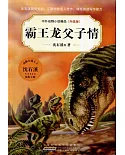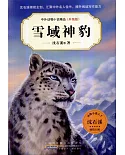本書選錄了作者陳思和教授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領域,圍繞「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而展開的代表性論述。作者在世界文學視野下,多層面地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的演變及其創造性成就,提出了包括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中國文學中的懺悔意識、現實戰斗精神、現代戰斗意識、現代生存意識、先鋒與常態、惡魔性因素等命題,在價值論與方法論兩個層面為中國比較文學和國別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啟示。
陳思和,1954年生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獲得者,兼任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學會、中國當代文學學會、中國文藝學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特聘「紫江學者」等。主要著作有:《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及編年體文集《筆走龍蛇》、《雞鳴風雨》、《犬耕集》等近20種。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獲全國普通高等教材一等獎;《巴金圖傳》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先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首爾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香港嶺南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和波恩大學任訪問研究員或客座教授。
目錄
序:作為文學關系研究范疇的「世界性因素」
上編: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整體觀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整體觀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代主義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
下編: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
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集》
《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的惡魔性因素
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
從巴赫金的民間理論看《兄弟》的民間敘事
自然主義與生存意識——試論新寫實小說的創作特點
附錄一:對中西文學關系的思考
附錄二:比較文學與精英化教育
上編: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整體觀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整體觀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代主義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
下編: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
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集》
《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的惡魔性因素
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
從巴赫金的民間理論看《兄弟》的民間敘事
自然主義與生存意識——試論新寫實小說的創作特點
附錄一:對中西文學關系的思考
附錄二:比較文學與精英化教育
序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陳思和先生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領域提出的一個最有影響力的「關鍵詞」,大約就是「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了。這個核心概念在他30多年的學術生涯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實踐中,經作家個案研究、文學思潮研究和文學史敘述等多個層面的同時展開和不斷推進,在思和先生的個人學術話語中可能已經成為最具范式意義的慨念。它在體現思和先生的個人學術創構及其特點的同時,對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的啟示意義也日漸顯露。這日漸顯露的過程,伴隨了30年來罔際文化格局和中罔文學學術語境的變遷,更是他在學術實踐中持續思考與探索的收獲。在我看來,這個過程幾乎貫穿了他至今全部學術歷程。
作為「文革」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人文學者,思和先生的學術生涯,起步於中困新文學研究剛剛開始擺脫僵化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而走向學科獨立的時期,也是比較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被再次引進,並逐步建立學科體系的時候。雖然一開始是以20世紀中國文學和當代文學批評為自己的志業,但比較文學的學術方法和視野,無疑對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有着重要的啟發意義,而他的文學學術工作,從一開始就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和現當代作家個案研究兩個方向同時展開。前者是與賈植芳先生一起,承擔「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田現代文學的影響」課題研究,后者即是現代作家個案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對西方文藝思潮、作家作品和創作方法在20世紀中圍的譯介及其影響資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感受到中困現代文學復雜多元的外來文化和文學資源,從而使其對中國文學創作的闡釋,建立在開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之上。關於思和先生的當代文學批評,這里不做具體展開,但有一贏可以肯定,他在當代批評界持續發揮的影響,除30多年來所傾注的熱情與心血外,還取決於其批評視野的世界文學與中罔文學現代轉型的二維參照意識,而作為個案的巴金研究就是從整理作家的原始資料開始,其論述框架是從思想文化和文學表現手法兩個方面,清理作家創作和中外思潮,特別是西方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歐美恐怖主義和法國民主主義等西方文化思潮,以及法、俄等歐洲文學間的復雜關系,其中無政府主義、恐怖主義等被國內學界長期回避的話題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學術視野與格局,為巴金研究乃至整個現代文學學術帶來一股清新之氣。
在此基礎上,《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是思和先生在新的學術語境下對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反思。它立足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學思潮在中罔的命運,辨析中國作家如何基於本土立場,主動汲取外來文化養料,從民族文學傳統轉型的需要出發進行創造性轉化。這一研究角度,同然出於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變革的需要,但也是比較文學研究在中罔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具體實踐。它以「中國新文學中的XX」為論述框架,探討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學和文化思潮影響下,對西方近現代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文學和文化思潮所作出的回應、借鑒和創造性轉化,從而體現中國文學從近代向現代的轉變過程。本書「上編」所選錄的幾篇論文,最早就構思寫作於80年代初期,陸續發表后成書於1987年,即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牛犢叢書」之一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小32開本,不足13萬字篇幅,但此書不僅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內引起廣泛關注和肯定,還在1990年貴陽舉行的中國比較文學第三屆年會上獲比較文學優秀著作一等獎。我至今還記得當時追蹤閱讀這些論文時的興奮之情(當時我並不把它們當做比較文學研究看待),它們為我這個青年學子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豐富的資源背景,也呈現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國際文學交流圖景。現在回想起來,我最初關注比較文學,並把早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興趣逐漸擴大至比較文學領域,這些文章起r重要作用。但就在此書出版后不久,一天我去見思和先生,在談及這系列研究時,他的一句話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說我現在對這些文章有了新的不滿,中國文學中的什麼什麼,是否成一個套路了?當時我並未真正從學理上理解這種自我不滿的內在含義,只是隱約猜想,大約就在他酣暢淋漓地寫作這些文章,並在陸續發表后引來許多肯定和贊揚的同時,已經伴隨了對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立場與方法的進一步思考了。這種猜想在不久后他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得到了證實。
思和先生以「新文學整體觀」命名而出版的著作至今有五個版本。他對這個書名或者命題應該是有特別感情的。而他的許多學術工作,又都可以與這個命題形成不同層次的邏輯關聯。我想,它同然是直接針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提出,但鑒於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兼具了中罔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兩個學科的性質,思和先生圍繞這一命題所做的論述、修訂、調整和豐富等一系列工作,正體現了他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領域的持續思考。因此,結合他的相關論述來觀察這種調整與變化,不妨也可以作為理解其「世界性因素」研究范疇形成、展開及其內涵的一個途徑。
在1987年《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出版之后的20多年里,思和先生相繼又有台灣版、韓文版、上海修訂版和作為「20世紀文學史理論創新叢書」之一的「續編」版問世。每次新版,思和先生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訂補充。比較起來,后兩版調整更多一些。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修訂版增加了關於文化狀態、戰爭文化心理與民間文化形態等章節的內容,而「續編版」變化最大。與初版相比,《新文學整體觀續編》完全是一部新著了,不過最后仍以「新文學整體觀」來命名,說明其論述對象和核心命題仍是思和先生一以貫之的,若從與比較文學的關聯性來看,這里我最關注的變化是,他把自90年代初以來有關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一系列思考,終於正式納入「新文學整體觀」的命題構架之中了。
……
作為「文革」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人文學者,思和先生的學術生涯,起步於中困新文學研究剛剛開始擺脫僵化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而走向學科獨立的時期,也是比較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被再次引進,並逐步建立學科體系的時候。雖然一開始是以20世紀中國文學和當代文學批評為自己的志業,但比較文學的學術方法和視野,無疑對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有着重要的啟發意義,而他的文學學術工作,從一開始就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和現當代作家個案研究兩個方向同時展開。前者是與賈植芳先生一起,承擔「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田現代文學的影響」課題研究,后者即是現代作家個案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對西方文藝思潮、作家作品和創作方法在20世紀中圍的譯介及其影響資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感受到中困現代文學復雜多元的外來文化和文學資源,從而使其對中國文學創作的闡釋,建立在開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之上。關於思和先生的當代文學批評,這里不做具體展開,但有一贏可以肯定,他在當代批評界持續發揮的影響,除30多年來所傾注的熱情與心血外,還取決於其批評視野的世界文學與中罔文學現代轉型的二維參照意識,而作為個案的巴金研究就是從整理作家的原始資料開始,其論述框架是從思想文化和文學表現手法兩個方面,清理作家創作和中外思潮,特別是西方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歐美恐怖主義和法國民主主義等西方文化思潮,以及法、俄等歐洲文學間的復雜關系,其中無政府主義、恐怖主義等被國內學界長期回避的話題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學術視野與格局,為巴金研究乃至整個現代文學學術帶來一股清新之氣。
在此基礎上,《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是思和先生在新的學術語境下對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反思。它立足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學思潮在中罔的命運,辨析中國作家如何基於本土立場,主動汲取外來文化養料,從民族文學傳統轉型的需要出發進行創造性轉化。這一研究角度,同然出於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變革的需要,但也是比較文學研究在中罔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具體實踐。它以「中國新文學中的XX」為論述框架,探討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學和文化思潮影響下,對西方近現代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文學和文化思潮所作出的回應、借鑒和創造性轉化,從而體現中國文學從近代向現代的轉變過程。本書「上編」所選錄的幾篇論文,最早就構思寫作於80年代初期,陸續發表后成書於1987年,即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牛犢叢書」之一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小32開本,不足13萬字篇幅,但此書不僅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內引起廣泛關注和肯定,還在1990年貴陽舉行的中國比較文學第三屆年會上獲比較文學優秀著作一等獎。我至今還記得當時追蹤閱讀這些論文時的興奮之情(當時我並不把它們當做比較文學研究看待),它們為我這個青年學子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豐富的資源背景,也呈現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國際文學交流圖景。現在回想起來,我最初關注比較文學,並把早期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興趣逐漸擴大至比較文學領域,這些文章起r重要作用。但就在此書出版后不久,一天我去見思和先生,在談及這系列研究時,他的一句話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說我現在對這些文章有了新的不滿,中國文學中的什麼什麼,是否成一個套路了?當時我並未真正從學理上理解這種自我不滿的內在含義,只是隱約猜想,大約就在他酣暢淋漓地寫作這些文章,並在陸續發表后引來許多肯定和贊揚的同時,已經伴隨了對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立場與方法的進一步思考了。這種猜想在不久后他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得到了證實。
思和先生以「新文學整體觀」命名而出版的著作至今有五個版本。他對這個書名或者命題應該是有特別感情的。而他的許多學術工作,又都可以與這個命題形成不同層次的邏輯關聯。我想,它同然是直接針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提出,但鑒於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兼具了中罔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兩個學科的性質,思和先生圍繞這一命題所做的論述、修訂、調整和豐富等一系列工作,正體現了他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領域的持續思考。因此,結合他的相關論述來觀察這種調整與變化,不妨也可以作為理解其「世界性因素」研究范疇形成、展開及其內涵的一個途徑。
在1987年《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出版之后的20多年里,思和先生相繼又有台灣版、韓文版、上海修訂版和作為「20世紀文學史理論創新叢書」之一的「續編」版問世。每次新版,思和先生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訂補充。比較起來,后兩版調整更多一些。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修訂版增加了關於文化狀態、戰爭文化心理與民間文化形態等章節的內容,而「續編版」變化最大。與初版相比,《新文學整體觀續編》完全是一部新著了,不過最后仍以「新文學整體觀」來命名,說明其論述對象和核心命題仍是思和先生一以貫之的,若從與比較文學的關聯性來看,這里我最關注的變化是,他把自90年代初以來有關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一系列思考,終於正式納入「新文學整體觀」的命題構架之中了。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