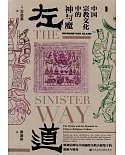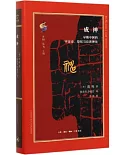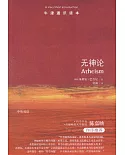本書主要關注的是:在當代中國鄉村的社會情境中,作為少數群體的基督徒,基督教信仰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何種意義,他們又是如何建構其宗教身份的。本研究希望透過基督徒身份建構的視角,通過對基督徒身份建構過程的不同側面的描述,探討基督徒身份建構的獨特模式。
身份認同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議題,第一章中首先梳理了有關身份認同的概念和社會認同理論;其次,對於基督徒宗教身份認同的研究已經受到學界的重視,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關於華人基督徒身份認同的歷史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文獻綜述。第二章介紹了Y縣的歷史文化與宗教概況、基督教的傳人與發展和基督教現狀,勾勒出基督教在Y縣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
第三章至第六章,通過對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實踐和日常生活不同側面的探究,討論基督徒身份建構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以及基督徒身份建構的模式特征。其中第三章主要討論基督徒的群體身份認同。基督徒皈信耶穌的路徑主要有家庭信仰傳統、疾病、遭遇生活困境和平安信主。基督教是制度型宗教,基督徒有明確的群體身份認同,表現在語言、思維方式、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受洗」是獲得基督徒身份的標志,「信與不信耶穌」是基督徒區分我群和他群的標准。在群際比較中,基督徒明顯地給予我群高評價,促進了基督徒的身份認同。
第四章中主要描述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團契活動,探究基督教的組織性對基督徒身份建構的作用。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包括禮拜聚會、團契活動和禱告,增強了基督徒的群體身份認同。宗教儀式是宗教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基督徒身份的一種標識和外在表現。基督徒通過這些宗教儀式和活動,加深了對基督教的理解,增強了對基督徒群體的歸屬感。
基督教的本土化過程,是基督教與地方傳統文化的互動過程。第五章和第六章通過對基督教改造地方傳統文化的活動和基督教葬禮的考察,分析基督教對社會生活參與的策略、影響的程度,基督教與地方傳統的沖突與融合,以及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參與對基督徒身份認同的影響。靈歌是基督徒的地方性信仰表達形式,采用當地流行的說唱藝術形式,配以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基督徒對包括春節風俗在內的地方性傳統文化的改造,使基督徒身份的表達具有地方性特征。祭祖問題是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一個沖突焦點,喪葬禮儀是祭祖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葬禮保留了傳統葬禮的基本框架,對其進行了基督教化的改造,顯示出其信仰模式由實踐正統轉向信仰正統。基督教葬禮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體系,但已經打出了基督教的名聲,成為基督教會進入社區公共生活的有效途徑,也為基督徒提供了彰顯其宗教身份的舞台。
在結論部分,討論了基督徒身份表達方式和身份建構模式等問題。基督徒的宗教身份是其多重身份的組成部分,基督徒身份是否居於核心位置,或因人而異,或視乎當時的情境而定。隨着當地基督教會的發展,基督徒的身份表達有從個體性、群體性到社會性表達的趨勢。基督徒的身份建構是一種群體化建構模式,基督教的有組織性是基督徒身份建構的重要影響因素。對於地方基督徒身份建構的研究,亦可透視出現代社會中,宗教如何「將不確定的復雜性轉化為確定的或可確定的復雜性」,從而為宗教信仰者提供生命的意義,並且通過個體信仰者的生活實踐進而影響社會。
目錄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雙重互動(序) 李向平
導論
第一章 身份認同與基督徒身份
第一節 身份認同相關理論綜述
第二節 基督徒身份研究綜述
第三節 有關身份概念的進一步討論
第二章 皇天后土——Y縣介紹
第一節 Y縣宗教、習俗概況
第二節 基督教的傳入與發展
第三節 基督教現狀
第三章 「我們是神的兒女」——基督徒的群體身份認同
第一節 為什麼信主——群體成員資格獲得的路徑
第二節 群體身份的辨識
第三節 基督徒的群體認同
第四章 「分別為聖」的宗教生活——基督徒身份的強化
第一節 主日崇拜與聖餐禮拜
第二節 團契活動
第三節 禱告:與上帝的交通
第五章 改造傳統:基督徒身份的地方性表達
第一節 靈歌:地方化的信仰形式
第二節 基督徒的春節
第三節 基督教與地方傳統文化
第六章 葬禮的選擇——新時代的「禮儀之爭」
第一節 「主內葬禮」與世俗葬禮
第二節 祭祖:禮儀還是偶然崇拜?
第三節 信仰正統VS實踐正統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基督徒身份:個人多重身份的組成部分
第二節 基督徒的身份表達:從個體性、群體性到社會性
第三節 基督徒的身份建構:群體化建構模式
第四節 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
參考文獻
附錄一 訪談記錄編碼表
附錄二 基督徒訪談提綱
后記
導論
第一章 身份認同與基督徒身份
第一節 身份認同相關理論綜述
第二節 基督徒身份研究綜述
第三節 有關身份概念的進一步討論
第二章 皇天后土——Y縣介紹
第一節 Y縣宗教、習俗概況
第二節 基督教的傳入與發展
第三節 基督教現狀
第三章 「我們是神的兒女」——基督徒的群體身份認同
第一節 為什麼信主——群體成員資格獲得的路徑
第二節 群體身份的辨識
第三節 基督徒的群體認同
第四章 「分別為聖」的宗教生活——基督徒身份的強化
第一節 主日崇拜與聖餐禮拜
第二節 團契活動
第三節 禱告:與上帝的交通
第五章 改造傳統:基督徒身份的地方性表達
第一節 靈歌:地方化的信仰形式
第二節 基督徒的春節
第三節 基督教與地方傳統文化
第六章 葬禮的選擇——新時代的「禮儀之爭」
第一節 「主內葬禮」與世俗葬禮
第二節 祭祖:禮儀還是偶然崇拜?
第三節 信仰正統VS實踐正統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基督徒身份:個人多重身份的組成部分
第二節 基督徒的身份表達:從個體性、群體性到社會性
第三節 基督徒的身份建構:群體化建構模式
第四節 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
參考文獻
附錄一 訪談記錄編碼表
附錄二 基督徒訪談提綱
后記
序
一千多年前,大秦景教初到中國,其后是元朝也里可溫教;至於三百多年前的利瑪竇,享有「西來孔子」之美稱,表明基督宗教與中國歷史、宗教文化之間一段深厚的交往。雖然其間有「禮儀之爭」,但其大有影響於西歐與中華世界。近代中國也多有教案,沖突紛紜,宗教信仰與政治軍事,各種因素層層疊疊。但它們均已說明,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歷史,斷斷續續卻也實在不短。
無論如何,基督宗教時至今日,它們在中國的歷史,斷斷續續,或深或淺,也可以說有千年之歷程了。然而,比較佛教之在中國,其歷史進程又大有不同。
倍受歷史青睞的佛教,從遙遠的印度、西域騎着白馬,來到中華,曾經也受到皇公貴族的疑惑與不同程度的抵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佛教信徒見了皇帝能否下跪磕頭。隋唐之前,佛門高僧為此與朝廷、官方學者沖突了很長時間,最后,佛教信徒終於能夠依照中國國情下跪磕頭了,把皇帝視為當今如來給予敬拜頂禮,佛教也就中國化了。
與此相反,基督宗教之在中國,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交上好運。
大秦景教之時,基督宗教依附於佛教,等到唐武宗滅佛,基督宗教也就隨着滅佛運動被運動去了;元朝有也里可溫發展模式,可惜好景不長。明代中葉之后,基督宗教再度人華,展開了中西文化初具規模的交流與互動。傳統中國信仰如佛教、儒教、道教,均與基督宗教的上帝信仰進行了真正的交往。然而,儒教及其中國人的「三聖信仰」聖人信仰、天命信仰、祖宗崇拜,與當時中國人理解的上帝(天主)信仰構成了沖突,及至「禮儀之爭」的爆發。到了近代,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近代基督宗教騎着炮彈再次進入中國,於是乎教案頻發,在一個充滿軍事、政治斗爭的環境之中,基督宗教始終難以獲得平實的理解。所以,如何理解、容納基督宗教,這一問題,毫無保留地留給了當代中國及其社會。
寓於古今中外之爭,佛教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構成,獲得了中國人的喜愛,往往喜歡稱之為佛教文化,而非佛教信仰;而基督宗教始終是被看作為外來的宗教,甚至沒有被視為基督宗教文化,僅僅是一種外來的宗教而已,沒有文化的象征與包裝。延至今日,全球化背景下諸多復雜因素,外來宗教又常常被看作是不穩定的異己,基督宗教難免首當其沖。
此類問題,如果置於宗教社會學的專業領域,實際上就是基督宗教及其信仰者在中國社會的被信仰現象、存在模式、宗教與文化融合以及身份建構等問題。基督宗教作為一種團體信仰模式,或者是一種共同體的信仰方式,它們與個人化的傳統中國人的信仰方式,不得不說是具有很大差異的。正是在此問題層面,梁漱溟才會說出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一是各信各的、各有各的利益而不求團體制約;一是信仰的共同體實踐要求,基於對一個神的信奉而構成普遍性的行為規范。其間差異大矣。
忽視這一差異,導致了迄今為止的信仰誤解;誇大這一差異.則會出現宗教信仰間的歧視,呈現唯我獨尊的民族信仰立場;利用這一差異,無疑是宗教信仰沖突的根源。
如今的問題是,基督宗教如何能夠成為中國宗教、中國信仰的有機構成部分,或者是當代中國人是否願意使基督宗教成為中國宗教、中國信仰的有機構成部分?
幾十年前,中國人就有「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說法;依據這一觀念,人們試圖以信仰划分國民。基督宗教如果是外來的宗教,那麼,信仰者就不是中國人,而基督宗教就不能成為中國宗教或中國的信仰。當然,隨着幾十年的社會進步與社會變遷,人們的觀念也在與時俱進,於是換了一種說法,這就是「多一個基督徒,多一個五好公民」。可是,問題依舊存在。使用一個五好公民的政治價值判斷,不一定就能夠消解多少年以來形成的宗教信仰偏見。一個中國人,如何能夠去信仰外來的神靈?她會保佑你嗎?上帝會成為中國人的神靈嗎?
這些問題,貌似老問題,實則也是改革開放的新問題。佛教的中國化問題早已解決,但基督宗教曾經也有過處境化、本地化等中國化的努力。時值改革開放今日,中國人只能信仰中國人自己的神靈、依據信仰來划分國民等觀念,也隨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在得以不斷強化。
在此過程之中,中國基督宗教界的努力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然而,中國社會為此本土化或處境化的構成,究竟提供了多大的空間,中國社會是否為基督宗教的中國化提供了相應的社會容納機制?這就是說,基督宗教在致力於適應中國社會,而中國社會在其結構與運作機制層面,是否真正具有了容納這樣一種信仰體系的空間。這些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好幾年前,基於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我就提出過「社會缺席,宗教何在」的問題。因為,一個健全的宗教信仰體系,唯有存在於—個現代社會的框架之中,它才會具有正常的社會整合功能與價值維系。除此之外。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往往會招致曲解或歧視。如果是一個一元化的權力萬能主義,如果是一個國家之下只有原子化國民的一元化社會結構,那麼,任何宗教信仰體系都會因此而被變型。只有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之中,各種宗教、各種信仰才會有機互動、積極對話,從對話的過程之中,轉換或消解那些有可能構成沖突的各種因素。化對抗為對話,轉對話為互動。這就是宗教社會學的「宗教社會化」命題及其意義的所在。
王瑩博士的《身份建構與文化融合——中原地區基督教會個案研究》,可以說就是致力予宗教社會化問題討論的一本專著。它基於王瑩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集中研究了地方鄉村社會中基督教的存在與信仰形式,及其與傳統信仰、民間習俗之間的互動關系,乃至基督教信仰與民間信仰習俗之間的相互吸納關系。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民間信俗得以復興的社會背景之下,基督教如何與之良性互動,如何在此過程中,設法把基督教及其信仰形式建構為中國人真正的信仰模式之一,甚至能夠像佛教那樣,使基督教成為中國宗教、中國文化、中國信仰習俗的有機構成部分,此乃為新時代框架中一種「新禮儀之爭」所應當具有的時代意義。雖然三百多年前,導致「禮儀之爭」的諸多因素依舊存在,祭天、祭聖人、祭祖等三聖信仰關系,依舊是中國信仰的諸類核心價值,但是社會的變遷以及社會容納空間的擴大,促使傳統的禮儀之爭,具有了新的社會學意義,此乃鄉村基督教及其「新禮儀之爭」給人的一個樂觀期待。這就構成了王瑩之鄉村基督教研究的學術價值。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民間基督教」(popular Christi-anity)這一概念,說明基督教在中國民間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問題,越來越受到相關學術界的關注。而王瑩的論著似乎也在討論這樣一些問題,比如基督教在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格局,基督教在中國的民間信仰形式,是否能夠構成與中國民間信仰有機互動的基督教信仰等等。我們期待着,民間基督教研究的繼續深入與王瑩博士的繼續努力。
拉拉雜雜,一些感想,權作為序。
李向平 2011年6月9日
無論如何,基督宗教時至今日,它們在中國的歷史,斷斷續續,或深或淺,也可以說有千年之歷程了。然而,比較佛教之在中國,其歷史進程又大有不同。
倍受歷史青睞的佛教,從遙遠的印度、西域騎着白馬,來到中華,曾經也受到皇公貴族的疑惑與不同程度的抵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佛教信徒見了皇帝能否下跪磕頭。隋唐之前,佛門高僧為此與朝廷、官方學者沖突了很長時間,最后,佛教信徒終於能夠依照中國國情下跪磕頭了,把皇帝視為當今如來給予敬拜頂禮,佛教也就中國化了。
與此相反,基督宗教之在中國,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交上好運。
大秦景教之時,基督宗教依附於佛教,等到唐武宗滅佛,基督宗教也就隨着滅佛運動被運動去了;元朝有也里可溫發展模式,可惜好景不長。明代中葉之后,基督宗教再度人華,展開了中西文化初具規模的交流與互動。傳統中國信仰如佛教、儒教、道教,均與基督宗教的上帝信仰進行了真正的交往。然而,儒教及其中國人的「三聖信仰」聖人信仰、天命信仰、祖宗崇拜,與當時中國人理解的上帝(天主)信仰構成了沖突,及至「禮儀之爭」的爆發。到了近代,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近代基督宗教騎着炮彈再次進入中國,於是乎教案頻發,在一個充滿軍事、政治斗爭的環境之中,基督宗教始終難以獲得平實的理解。所以,如何理解、容納基督宗教,這一問題,毫無保留地留給了當代中國及其社會。
寓於古今中外之爭,佛教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構成,獲得了中國人的喜愛,往往喜歡稱之為佛教文化,而非佛教信仰;而基督宗教始終是被看作為外來的宗教,甚至沒有被視為基督宗教文化,僅僅是一種外來的宗教而已,沒有文化的象征與包裝。延至今日,全球化背景下諸多復雜因素,外來宗教又常常被看作是不穩定的異己,基督宗教難免首當其沖。
此類問題,如果置於宗教社會學的專業領域,實際上就是基督宗教及其信仰者在中國社會的被信仰現象、存在模式、宗教與文化融合以及身份建構等問題。基督宗教作為一種團體信仰模式,或者是一種共同體的信仰方式,它們與個人化的傳統中國人的信仰方式,不得不說是具有很大差異的。正是在此問題層面,梁漱溟才會說出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一是各信各的、各有各的利益而不求團體制約;一是信仰的共同體實踐要求,基於對一個神的信奉而構成普遍性的行為規范。其間差異大矣。
忽視這一差異,導致了迄今為止的信仰誤解;誇大這一差異.則會出現宗教信仰間的歧視,呈現唯我獨尊的民族信仰立場;利用這一差異,無疑是宗教信仰沖突的根源。
如今的問題是,基督宗教如何能夠成為中國宗教、中國信仰的有機構成部分,或者是當代中國人是否願意使基督宗教成為中國宗教、中國信仰的有機構成部分?
幾十年前,中國人就有「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說法;依據這一觀念,人們試圖以信仰划分國民。基督宗教如果是外來的宗教,那麼,信仰者就不是中國人,而基督宗教就不能成為中國宗教或中國的信仰。當然,隨着幾十年的社會進步與社會變遷,人們的觀念也在與時俱進,於是換了一種說法,這就是「多一個基督徒,多一個五好公民」。可是,問題依舊存在。使用一個五好公民的政治價值判斷,不一定就能夠消解多少年以來形成的宗教信仰偏見。一個中國人,如何能夠去信仰外來的神靈?她會保佑你嗎?上帝會成為中國人的神靈嗎?
這些問題,貌似老問題,實則也是改革開放的新問題。佛教的中國化問題早已解決,但基督宗教曾經也有過處境化、本地化等中國化的努力。時值改革開放今日,中國人只能信仰中國人自己的神靈、依據信仰來划分國民等觀念,也隨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在得以不斷強化。
在此過程之中,中國基督宗教界的努力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然而,中國社會為此本土化或處境化的構成,究竟提供了多大的空間,中國社會是否為基督宗教的中國化提供了相應的社會容納機制?這就是說,基督宗教在致力於適應中國社會,而中國社會在其結構與運作機制層面,是否真正具有了容納這樣一種信仰體系的空間。這些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好幾年前,基於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我就提出過「社會缺席,宗教何在」的問題。因為,一個健全的宗教信仰體系,唯有存在於—個現代社會的框架之中,它才會具有正常的社會整合功能與價值維系。除此之外。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往往會招致曲解或歧視。如果是一個一元化的權力萬能主義,如果是一個國家之下只有原子化國民的一元化社會結構,那麼,任何宗教信仰體系都會因此而被變型。只有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之中,各種宗教、各種信仰才會有機互動、積極對話,從對話的過程之中,轉換或消解那些有可能構成沖突的各種因素。化對抗為對話,轉對話為互動。這就是宗教社會學的「宗教社會化」命題及其意義的所在。
王瑩博士的《身份建構與文化融合——中原地區基督教會個案研究》,可以說就是致力予宗教社會化問題討論的一本專著。它基於王瑩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集中研究了地方鄉村社會中基督教的存在與信仰形式,及其與傳統信仰、民間習俗之間的互動關系,乃至基督教信仰與民間信仰習俗之間的相互吸納關系。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民間信俗得以復興的社會背景之下,基督教如何與之良性互動,如何在此過程中,設法把基督教及其信仰形式建構為中國人真正的信仰模式之一,甚至能夠像佛教那樣,使基督教成為中國宗教、中國文化、中國信仰習俗的有機構成部分,此乃為新時代框架中一種「新禮儀之爭」所應當具有的時代意義。雖然三百多年前,導致「禮儀之爭」的諸多因素依舊存在,祭天、祭聖人、祭祖等三聖信仰關系,依舊是中國信仰的諸類核心價值,但是社會的變遷以及社會容納空間的擴大,促使傳統的禮儀之爭,具有了新的社會學意義,此乃鄉村基督教及其「新禮儀之爭」給人的一個樂觀期待。這就構成了王瑩之鄉村基督教研究的學術價值。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民間基督教」(popular Christi-anity)這一概念,說明基督教在中國民間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問題,越來越受到相關學術界的關注。而王瑩的論著似乎也在討論這樣一些問題,比如基督教在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格局,基督教在中國的民間信仰形式,是否能夠構成與中國民間信仰有機互動的基督教信仰等等。我們期待着,民間基督教研究的繼續深入與王瑩博士的繼續努力。
拉拉雜雜,一些感想,權作為序。
李向平 2011年6月9日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