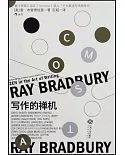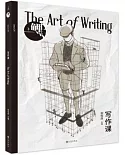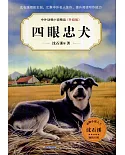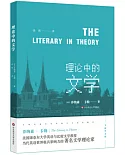本書是「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文庫」系列之一。
本書以三個層面的布局較為集中地闡發了著者在比較文學領域中通過東亞「文學關系」研究的學術實踐與對相應的「比較詩學」的思考,逐步綜合人文領域相關部類的學識而形成的「文學發生學」的學理觀念與方法論系統。在闡述學術觀念的同時,以對日本經典文本解析的實際「個案」與對同一主題的十余部著作的評述為范本,試圖展示以「文本細讀」為研究基礎,以把握「多元文化語境」為觀察文化的基本視角,力圖在文明流動與傳遞的「不正確理解」的通道中,最終揭示文明時代多類型文化的本質,由此而闡明以「文化變異體」為核心的「文化發生學」的基本學理。
目錄
自序:我走上「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化歷程
第一編 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觀念——關於「比較文學」一般觀念的思考
創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國學派的構想
樹立科學的比較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
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名稱的質疑
關於比較文學博士養成的淺見
賈植芳先生的比較文學觀
樂黛雲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之路——她對20世紀最后30年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的啟示
第二編「比較文學」領域中的「變異體」研究——關於「比較文學」的「發生學」研究的思考
關於文學「變異體」與發生學的思考
確立關於表述「東亞文學」歷史的更加真實的觀念——我對「比較文學研究」課題的思考和追求
民族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文學空間——為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創刊20周年而作
「文學」與「比較文學」同在共存——由巴斯奈特發表的論說引發的思考
確立「比較文學」研究的本體論觀念——就《中外文學交流史》15卷起筆事致錢林森教授書
第三編 關於「Sinology」的屬性與范疇的思考——提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國際「Sinology」研究范疇的界定
我對國際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
中國學術界對 Sinology 研究應有的反思
第四編 「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思考
雙邊文化和多邊文化研究的原典實證的觀念與方法論
第五編 關於「比較文學」的「發生學」文本解析實踐
日本「記紀神話」變異體的模式和形態及其與中國文化的關聯
日本「浦島文學」成型中「中間媒體」的意義
日本江戶時代「町人文學」繁榮的「文化語境」研討——關於中國明清俗語文學東漸的幾個問題
中國儒學在日本近代「變異」的考察——追蹤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的「儒學觀」:「源文化」在異質文化
中傳遞的「不正確理解」的個案解析
第六編 關於「比較文學」的「發生學」研究范例的評述
關於中國文學中日本形象的生成——序張哲俊著《中國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白居易文學進入日本古典的形態——序雋雪艷著《文化的重寫: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空海和尚學術概念的生成——序王益鳴著《空海學術的范疇研究》
日本江戶時期漢學家最后的學問——序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
內藤湖南學術的生成軌跡——序錢婉約著《內藤湖南研究》
津田左右吉學術的文化語境特征——序劉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從文化語境中透視真實的廚川白村——序李強著《廚川白村研究》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創作力的特征——序王琢著《想象力論: 大江健三郎的小說方法》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文學的東方文化語境——序周閱著《川端康成文學的文化學研究》
日本當代中國學的耆宿: 雙邊文化學者養成的條件——序《戶川芳郎古稀紀念文集》
歐洲人「赫恩文學」的實像與日本人「小泉文學」的虛影——序牟學苑著 《拉夫卡迪奧·赫恩文學的發生學研究》
附 嚴紹相關本書主題的論著(1979—2010年)目錄
后記
第一編 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觀念——關於「比較文學」一般觀念的思考
創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國學派的構想
樹立科學的比較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
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名稱的質疑
關於比較文學博士養成的淺見
賈植芳先生的比較文學觀
樂黛雲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之路——她對20世紀最后30年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的啟示
第二編「比較文學」領域中的「變異體」研究——關於「比較文學」的「發生學」研究的思考
關於文學「變異體」與發生學的思考
確立關於表述「東亞文學」歷史的更加真實的觀念——我對「比較文學研究」課題的思考和追求
民族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文學空間——為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創刊20周年而作
「文學」與「比較文學」同在共存——由巴斯奈特發表的論說引發的思考
確立「比較文學」研究的本體論觀念——就《中外文學交流史》15卷起筆事致錢林森教授書
第三編 關於「Sinology」的屬性與范疇的思考——提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國際「Sinology」研究范疇的界定
我對國際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
中國學術界對 Sinology 研究應有的反思
第四編 「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思考
雙邊文化和多邊文化研究的原典實證的觀念與方法論
第五編 關於「比較文學」的「發生學」文本解析實踐
日本「記紀神話」變異體的模式和形態及其與中國文化的關聯
日本「浦島文學」成型中「中間媒體」的意義
日本江戶時代「町人文學」繁榮的「文化語境」研討——關於中國明清俗語文學東漸的幾個問題
中國儒學在日本近代「變異」的考察——追蹤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的「儒學觀」:「源文化」在異質文化
中傳遞的「不正確理解」的個案解析
第六編 關於「比較文學」的「發生學」研究范例的評述
關於中國文學中日本形象的生成——序張哲俊著《中國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白居易文學進入日本古典的形態——序雋雪艷著《文化的重寫: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空海和尚學術概念的生成——序王益鳴著《空海學術的范疇研究》
日本江戶時期漢學家最后的學問——序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
內藤湖南學術的生成軌跡——序錢婉約著《內藤湖南研究》
津田左右吉學術的文化語境特征——序劉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從文化語境中透視真實的廚川白村——序李強著《廚川白村研究》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創作力的特征——序王琢著《想象力論: 大江健三郎的小說方法》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文學的東方文化語境——序周閱著《川端康成文學的文化學研究》
日本當代中國學的耆宿: 雙邊文化學者養成的條件——序《戶川芳郎古稀紀念文集》
歐洲人「赫恩文學」的實像與日本人「小泉文學」的虛影——序牟學苑著 《拉夫卡迪奧·赫恩文學的發生學研究》
附 嚴紹相關本書主題的論著(1979—2010年)目錄
后記
序
謝天振、陳思和與宋炳輝三位先生主編「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文庫」,旨在集合30余年來我國學界人士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表述的多彩智慧,展現比較文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的實踐與經驗,既可為國人繼續推進這一學術提供參考和提示,從而或許多少可以削弱一些在這個領域市「言必稱希臘」的「無主體」狀態;又可為中國學界與國際同行的對話建立起較成規模的研討平台,展示「中國話語」的力量。此於人文學界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2009年初春,文庫主編之一宋炳輝先牛來京告訴我這件事情,感到很是振奇。炳輝告訴我,規划中邀約的單子上也列有我的文稿,則又感到受寵若驚。這倒小是故作虛偽,實在是我自己感到,在我50年的人文學術生涯中,特別是30余年來逐步走進「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我的學術基礎、學術起步與學術實踐,與我們比較文學學術研究領域中人多數學者的狀態,殊不一致。自己數十年來依憑興趣,經常在兒個「學科」的層面中融合操作。知我者譽我「融通」,不知我者責我「越界」。炳輝兄至誠感人,熱情可掬,他轉達思和、天振二兄盛邀之情,又是復旦人學出版社這樣的知名學術機構刊出,我就被鼓勵和被誘惑到這項很有意義的學術工作中來了。
綜觀世界華人學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路徑,大致有兩種歷程狀態較為普遍。一種是在國別文化(中國的或世界各國)的研究中,逐步接受了「比較文學」的基本學理,於是在不同的學術層次和層面中躍起而進入「跨文化立場」的「比較文學」研究;一種是在尚未形成自己的國別文化研究本位時,已經先行接受了「比較文學」的學理,直接進入這一領域。上述兩大營壘雖然出發點不一,但幾乎都是在學術的行程中受到歐美「比較文學」基本學理的洗禮而一步躍入這一「學術殿堂」的。我自己在這個領域中的行程,顯得非常異類。直到現在使自己忐忑不安的是,閃為至今我也沒有接受過學界普遍認定的耶種「純正學理」的洗禮,卻已經在這個神聖的祭壇上做起了彌撒,盡管當下學界有朋友對我在30余年間以「文本解析」為基礎而積累的關於「跨文化研究」的實踐和經驗,以「文化變異體」為核心提出的「文本發生學」論說,給予了不少的美譽,但也有些先生和朋友對我在學界的「身份」(假如有這樣的「身份」標識的話)持有異見,沒有一定之規。
(一)
回憶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北京入學在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古典文獻專業讀書,用今大學界最時髦的話來說,受到的是很經典的「國學」教育,然而自己在一生的學術道路中卻在不知不覺跌跌撞撞間竟然走到了被學術界稱為「最前沿學科」的「比較文學領域」中了(假定自己走的這條道還叫做「學術」的話).小禁感慨良多。
回想50多年來自己的歷程,不知足天性的使然,還足先輩的教導,或許二者兼而有之,自己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在最基礎層面上接受最基礎的「國學」教育的時候,常常有些「躁動不安」的質疑,例如我常常捉摸我們的「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的總體進程究竟是什麼關系?有時候又捉摸當時提倡的所謂「占為令用」究竟應該怎麼個用法?自己的這些質疑埋在心底,卻總想知道其所以然。學生時代依據「教學大綱」讀到的書本,從《周易》、《尚書》到儒學宗師孔老先生等諸子百家,由此延續數千年一直到浩如煙海的《皇清經解》,都是中國人編著的給中國人讀的書;為我們講授課程的先輩,皆是學界名師,當代在各種「論壇」上那些花里胡哨張揚妄說的「專家學者」豈能望其項背!像游國恩、林庚、馮鍾芸、吳組緗諸先生講授「中國文學史」,張政琅、田余慶、鄧廣銘諸先生講授「中國史」,張岱年、馮友蘭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和「史料學」,顧頡剛先生講授「中國經學史」,魏建功先生講授「文字音韻訓沾學」,王重民先生講授《目錄版本校勘學》,王力,吉常宏先生講授《古代漢語》,林濤、朱德熙先生講授《現代漢語》,以及由郭沫若、吳晗濟燕銘、候仁之、席澤忠、向達、史樹青、啟功、陰法魯諸先生組成的巨大陣容連續兩年講授《中國文化史》。他們皆是經綸滿腹的天下名士。我等聽諸位先生的講授,趣味叢生,自己考試竟然門門得了「五分」。盡管「學術氛圍」很是濃重,但諸位導師講授的卻還只是在中國范圍內的關於中國古文化的學識,自己心里的質疑時時作祟,揮之不去。時間稍長一些,與諸先生在「私下」的聊天中卻似乎又慢慢明白了許多,原來諸位先輩導師在當時課堂上依照「教學大綱」的講授與他們本身所具備的知識量其實是不相等的,他們滿腹經綸好像只透露了一半似的,例如,專業主任魏建功先生與我們「聊天」,說他20年代在北大當學生,先師錢玄同使用的是瑞典學者高本漢(B.Karlgren)構擬的《切韻音系》作為教本來講授「漢語聲韻學」的。魏先生是放學術界定評為「架起了從傳統的音韻學研究通向近代音韻學研究的橋粱」,他作為近代漢語音韻學的奠基者的學識表述以《古音系研究》為主要的代表。我受好奇心驅使,於是找來此書閱讀,想一明究竟,翻閱后則使我大受震動。先生在大著中明確說,「這十年中的情況(指上世紀20—30年代),我們音韻學的新建設現在才算有一點萌芽。想當初,十年前我聽錢玄同先生講的時候,他就拿高本漢的著作作為教材,同時說明他自己的主張」。我讀到此段,便一時興發查查「高本漢」的業績如何,才知道原來他是20世紀初歐洲傑出的中國學家,擅長於漢語音韻訓詁的研究。使我更加震驚的事是,高本漢1889年出牛,當時還是個不算年老的學人,但是在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有卓著名望的驍將之一錢玄同先生,雖然年齡比高本漢還大兩歲,卻拿小弟的著作作為教本,可見前輩不居高視下,積極尋求新學問的氣度。錢先生不僅把歐洲人關於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引入自己的學問中,並且引導他的學生建立「中國文化的新視野」。再讀魏先生的書,先生在自己的論說中對於極為豐厚的漢語語料的「聲韻學」闡述,除了以自我的思辨提純我國傳統的研究觀念和方法論之外,還遵循他導師的軌跡,高度重視歐洲由沙畹(E.Chavnnes)、伯希和(P.Pelliot)等在《通報》上發表的有關「Sinology」的相關闡釋,特別是由伯希和與馬伯樂(H.Masporo)所做的關於漢語古音的構定,並且追蹤由愛約瑟(J.Edkins)、賽萊凱爾(F.Schlegci)、武爾皮奇利(Z.Volpicelli)、桑克(S.H.Schaank)和伏爾克(A.Forke)等學者提出的主張。原來被我們這等學生視為非常枯燥和閉關的「漢語音韻學」,在歐洲學界竟然有這麼多的學者關心,並且創造出如此熱鬧的世界;而被人指責為「封建余孽」的魏建功先生,竟然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具有如此寬闊的學術視野,直是為我等后人打開了一個偌大的視窗。恰好當時,我用一學期的時間,修完了北大規定的兩年半的英語,魏先生就對我說,「你再去讀點日文吧,日本人搞了我們很多東西,將來總歸要有人來清理的」。於是,我就邊上日文課,邊閱讀一些日文的「中國學」的著作,記得上《史記》課的時候,我就嘗試翻譯日本學者撰著的《司馬遷生卒年考》,感覺到其對中國學術的表述真的還有一種新天地。於是便尋思這個「Sinology」或許就是我們中國文化與世界連接的一種「通道」吧?
一個人一生中的道路在冥冥之中或許可能真的與「機運」有着一些聯系的。1964年由於當時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先生在與學界數位大先生協商后,希望把由1948年被我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北京的過程中在京西美國燕京大學封存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機構」即「燕京一哈佛學社」的檔案進行拆封登錄,「看看有哪些對我們文化建設還是有用的」,他要求北大安排一兩個年輕助教,乘着原來的中方老人還在,讓他們做些指導,好好地做起來。經過北大謹慎研討,出身「黑類」的嚴紹塑被留校作為助教從事此項工作。現在想來,齊燕銘先生作為國家高級領導成員,大概是想對「燕京一哈佛學社」實施「解禁」,似乎希單以此為一個突破門,拓展中國文化研究的世界性眼光。但是,這個工作我實際上只做了不到兩個月,齊先生就被毛澤東主席指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由他規划的人文學術在一個角落里的整頓、重組和復興被阻斷了。但對於我來說,齊先生雖然不幸被臨禁,但「Sinology」這個概念,卻與我學生時代的朦朧的感覺桕契合,由此在我心中播下了努力探索「中國文化」與「世界連接」的學術性「種子」,開辟了一生的道路。
……
2009年初春,文庫主編之一宋炳輝先牛來京告訴我這件事情,感到很是振奇。炳輝告訴我,規划中邀約的單子上也列有我的文稿,則又感到受寵若驚。這倒小是故作虛偽,實在是我自己感到,在我50年的人文學術生涯中,特別是30余年來逐步走進「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我的學術基礎、學術起步與學術實踐,與我們比較文學學術研究領域中人多數學者的狀態,殊不一致。自己數十年來依憑興趣,經常在兒個「學科」的層面中融合操作。知我者譽我「融通」,不知我者責我「越界」。炳輝兄至誠感人,熱情可掬,他轉達思和、天振二兄盛邀之情,又是復旦人學出版社這樣的知名學術機構刊出,我就被鼓勵和被誘惑到這項很有意義的學術工作中來了。
綜觀世界華人學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路徑,大致有兩種歷程狀態較為普遍。一種是在國別文化(中國的或世界各國)的研究中,逐步接受了「比較文學」的基本學理,於是在不同的學術層次和層面中躍起而進入「跨文化立場」的「比較文學」研究;一種是在尚未形成自己的國別文化研究本位時,已經先行接受了「比較文學」的學理,直接進入這一領域。上述兩大營壘雖然出發點不一,但幾乎都是在學術的行程中受到歐美「比較文學」基本學理的洗禮而一步躍入這一「學術殿堂」的。我自己在這個領域中的行程,顯得非常異類。直到現在使自己忐忑不安的是,閃為至今我也沒有接受過學界普遍認定的耶種「純正學理」的洗禮,卻已經在這個神聖的祭壇上做起了彌撒,盡管當下學界有朋友對我在30余年間以「文本解析」為基礎而積累的關於「跨文化研究」的實踐和經驗,以「文化變異體」為核心提出的「文本發生學」論說,給予了不少的美譽,但也有些先生和朋友對我在學界的「身份」(假如有這樣的「身份」標識的話)持有異見,沒有一定之規。
(一)
回憶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北京入學在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古典文獻專業讀書,用今大學界最時髦的話來說,受到的是很經典的「國學」教育,然而自己在一生的學術道路中卻在不知不覺跌跌撞撞間竟然走到了被學術界稱為「最前沿學科」的「比較文學領域」中了(假定自己走的這條道還叫做「學術」的話).小禁感慨良多。
回想50多年來自己的歷程,不知足天性的使然,還足先輩的教導,或許二者兼而有之,自己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在最基礎層面上接受最基礎的「國學」教育的時候,常常有些「躁動不安」的質疑,例如我常常捉摸我們的「中華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的總體進程究竟是什麼關系?有時候又捉摸當時提倡的所謂「占為令用」究竟應該怎麼個用法?自己的這些質疑埋在心底,卻總想知道其所以然。學生時代依據「教學大綱」讀到的書本,從《周易》、《尚書》到儒學宗師孔老先生等諸子百家,由此延續數千年一直到浩如煙海的《皇清經解》,都是中國人編著的給中國人讀的書;為我們講授課程的先輩,皆是學界名師,當代在各種「論壇」上那些花里胡哨張揚妄說的「專家學者」豈能望其項背!像游國恩、林庚、馮鍾芸、吳組緗諸先生講授「中國文學史」,張政琅、田余慶、鄧廣銘諸先生講授「中國史」,張岱年、馮友蘭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和「史料學」,顧頡剛先生講授「中國經學史」,魏建功先生講授「文字音韻訓沾學」,王重民先生講授《目錄版本校勘學》,王力,吉常宏先生講授《古代漢語》,林濤、朱德熙先生講授《現代漢語》,以及由郭沫若、吳晗濟燕銘、候仁之、席澤忠、向達、史樹青、啟功、陰法魯諸先生組成的巨大陣容連續兩年講授《中國文化史》。他們皆是經綸滿腹的天下名士。我等聽諸位先生的講授,趣味叢生,自己考試竟然門門得了「五分」。盡管「學術氛圍」很是濃重,但諸位導師講授的卻還只是在中國范圍內的關於中國古文化的學識,自己心里的質疑時時作祟,揮之不去。時間稍長一些,與諸先生在「私下」的聊天中卻似乎又慢慢明白了許多,原來諸位先輩導師在當時課堂上依照「教學大綱」的講授與他們本身所具備的知識量其實是不相等的,他們滿腹經綸好像只透露了一半似的,例如,專業主任魏建功先生與我們「聊天」,說他20年代在北大當學生,先師錢玄同使用的是瑞典學者高本漢(B.Karlgren)構擬的《切韻音系》作為教本來講授「漢語聲韻學」的。魏先生是放學術界定評為「架起了從傳統的音韻學研究通向近代音韻學研究的橋粱」,他作為近代漢語音韻學的奠基者的學識表述以《古音系研究》為主要的代表。我受好奇心驅使,於是找來此書閱讀,想一明究竟,翻閱后則使我大受震動。先生在大著中明確說,「這十年中的情況(指上世紀20—30年代),我們音韻學的新建設現在才算有一點萌芽。想當初,十年前我聽錢玄同先生講的時候,他就拿高本漢的著作作為教材,同時說明他自己的主張」。我讀到此段,便一時興發查查「高本漢」的業績如何,才知道原來他是20世紀初歐洲傑出的中國學家,擅長於漢語音韻訓詁的研究。使我更加震驚的事是,高本漢1889年出牛,當時還是個不算年老的學人,但是在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有卓著名望的驍將之一錢玄同先生,雖然年齡比高本漢還大兩歲,卻拿小弟的著作作為教本,可見前輩不居高視下,積極尋求新學問的氣度。錢先生不僅把歐洲人關於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引入自己的學問中,並且引導他的學生建立「中國文化的新視野」。再讀魏先生的書,先生在自己的論說中對於極為豐厚的漢語語料的「聲韻學」闡述,除了以自我的思辨提純我國傳統的研究觀念和方法論之外,還遵循他導師的軌跡,高度重視歐洲由沙畹(E.Chavnnes)、伯希和(P.Pelliot)等在《通報》上發表的有關「Sinology」的相關闡釋,特別是由伯希和與馬伯樂(H.Masporo)所做的關於漢語古音的構定,並且追蹤由愛約瑟(J.Edkins)、賽萊凱爾(F.Schlegci)、武爾皮奇利(Z.Volpicelli)、桑克(S.H.Schaank)和伏爾克(A.Forke)等學者提出的主張。原來被我們這等學生視為非常枯燥和閉關的「漢語音韻學」,在歐洲學界竟然有這麼多的學者關心,並且創造出如此熱鬧的世界;而被人指責為「封建余孽」的魏建功先生,竟然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具有如此寬闊的學術視野,直是為我等后人打開了一個偌大的視窗。恰好當時,我用一學期的時間,修完了北大規定的兩年半的英語,魏先生就對我說,「你再去讀點日文吧,日本人搞了我們很多東西,將來總歸要有人來清理的」。於是,我就邊上日文課,邊閱讀一些日文的「中國學」的著作,記得上《史記》課的時候,我就嘗試翻譯日本學者撰著的《司馬遷生卒年考》,感覺到其對中國學術的表述真的還有一種新天地。於是便尋思這個「Sinology」或許就是我們中國文化與世界連接的一種「通道」吧?
一個人一生中的道路在冥冥之中或許可能真的與「機運」有着一些聯系的。1964年由於當時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先生在與學界數位大先生協商后,希望把由1948年被我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北京的過程中在京西美國燕京大學封存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機構」即「燕京一哈佛學社」的檔案進行拆封登錄,「看看有哪些對我們文化建設還是有用的」,他要求北大安排一兩個年輕助教,乘着原來的中方老人還在,讓他們做些指導,好好地做起來。經過北大謹慎研討,出身「黑類」的嚴紹塑被留校作為助教從事此項工作。現在想來,齊燕銘先生作為國家高級領導成員,大概是想對「燕京一哈佛學社」實施「解禁」,似乎希單以此為一個突破門,拓展中國文化研究的世界性眼光。但是,這個工作我實際上只做了不到兩個月,齊先生就被毛澤東主席指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由他規划的人文學術在一個角落里的整頓、重組和復興被阻斷了。但對於我來說,齊先生雖然不幸被臨禁,但「Sinology」這個概念,卻與我學生時代的朦朧的感覺桕契合,由此在我心中播下了努力探索「中國文化」與「世界連接」的學術性「種子」,開辟了一生的道路。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