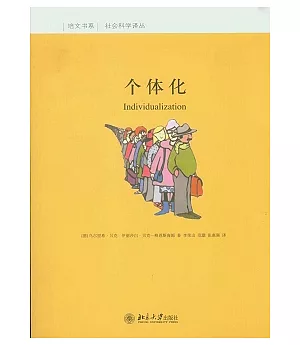個體化再探︰一種普世主義視角
世界秩序崩潰之時,即是理當開始反思之時。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就當今主流社會理論而言,情況卻並非如此。主流社會理路帶著其普遍主義的優越性和天生的不確定性,依然高懸在種種重大轉變(氣候變化、金融危機和民族國家)的上空。這種普遍主義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主義、互動論、馬克思主義,還是系統理論,如今看來既是過時的,也是偏頗的。說它們過時,是因為它們先驗地排除了能被經驗觀察到的東西︰社會和政治在現代性之下經歷了一個根本的轉變(從第一現代性轉向第二現代性);說它們偏頗,是因為它們錯誤地把發展軌跡,把以歐洲和北美為主的西方歷史經驗和未來期望,把現代化給絕對化了,忽略了其獨特性。
其結果就是,必須在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中引發一次普世主義轉向(Beck,2006;Beck/Sznaider,2006;Beck/Grande,2010)︰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如何才能向一種新近出現的、扭結纏繞的,危及其自身基礎的現代性敞開?如何解釋21世紀初在資本和風險的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種種社會動力(包括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支配和權力)的根本脆弱性和易變性?出現了哪些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在經驗研究中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下面我們將就以上問題展開討論。首先,我們特地指出了一些概念和方法論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在這一觀念轉變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一、二兩節);其次,我們會通過中國和歐洲個體化路徑的比較,來具體呈現這些問題(三、四兩節)。
一
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前提中有一種美妙的觀念︰可以把歐洲理論擴散或移用至歐洲以外的地方。長期來看,一切社會都會屈從傳統和現代這種現代性的經典區分,並復制西方現代性的典型制度模式,後者是可資利用的“世界通行曲日”(Stichweh,2000,p.256)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發展程度也不同,不過,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一旦踏上現代化之路,就或多或少會邁向相同的目標……一切非現代的文化和社會結構終將讓位于現代文化和社會結構。這是它們的宿命。
(Berger. 2006, pp.202-204)
現代性也許有各種變體,但卻不存在基于不同現代化標準的多種獨立現代性(autonomous
modernities)。到處都在上演“不同演員參與的同一出戲”(Berger,2006,p.203)。作為這一擴散過程的後果之一,經驗研究得出結論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日漸一致的世界中。人們似乎達成了共識︰21世紀的社會將是一個“世界社會”,是一個“整體”,在其中形成了某種“元文化”(Stichweh,2000,p.22;Meyer,2005)。將這種邏輯推至極端就意味著,隨著現代性這項普遍事業的完成,“歷史的終結”(
Fukuyama.1992)已成事實。反過來說也成立︰我們正面臨著歷史終結的終結(the end ofthe end ofhistory)。
這是一種趨同(convergence)預期,相信同質性的、普遍的(西方)現代性模式遲早會遍及全世界。我們的自反性現代化理論恰恰與這種預期相反。社會理論中“普世主義轉向”的關鍵,一方面在于,社會理論要向各種不同的、獨立而又彼此聯系的種種現代性(“多元現代性”)的可能性敞開;另一方面在于,要向新的、全球性的命令(imperatives)、壓力和約束敞開。這些新的“普世命令”並非普遍給定的,而是在21世紀初(歷史地)累積起來的,它們造就了新的沖突結構、沖突動力和新的共同體構築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