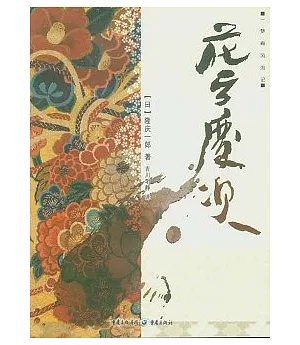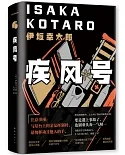★“天下御免”的男類男子
破滅美學的極致體驗
生存夾縫中的冒險傳奇
戰國第一傾奇者的任俠與逍遙
本書是一本時代小說,雖然其中也錯綜交織著大量史實與真實歷史人物,內容畢竟屬于七實三虛,前田慶次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離不開小說原作者隆慶一郎嘔心瀝血的拳拳創作。
隆慶一郎在中國的知名度不如司馬遼太郎、井上靖、山岡莊八等知名歷史小說家,或許當歸過于他的大器晚成和日後的急逝。隆慶一郎本是影視劇本作家,作為小說家發表處女作《吉原御免狀》是在1984年(61歲),這本交織著諸多歷史謎團的小說一問世便博得了廣泛的好評。隆慶一郎與其他歷史小說家最大的風格特點區別在于兩點︰一是在人物尤其是庶民生活的描寫上非常細致秀逸;二是愛以史料為基礎來展開對歷史真相天巴行空的想象。其代表作就是《一夢庵風流記》和《影武者德川家康》(後者亦由原哲夫先生進行了漫畫化),而前者更是在1989年一舉獲得柴田煉三郎文學獎。
目錄
序
第一章 傾奇者
第二章 無欲之人
第三章 松風
第四章 招待
第五章 敦賀城
第六章 七里半嶺
第七章 聚樂第(上)
第八章 聚樂第(下)
第九章 決斗之風
第十章 奪心男子
第十一章 骨
第十二章 女體
第十三章 死地
第十四章 攻打佐渡
第十五章 傀儡子舞
第十六章 捕童
第十七章 治部(上)
第十八章 治部(下)
第十九章 入唐
第二十章 伽琴
第二十一章 伽姬
第二十二章 漢陽
第二十三章 歸還
第二十四章 入唐之陣
第二十五章 難波之夢
第二十六章 奪取天下
第二十七章 會津陣
第二十八章 最上之戰
第二十九章 講和
第三十章 風流
作者後記
譯後記
第一章 傾奇者
第二章 無欲之人
第三章 松風
第四章 招待
第五章 敦賀城
第六章 七里半嶺
第七章 聚樂第(上)
第八章 聚樂第(下)
第九章 決斗之風
第十章 奪心男子
第十一章 骨
第十二章 女體
第十三章 死地
第十四章 攻打佐渡
第十五章 傀儡子舞
第十六章 捕童
第十七章 治部(上)
第十八章 治部(下)
第十九章 入唐
第二十章 伽琴
第二十一章 伽姬
第二十二章 漢陽
第二十三章 歸還
第二十四章 入唐之陣
第二十五章 難波之夢
第二十六章 奪取天下
第二十七章 會津陣
第二十八章 最上之戰
第二十九章 講和
第三十章 風流
作者後記
譯後記
序
寫在《花之慶次》之前
日文小說的翻譯,一向是件困難的事。
雖然我們總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啦,又都是漢字文化圈內的一員,可兩國在文化上的差異,卻往往比想象中大上許多。事實上,日文翻譯的難度,比起歐美語系文學作品來說不遑多讓,甚至有所過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種清淺、平淡的風格,已經深深地滲透進了日文的骨髓之中,遠如井原西鶴、曲亭馬琴,近如莽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他們的文筆各有千秋,卻總有一種特有的味道索繞在不同風格的著作之間,讓人一眼望去,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筆,幾乎可稱為文化血統。
若想在把日文轉譯到中文的時候,保留這一種“味道”,並不容易。錢錘書在討論林紓的翻譯時曾明確對翻譯提出一個要求︰“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舍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
這個標準是相當高的,尤其對日本文學來說尤其顯著許多譯者因為中日文化的傳承關系,而武斷地認為可以直接取中土風格強行嫁接,渾然不覺兩者之問的差異,以致喪失了本有的風格與味道。
如豐子愷所譯的《源民物語》,文字頗為流暢,確實不錯。但我個人的感覺,總有一種看《三言二拍》的錯覺,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種特有的“平安風”韻味。所以周作人批評此譯本“喜用俗惡成語,對于平安朝文學的空氣,似全無了解”。就連豐子峨眉山自己也在譯後記里承認“恨未能表達原諒之風格也”。可見倘若譯者對于作品本身所處時代、作者所處時代沒有一個精深的了解,翻譯出來的東西總會不倫不類。
即便是現代作品,比如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有林少華、賴興珠兩種譯本流派,風格迥異,各自都有擁躉。林派譏賴譯粗疏,賴派嫌林譯土氣,至今爭論不休,難分軒輊。
如何忠實于原本,如何準確體現出原本文字風貌,這是從作者角度來說,對譯者的考驗。
但考驗並沒有結束。
從讀者的角度來說,要想讓慣于濃烈渲染的中國讀者接受日文這種風格——尤其是日文小說的風格——也十分不容易。以《花之慶次》這本小說為例,就能看出中日兩國作家對一些細節處理的異趣與不同。比如開篇談到駿馬松風,倘若是中國作家,泰半會在此費上一番筆墨,通過馬夫、衛兵等下人之口把這匹馬的傳奇故事大大地演繹出來,從小處反襯凸顯出慶次的英雄氣概;而作者卻放過這一個大好機會。反以淡淡的筆觸平板直敘,娓娓道來。這種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佐渡一戰,本是慶次單騎奪城,如常山趙子龍般華麗的上好戲碼,作者卻並未著力渲染,字里行間卻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種刻意壓抑的豪情。
兩種處理方式熟優熟劣,見仁見智。就像是中日飲食一樣,前者華貴絢爛,後者清淡素雅,各有口味不同罷了。其實還都要看廚子的功力如何。若踫到個劣手,就是再好的菜譜,也做不出佳肴;反之,倘若廚師本身手段高超,又深諳食客口味,做出來的確良東西即便風格不同,一樣可以大快朵頤。
我曾經看過一版司機遼太郎的中譯本,實在是不忍卒睹,通篇像老太婆一樣絮絮叨叨,另外唆無比,害得我以為是作者的問題,大罵司馬“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直到看到另外一位先生的譯本,才知道司馬本身文字是好的,只是生生被拙劣的翻譯給連累了。
所以說,翻譯日文作品,與其說這是對作者的試煉,毋寧說是對譯者的一個極大考驗。翻譯很好,能夠讓人如漆春風,于清談處听驚雷;翻譯得不好,便會味如嚼蠟。常言道︰“翻譯筆若是再創作”,誠不我欺。
……
日文小說的翻譯,一向是件困難的事。
雖然我們總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啦,又都是漢字文化圈內的一員,可兩國在文化上的差異,卻往往比想象中大上許多。事實上,日文翻譯的難度,比起歐美語系文學作品來說不遑多讓,甚至有所過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種清淺、平淡的風格,已經深深地滲透進了日文的骨髓之中,遠如井原西鶴、曲亭馬琴,近如莽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他們的文筆各有千秋,卻總有一種特有的味道索繞在不同風格的著作之間,讓人一眼望去,使知出自日本作家手筆,幾乎可稱為文化血統。
若想在把日文轉譯到中文的時候,保留這一種“味道”,並不容易。錢錘書在討論林紓的翻譯時曾明確對翻譯提出一個要求︰“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舍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
這個標準是相當高的,尤其對日本文學來說尤其顯著許多譯者因為中日文化的傳承關系,而武斷地認為可以直接取中土風格強行嫁接,渾然不覺兩者之問的差異,以致喪失了本有的風格與味道。
如豐子愷所譯的《源民物語》,文字頗為流暢,確實不錯。但我個人的感覺,總有一種看《三言二拍》的錯覺,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種特有的“平安風”韻味。所以周作人批評此譯本“喜用俗惡成語,對于平安朝文學的空氣,似全無了解”。就連豐子峨眉山自己也在譯後記里承認“恨未能表達原諒之風格也”。可見倘若譯者對于作品本身所處時代、作者所處時代沒有一個精深的了解,翻譯出來的東西總會不倫不類。
即便是現代作品,比如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有林少華、賴興珠兩種譯本流派,風格迥異,各自都有擁躉。林派譏賴譯粗疏,賴派嫌林譯土氣,至今爭論不休,難分軒輊。
如何忠實于原本,如何準確體現出原本文字風貌,這是從作者角度來說,對譯者的考驗。
但考驗並沒有結束。
從讀者的角度來說,要想讓慣于濃烈渲染的中國讀者接受日文這種風格——尤其是日文小說的風格——也十分不容易。以《花之慶次》這本小說為例,就能看出中日兩國作家對一些細節處理的異趣與不同。比如開篇談到駿馬松風,倘若是中國作家,泰半會在此費上一番筆墨,通過馬夫、衛兵等下人之口把這匹馬的傳奇故事大大地演繹出來,從小處反襯凸顯出慶次的英雄氣概;而作者卻放過這一個大好機會。反以淡淡的筆觸平板直敘,娓娓道來。這種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佐渡一戰,本是慶次單騎奪城,如常山趙子龍般華麗的上好戲碼,作者卻並未著力渲染,字里行間卻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種刻意壓抑的豪情。
兩種處理方式熟優熟劣,見仁見智。就像是中日飲食一樣,前者華貴絢爛,後者清淡素雅,各有口味不同罷了。其實還都要看廚子的功力如何。若踫到個劣手,就是再好的菜譜,也做不出佳肴;反之,倘若廚師本身手段高超,又深諳食客口味,做出來的確良東西即便風格不同,一樣可以大快朵頤。
我曾經看過一版司機遼太郎的中譯本,實在是不忍卒睹,通篇像老太婆一樣絮絮叨叨,另外唆無比,害得我以為是作者的問題,大罵司馬“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直到看到另外一位先生的譯本,才知道司馬本身文字是好的,只是生生被拙劣的翻譯給連累了。
所以說,翻譯日文作品,與其說這是對作者的試煉,毋寧說是對譯者的一個極大考驗。翻譯很好,能夠讓人如漆春風,于清談處听驚雷;翻譯得不好,便會味如嚼蠟。常言道︰“翻譯筆若是再創作”,誠不我欺。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