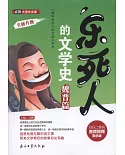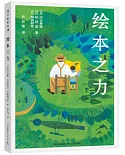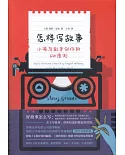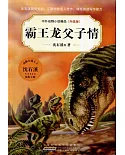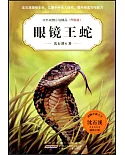蒼涼是一種參差的對照,世故是一場刻骨的悲涼。張愛玲——從小人物世界創造的新傳奇。
「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張愛玲認為,具有啟示性的「蒼涼」的顯現能揭示素朴的真理。她以一種卡桑德拉式的姿態和當時彌漫的民族氣質和革命進程唱反調,卻從日常生活的小人物世界創造了另一種「新傳奇」。
真正的愛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在那個時間終端,時間本身便不再重要。正是在那樣的時刻,張愛玲的「蒼涼」美學才是可以想象的,她的世故也從刻骨的悲涼中釀出。
《蒼涼與世故》收入了著名學者李歐梵為張迷們寫的關於張愛玲的文章,並且在原版本的基礎上新增了他為《色戒》寫的所有電影評論。
本書匯集了李歐梵教授近年新寫的六篇關於張愛玲的研究論文。《蒼涼與世故》的前半部分談論張愛玲,蒼涼代表了張愛玲自己的美學觀點,世故則體現了作者對張愛玲的看法。後半部分則是作者在香港生活的所思所行,對於作者來說,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沖擊下,仍能夠堅持閱讀、觀察和思考,既是一種歡喜,也是一種失落?
李歐梵,一九三九年生於河南,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哈佛大學等,現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鐵屋中的吶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話語》等。
目錄
總序
張愛玲的啟示
張愛玲筆下的日常生活和「現時感」
看張愛玲的《對照記》
張愛玲:淪陷都市的傳奇
不了情:張愛玲和電影
香港:張愛玲筆下的「她者」
從《溫柔的陷阱》到《情場如戰場》
蒼涼的啟示
剎那懷想重拾經典
張愛玲與好萊塢電影
睇《色,戒》
《色,戒》的回響(代序)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走出張愛玲的陰影
李安對張愛玲的挑戰
《色,戒》的歷史聯想
附錄一 Lust,Caution:Vision and Revision
附錄二 真假的界線(郭詩詠)
張愛玲的啟示
張愛玲筆下的日常生活和「現時感」
看張愛玲的《對照記》
張愛玲:淪陷都市的傳奇
不了情:張愛玲和電影
香港:張愛玲筆下的「她者」
從《溫柔的陷阱》到《情場如戰場》
蒼涼的啟示
剎那懷想重拾經典
張愛玲與好萊塢電影
睇《色,戒》
《色,戒》的回響(代序)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走出張愛玲的陰影
李安對張愛玲的挑戰
《色,戒》的歷史聯想
附錄一 Lust,Caution:Vision and Revision
附錄二 真假的界線(郭詩詠)
序
我的寫作生活不算長,至少比學術生活短得多。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學,在環境影響下用英文寫學術論文,不覺已有半個世紀,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寫作。所以我一直認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習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稱為「學者散文」,但沒有解釋,顧名思義,似乎指的是作為一個學者寫下來的隨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來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稱之為「essay」,法文叫作「essa1」(有嘗試之意),這兩個傳統不盡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強稱之為「雜文」,但又缺乏魯迅式的匕首投槍的作風。我從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評世界或人物——這一點「魯迅風」我完全沒有學到,雖然自己確曾研究過魯迅。也許,對我而言,「生活」這個人文文本太豐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靈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時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寶山。我每讀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論中西,都覺得如在山下掘寶,越挖越興奮,越發感到高山仰止,靈光燦爛。個人最中意的小文都與這類讀書報告有關,如《狐狸洞書話況生活加讀書,人生的意義足夠了。
現在我的好友季進和黃育海、陳子善策划將這些中文作品和中譯的學術著作,匯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為送給我的七十歲生日禮物,我卻之不恭,只好笑納。這個作品系列不代表什麼寫作成績,只是一種生活和讀書的感受與潛思的記錄。這麼多年積少成多,竟然有將近二十卷之多,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
除了某種紀念意義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義:這些參差不齊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現在讀者面前,成為一個文本的「整體」,有點太「重」了,似乎當年的「狐狸」變成一個大「刺蝟」。然而,我曾屢次提過,自己的文章絕對成不了系統,因為我的興趣太廣,在人文領域幾乎無所不包,也從來沒有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豈能成為刺蝟式的思想大師?我愧不敢當,只能說,這個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種積累,猶如重新發行的一套唱碟,希望價廉物美,消費者喜歡就好。
這個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趨多元的興趣。回顧起來,嘈雜之中也自有脈絡可尋,總而言之,可以用文學、歷史、音樂、藝術、電影和建築這幾項人文科目來概括。我學的是歷史和文學,但興趣遍及其他各項,加起來看,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文主義者。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現代性?文化的各種吊詭層面。我的時間范疇是近現代——特別是二十世紀,我游移的文化空間也遍及東西方。不知何故,近年來反而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學和文化興趣日增。別人可以在文化上落葉歸根,我卻不自覺地飄零四海,其樂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認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甚至把雙語寫作和閱讀作為一種常態。
這個系列中的各書出版次序可能不會以寫作先后為序,因此我必須略作交待。如果把學術著作和雜文寫作放在一起,很明顯地可以歸納出一個輪廊:我是先從「五四」時期的浪漫精神出發,逐漸向不同的文化時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從「五四」走向一九三○年代,而魯迅研究則成為一個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覺對上海的都市文化產生興趣,甚至為了擺脫魯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歡的東西——十里洋場的摩登上海。我萬萬沒有想到,當年的一股「反動」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為上海懷舊浪潮的標志之一,這更激發了我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稱為「學者散文」,但沒有解釋,顧名思義,似乎指的是作為一個學者寫下來的隨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來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稱之為「essay」,法文叫作「essa1」(有嘗試之意),這兩個傳統不盡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強稱之為「雜文」,但又缺乏魯迅式的匕首投槍的作風。我從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評世界或人物——這一點「魯迅風」我完全沒有學到,雖然自己確曾研究過魯迅。也許,對我而言,「生活」這個人文文本太豐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靈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時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寶山。我每讀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論中西,都覺得如在山下掘寶,越挖越興奮,越發感到高山仰止,靈光燦爛。個人最中意的小文都與這類讀書報告有關,如《狐狸洞書話況生活加讀書,人生的意義足夠了。
現在我的好友季進和黃育海、陳子善策划將這些中文作品和中譯的學術著作,匯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為送給我的七十歲生日禮物,我卻之不恭,只好笑納。這個作品系列不代表什麼寫作成績,只是一種生活和讀書的感受與潛思的記錄。這麼多年積少成多,竟然有將近二十卷之多,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
除了某種紀念意義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義:這些參差不齊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現在讀者面前,成為一個文本的「整體」,有點太「重」了,似乎當年的「狐狸」變成一個大「刺蝟」。然而,我曾屢次提過,自己的文章絕對成不了系統,因為我的興趣太廣,在人文領域幾乎無所不包,也從來沒有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豈能成為刺蝟式的思想大師?我愧不敢當,只能說,這個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種積累,猶如重新發行的一套唱碟,希望價廉物美,消費者喜歡就好。
這個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趨多元的興趣。回顧起來,嘈雜之中也自有脈絡可尋,總而言之,可以用文學、歷史、音樂、藝術、電影和建築這幾項人文科目來概括。我學的是歷史和文學,但興趣遍及其他各項,加起來看,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文主義者。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現代性?文化的各種吊詭層面。我的時間范疇是近現代——特別是二十世紀,我游移的文化空間也遍及東西方。不知何故,近年來反而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學和文化興趣日增。別人可以在文化上落葉歸根,我卻不自覺地飄零四海,其樂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認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甚至把雙語寫作和閱讀作為一種常態。
這個系列中的各書出版次序可能不會以寫作先后為序,因此我必須略作交待。如果把學術著作和雜文寫作放在一起,很明顯地可以歸納出一個輪廊:我是先從「五四」時期的浪漫精神出發,逐漸向不同的文化時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從「五四」走向一九三○年代,而魯迅研究則成為一個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覺對上海的都市文化產生興趣,甚至為了擺脫魯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歡的東西——十里洋場的摩登上海。我萬萬沒有想到,當年的一股「反動」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為上海懷舊浪潮的標志之一,這更激發了我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