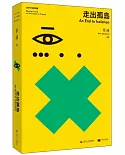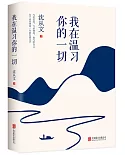這是散文家諸榮會創作的一部關於江南系列文化散文作品集,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不僅以一種獨特的審美眼光和審美情趣,對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進行了新的文化意義的開掘,而且還以此為出發點仰觀俯察,將古往今來這些雖屬於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坐標中進行了一番新的文化定位和現實觀照。
榮會先生圍繞着江南文化這一母題,選取豐富的素材和個人獨特的視角,整合、提煉、升華了歷史故實,用以表述飛揚的意緒、審美的情思。人文精神是這部作品的靈魂,是隨處可觸可感的內在生命。應該說,用這種文筆來描繪源遠流長、意蘊深厚、獨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圖譜,是十分恰當的。可以預期,它帶給廣大讀者的會是一種厚重感、鮮活感、愉悅感。
目錄
關於江南(代自序)
穿越時空的輝煌
姊妹命不同
悲壯的逃離
江南名山詩占盡
乾坤一壺
兩個周邦彥
江南的傳說與傳說的江南
從零丁洋到金陵驛
詩余江南
飄散的笛聲
大都市中的幾個小地方
貢院的那些事兒
尋夢午夢堂
皇恩浩盪下江南
一聲嘆息
深入東王府
文房四寶
月夜永罩的城市
徐志摩的1921
在潭渡看見一道彩虹
他從山中來
后記
穿越時空的輝煌
姊妹命不同
悲壯的逃離
江南名山詩占盡
乾坤一壺
兩個周邦彥
江南的傳說與傳說的江南
從零丁洋到金陵驛
詩余江南
飄散的笛聲
大都市中的幾個小地方
貢院的那些事兒
尋夢午夢堂
皇恩浩盪下江南
一聲嘆息
深入東王府
文房四寶
月夜永罩的城市
徐志摩的1921
在潭渡看見一道彩虹
他從山中來
后記
序
文友諸榮會先生與我為忘年交,盡管彼此至今尚無一面之雅,但繆斯女神已經把兩人牽到了一起,相知相重,還是很投緣的。他的散文新作《IA,景舊曾諳》即將付梓,囑余作序;雖然自認並非理想的人選,但「卻之卻之為不恭也」。
序言,作為批評的一種形式,向來是難於撰寫的。前人講,應該「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換言之,就是既能體會,又能超脫。能「入內」、能體會,方能身在局中,各知甘苦;能「出外」,能超脫,始可思路開闊,公允客觀。作序的理想境界是能夠慧眼識珠,善於發現與挖掘作品中的蘊涵,富有創造性與想象力。像米歇爾·福柯所說的:「它不應該是穿紅袍的君主」,而是能夠「迸發出想象的火花」,「給一部作品、一本書帶來生命」。這個要求實在是太高了,也許只有他那樣當代思想界的巨擘才能做到。我們還是「卑之無甚高論」,立足實際,按照中國古籍中「序者,緒也,謂端緒也」的詮釋,從書稿中理出一點頭緒,先於讀者陳述一些個人見解,力求能起到一點引導作用;如果再進一步,能夠跳出文本,從文化的維度上就一兩個話題談一談,就大致可以了吧。
白傅為詩,淚花滿頰,為其心系民生疾苦者多;而《憶江南》詞牌下的幾首小詞,無論是「花紅似火」、「水碧於藍」,還是「月中尋桂」、「枕上觀潮」,則主要着眼於眼前風景。當然,按照泰特羅教授的說法,「自然行跡」、「自然景觀」,也是一種閱讀對象,同樣也是一種「人文話語」。而榮會眼中「舊曾諳」的「風景」,卻並非、或者說主要不是自然景色,而是人文風景線,縱令有花有月,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其間蘊涵着詩性、史眼、哲思。「詩性」也者,指其行文空靈、飄灑,有些像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雨中春樹萬人家」;而文筆委婉纏綿,旁行斜出,別有一番情致。「史眼」寓於故實、人物的辨析與品鑒之中,寫到歷史人物時並不滯留於流行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道德層面的評判,而是把他們還原成一個現實、復雜的、多側面存在的人,將視點聚焦在他們現實生存背景下心理發展的邏輯上。讀者可以從中體驗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認識自我,獲取一種新的感悟。「哲思」在這里體現為一種深度追求。歷史是通過發現而存在的。通過展現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識、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環境中獲得的生存狀態、生命體驗,達到對人性、人生、社會、歷史的深度思考。
當然,這是就創作特色而言;而詩思史結合的完美實現,絕非易事。我們一般的寫作者,只能作為一個心儀的目標,奮力地加以實踐。有一點,我認為至關重要,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所提出的,作為一個作家應該掌握「第二視力」,憑借「第二視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對象——題材」,閃現出審美的絢爛。他說,與「第一視力」(天然眼睛)不同,「第二視力」是有別於他人的作家自己獨具的眼光——視力。這「第二視力」可稱為「文化的眼睛」——ˉ「文化視力」。在中國,有個傳統的說法,叫做「獨具只眼,別有會心」。
通讀這部散文集,包括作家另外那本《風生白下》,我覺得榮會先生具有比較明顯的「文體意識」和「工程意識」。論者以為,他的這些散文「在解讀歷史的同時,着意揭示作者對於具體生命形態的超越性理解,其意旨不是簡單地從一堆史料中再現過去,而是從對過去的追憶、闡釋中揭示它對現實的影響和歷史的內在意義。作者不僅以一種獨特的審美眼光和審美情趣,對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進行了新的文化意義的開掘,而且還以此為出發點,仰觀俯察,將古往今來這些雖屬於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坐標中,進行一番新的文化定位和現實觀照」。其「筆墨縱橫而又不失細致,詩意澇沛而又不失犀利」。這些,都表述了他的比較鮮明的文體風格。
……
序言,作為批評的一種形式,向來是難於撰寫的。前人講,應該「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換言之,就是既能體會,又能超脫。能「入內」、能體會,方能身在局中,各知甘苦;能「出外」,能超脫,始可思路開闊,公允客觀。作序的理想境界是能夠慧眼識珠,善於發現與挖掘作品中的蘊涵,富有創造性與想象力。像米歇爾·福柯所說的:「它不應該是穿紅袍的君主」,而是能夠「迸發出想象的火花」,「給一部作品、一本書帶來生命」。這個要求實在是太高了,也許只有他那樣當代思想界的巨擘才能做到。我們還是「卑之無甚高論」,立足實際,按照中國古籍中「序者,緒也,謂端緒也」的詮釋,從書稿中理出一點頭緒,先於讀者陳述一些個人見解,力求能起到一點引導作用;如果再進一步,能夠跳出文本,從文化的維度上就一兩個話題談一談,就大致可以了吧。
白傅為詩,淚花滿頰,為其心系民生疾苦者多;而《憶江南》詞牌下的幾首小詞,無論是「花紅似火」、「水碧於藍」,還是「月中尋桂」、「枕上觀潮」,則主要着眼於眼前風景。當然,按照泰特羅教授的說法,「自然行跡」、「自然景觀」,也是一種閱讀對象,同樣也是一種「人文話語」。而榮會眼中「舊曾諳」的「風景」,卻並非、或者說主要不是自然景色,而是人文風景線,縱令有花有月,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其間蘊涵着詩性、史眼、哲思。「詩性」也者,指其行文空靈、飄灑,有些像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雨中春樹萬人家」;而文筆委婉纏綿,旁行斜出,別有一番情致。「史眼」寓於故實、人物的辨析與品鑒之中,寫到歷史人物時並不滯留於流行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道德層面的評判,而是把他們還原成一個現實、復雜的、多側面存在的人,將視點聚焦在他們現實生存背景下心理發展的邏輯上。讀者可以從中體驗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認識自我,獲取一種新的感悟。「哲思」在這里體現為一種深度追求。歷史是通過發現而存在的。通過展現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識、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環境中獲得的生存狀態、生命體驗,達到對人性、人生、社會、歷史的深度思考。
當然,這是就創作特色而言;而詩思史結合的完美實現,絕非易事。我們一般的寫作者,只能作為一個心儀的目標,奮力地加以實踐。有一點,我認為至關重要,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所提出的,作為一個作家應該掌握「第二視力」,憑借「第二視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對象——題材」,閃現出審美的絢爛。他說,與「第一視力」(天然眼睛)不同,「第二視力」是有別於他人的作家自己獨具的眼光——視力。這「第二視力」可稱為「文化的眼睛」——ˉ「文化視力」。在中國,有個傳統的說法,叫做「獨具只眼,別有會心」。
通讀這部散文集,包括作家另外那本《風生白下》,我覺得榮會先生具有比較明顯的「文體意識」和「工程意識」。論者以為,他的這些散文「在解讀歷史的同時,着意揭示作者對於具體生命形態的超越性理解,其意旨不是簡單地從一堆史料中再現過去,而是從對過去的追憶、闡釋中揭示它對現實的影響和歷史的內在意義。作者不僅以一種獨特的審美眼光和審美情趣,對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進行了新的文化意義的開掘,而且還以此為出發點,仰觀俯察,將古往今來這些雖屬於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坐標中,進行一番新的文化定位和現實觀照」。其「筆墨縱橫而又不失細致,詩意澇沛而又不失犀利」。這些,都表述了他的比較鮮明的文體風格。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