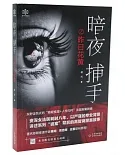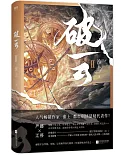★當代中國版「變貌記」
用荒誕藝術手法描寫知識分子生活
鮮明的時代烙印 大膽的藝術實驗
迄今為止,莫言和他的作品已經獲得了海內外眾多獎項,主要有:1987年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1988年台灣地區「聯合文學獎」;1996年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2001年第二屆「馮牧文學獎·軍旅文學創作獎」;2001年法國「Laure
Batailli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2002年首屆「鼎鈞文學獎」,「『茅台懷』人民文學獎」,法國「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第十三屆意大利「NONI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日本第十七屆「福岡亞洲文化獎」;2007年「『福星惠譽杯』《十月》優秀作品獎」;2008年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等。
《十三步》是莫言在1988年運用荒誕藝術手法描寫知識分子和現實生活的一部力作。中學物理教師方富貴累死後,由於得給王副市長讓路整容,被塞冰冰櫃,居然又荒誕離奇地復活了。但以為他已死的妻子屠小英卻拒絕他再進家門。殯儀館特級美容師李玉蟬把死而復活的方富貴改容成自己的丈夫張赤球,讓他代替自己的合法丈夫登講台給學生上課,而讓真正的張赤球去做生意賺錢。真正的張赤球則像一個孤魂野鬼,變得無家可歸——現實生活中原有的秩序已不復存在。此次出版的是全新修訂版。
序
大約是兩年前,《長篇小說選刊》創刊,讓我寫幾句話,推辭不過,斗膽寫道:「長度、密度和難度,是長篇小說的標忘,也是這偉大文體的尊嚴。」
所謂長度,自然是指小說的篇幅。沒有二十萬字以上的篇幅,長篇小說就缺少應有的威嚴。就像金錢豹子,雖然也勇猛,雖然也剽悍,但終因體形稍遜,難成山中之王。我當然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其力量和價值都勝過某些臃腫的長篇,我當然也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已經成為經典,但那種猶如長江大河般的波瀾壯闊之美,卻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備的。長篇就是要長,不長算什麽長篇?要把長篇寫長,當然很不容易。我們慣常聽到的是把長篇寫短的呼吁,我卻在這里呼吁:長篇就是要往長里寫!當然,把長篇寫長,並不是事件和宇數的累加,而是一種胸中的大氣象,一種藝術的大營造。那些能夠營造精致的江南園林的建築師,那些在假山上蓋小亭子的建築師,當然也很了不起,但他們大概營造不來故官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萬里長城那樣的浩大工程。這如同戰爭中,有的人,指揮一個團,可能非常出色,但給他一個軍,一個兵團,就亂了陣腳。將才就是將才,帥才就是帥才,而帥才大都不是從行伍中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當然,不能簡單地把寫長篇小說的稱作帥才,更不敢把寫短篇小說的貶為將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請原諒。
一個善寫長篇小說的作家,並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長的道路,盡管許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這樣的道路。許多偉大的長篇小說作者,一開始上手就是長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羅貫中等。我認為一個作家能夠寫出開且能夠寫好長篇小說,關鍵的是要具有「長篇胸懷」。「長篇胸懷」者,胸中有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之謂也。要有粗糲莽盪之氣,要有容納百川之涵。所謂大家手筆,正是胸中之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的外在表現也。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天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大感悟——這些都是「長篇胸懷」之內涵也。
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開來說,我只想就「大悲憫」多說幾句。近幾年來,「悲憫情懷」已成時髦話語,就像前幾年「終極關懷」成為時髦話語一樣。我自然也知道悲憫是好東西,但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剛吃完紅燒乳鶴,又趕緊給一只翅膀受傷的鴿子包扎的悲憫;不是蘇聯戰爭片中和好萊塢大片中那種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憫;不是那種全社會為一只生病的熊貓獻愛心、但置元數因為元錢而在家等死的人於不顧的悲憫。悲憫不僅僅是「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讓你打」,悲憫也不僅僅是在苦難中保持善心和優雅姿態,悲憫不是見到血就暈過去或者是高喊著「我要暈過去了」,悲憫更不是要回避罪惡和骯臟。《聖經》是悲憫的經典,但那里邊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場面。佛教是大悲憫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獄和令人發指的酷刑。如果悲憫是把人類的邪惡和且陋掩蓋起來,那這樣的悲憫和偽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負惡名,但有見地的批評家卻說那是一部悲憫之書。這才是中岳式的悲憫,這才是建立在中國的哲學、宗教基礎上的悲憫,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學和西方宗教基礎上的悲憫。長篇小說是包羅萬象的龐大文體,這里邊有羊羔也有小鳥,有獅子也有鱷魚。你不能因為獅子吃了羊羔或者鱷魚吞了小鳥就說它們不悲恫.你不能因為它們捕殺獵物時展現了高度技巧、獲得獵物時喜氣洋洋就說它們殘忍。只有羊羔和小烏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說不是小說。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鳥,也要吃昆蟲;即便是好人,也有惡念頭.站在高一點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壞人,都是可憐的人。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
┅┅
所謂長度,自然是指小說的篇幅。沒有二十萬字以上的篇幅,長篇小說就缺少應有的威嚴。就像金錢豹子,雖然也勇猛,雖然也剽悍,但終因體形稍遜,難成山中之王。我當然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其力量和價值都勝過某些臃腫的長篇,我當然也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已經成為經典,但那種猶如長江大河般的波瀾壯闊之美,卻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備的。長篇就是要長,不長算什麽長篇?要把長篇寫長,當然很不容易。我們慣常聽到的是把長篇寫短的呼吁,我卻在這里呼吁:長篇就是要往長里寫!當然,把長篇寫長,並不是事件和宇數的累加,而是一種胸中的大氣象,一種藝術的大營造。那些能夠營造精致的江南園林的建築師,那些在假山上蓋小亭子的建築師,當然也很了不起,但他們大概營造不來故官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萬里長城那樣的浩大工程。這如同戰爭中,有的人,指揮一個團,可能非常出色,但給他一個軍,一個兵團,就亂了陣腳。將才就是將才,帥才就是帥才,而帥才大都不是從行伍中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當然,不能簡單地把寫長篇小說的稱作帥才,更不敢把寫短篇小說的貶為將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請原諒。
一個善寫長篇小說的作家,並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長的道路,盡管許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這樣的道路。許多偉大的長篇小說作者,一開始上手就是長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羅貫中等。我認為一個作家能夠寫出開且能夠寫好長篇小說,關鍵的是要具有「長篇胸懷」。「長篇胸懷」者,胸中有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之謂也。要有粗糲莽盪之氣,要有容納百川之涵。所謂大家手筆,正是胸中之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的外在表現也。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天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大感悟——這些都是「長篇胸懷」之內涵也。
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開來說,我只想就「大悲憫」多說幾句。近幾年來,「悲憫情懷」已成時髦話語,就像前幾年「終極關懷」成為時髦話語一樣。我自然也知道悲憫是好東西,但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剛吃完紅燒乳鶴,又趕緊給一只翅膀受傷的鴿子包扎的悲憫;不是蘇聯戰爭片中和好萊塢大片中那種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憫;不是那種全社會為一只生病的熊貓獻愛心、但置元數因為元錢而在家等死的人於不顧的悲憫。悲憫不僅僅是「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讓你打」,悲憫也不僅僅是在苦難中保持善心和優雅姿態,悲憫不是見到血就暈過去或者是高喊著「我要暈過去了」,悲憫更不是要回避罪惡和骯臟。《聖經》是悲憫的經典,但那里邊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場面。佛教是大悲憫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獄和令人發指的酷刑。如果悲憫是把人類的邪惡和且陋掩蓋起來,那這樣的悲憫和偽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負惡名,但有見地的批評家卻說那是一部悲憫之書。這才是中岳式的悲憫,這才是建立在中國的哲學、宗教基礎上的悲憫,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學和西方宗教基礎上的悲憫。長篇小說是包羅萬象的龐大文體,這里邊有羊羔也有小鳥,有獅子也有鱷魚。你不能因為獅子吃了羊羔或者鱷魚吞了小鳥就說它們不悲恫.你不能因為它們捕殺獵物時展現了高度技巧、獲得獵物時喜氣洋洋就說它們殘忍。只有羊羔和小烏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說不是小說。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鳥,也要吃昆蟲;即便是好人,也有惡念頭.站在高一點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壞人,都是可憐的人。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