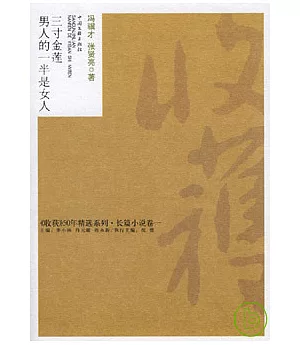《三寸金蓮》中的一種意圖,即用大量充分的歷史細節——實物照片,復原那曾經活着的奇異的歷史,再現三寸金蓮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給這中國文化中最隱秘、最閉鎖、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曝光。
歷史的幽靈總是躲在某種遮蔽之下不肯離去,暗暗作崇;所以,當歷史的一幕過去,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開。
序
《收獲》文學雜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個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門口有一間收發室,這間收發室,很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間收發室,沒有一個收發室像它這樣深刻地介人中國文學的歷史,尤其在網絡時代以前,許多對當世以及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就是混跡於堆積如山的郵件中,從這里輾轉到編輯部,等待編輯們的辨識。很多年中,從郵局、收發室、到編輯部、印刷廠,再回到郵局,組成了—條隱秘的循環線路,像鏈條,周而復始地轉動,使文學同時獲得了力量和速度,經過它的轉動,中國文學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處。在文學界和讀者心中,巨鹿路615號那座花木深處的西式洋樓,不僅是一家高品質的文學加工廠,更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聖地。
《收獲》的歷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作家們的回憶錄、創作談,甚至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中。進人中國當代文學史可能有許多條路徑,但每一條路徑最終都會抵達這里。它是中國文學地圖上一個最為顯著的地標,如果我們有起碼的公正,我們就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這不僅是因為它擁有非凡的資歷——早在1951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創辦了這份雜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國唯一的大型純文學期刊,它發表的作品,諸如《創業史》 (柳青)、 《茶館》 (老舍)、 《山鄉巨變》 (周立波)、 《野火春風斗古城》 (李英儒)、 《上海的早晨》 (周而復)、 《雜色》 (王蒙)、 《美食家》 (陸文夫)、 《煙壺》(鄧友梅)、 《人生》 (路遙)、 《人到中年》 (諶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 《三寸金蓮》 (馮驥才)、 《我愛比爾》 (王安憶)、《麥秸垛》 (鐵凝)、 《虛構》 (馬原)、 《極地之側》 (洪峰)、 《活著》(余華)、 《妻妾成群》 (蘇童)、 《信使之函》 (孫甘露)、 《頑主》 (王朔)、 《迷舟》 (格非)、 《棗樹的故事》 (葉兆言)、 《年月日》 (閻連科)、 《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 (池莉)、 《奔跑的火光》 (方方), 《東藏記》 (宗璞)、 《務虛筆記》 (史鐵生)、 《秦腔》 (賈平凹)、 《平原》(畢飛宇)、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等,無不代表著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作品,更是標准、原則、精神,它們通過那條永動機一般的隱形鏈條,得以確認、延續和發展。無論在言說空間受到貶抑,還是在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 《收獲》始終如一地傳布著文學的真理,把《收獲》視為一面旗幟,應不為過。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事實,文學家也不例外,欲望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唯一靈魂或靈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強大壓力下,文學開始變得手足無措、內分泌失調,唯有《收獲》的高貴、堅定和沉著沒有絲毫改變,它證明了文學在這個益發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嚴地生活。這是中國文學應有的氣質,但在這個時代里,它卻成為一個奇跡。
這使我們有必要認真打量這本雜志的歷史。我曾有過以這本雜志為研究對象寫一本專著的願望,試圖通過《收獲》的個案,剖析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和精神史,但因時間、精力所限,始終未能如願。編選這套叢書的動議,起於2007年, 《收獲》創刊50周年的時候。對那些曾經影響過我們的作品進行分梳、整理、編選,我們看到的絕不僅僅是雜志本身,所有經歷過的歲月都會附著在紙頁上呼嘯而來,它是一部回憶之書,一部史書,它見證了文學的傳奇和我們自身的奇跡,它同時也是一部未來之書,因為它給我們希望。這喚起了我這位出版人的職業沖動,一種無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開始主持這套叢書的編選工作。我們通讀了《收獲》50余年的全部作品,盡可能選擇那些既影響過時代,又不受時代的局限,具有某種超越性的作品,這是我們權衡棄取的重要標准。當然,由於篇幅的限制,或者由於版權方面的原因,有些我們很想收選的作品,最後不得不割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無論怎樣,在歷經兩年反反復復的出版過程之後,這套叢書終於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為此,我要感謝《收獲》文學雜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與合作,當然也要感謝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經試圖去掉「50年」這一時間界定,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我已不再把它視為一個具體的數字,而是一種象征,是對中國文學半個多世紀的艱辛而漫長的旅程作出的精確概括
如果用物質主義者最擅長的比喻,我想,我是觸及了中國文學的銀行中一筆最珍貴的款項。我毫不懷疑,它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救助我們。
《收獲》的歷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作家們的回憶錄、創作談,甚至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中。進人中國當代文學史可能有許多條路徑,但每一條路徑最終都會抵達這里。它是中國文學地圖上一個最為顯著的地標,如果我們有起碼的公正,我們就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這不僅是因為它擁有非凡的資歷——早在1951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創辦了這份雜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國唯一的大型純文學期刊,它發表的作品,諸如《創業史》 (柳青)、 《茶館》 (老舍)、 《山鄉巨變》 (周立波)、 《野火春風斗古城》 (李英儒)、 《上海的早晨》 (周而復)、 《雜色》 (王蒙)、 《美食家》 (陸文夫)、 《煙壺》(鄧友梅)、 《人生》 (路遙)、 《人到中年》 (諶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 《三寸金蓮》 (馮驥才)、 《我愛比爾》 (王安憶)、《麥秸垛》 (鐵凝)、 《虛構》 (馬原)、 《極地之側》 (洪峰)、 《活著》(余華)、 《妻妾成群》 (蘇童)、 《信使之函》 (孫甘露)、 《頑主》 (王朔)、 《迷舟》 (格非)、 《棗樹的故事》 (葉兆言)、 《年月日》 (閻連科)、 《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 (池莉)、 《奔跑的火光》 (方方), 《東藏記》 (宗璞)、 《務虛筆記》 (史鐵生)、 《秦腔》 (賈平凹)、 《平原》(畢飛宇)、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等,無不代表著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作品,更是標准、原則、精神,它們通過那條永動機一般的隱形鏈條,得以確認、延續和發展。無論在言說空間受到貶抑,還是在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 《收獲》始終如一地傳布著文學的真理,把《收獲》視為一面旗幟,應不為過。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事實,文學家也不例外,欲望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唯一靈魂或靈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強大壓力下,文學開始變得手足無措、內分泌失調,唯有《收獲》的高貴、堅定和沉著沒有絲毫改變,它證明了文學在這個益發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嚴地生活。這是中國文學應有的氣質,但在這個時代里,它卻成為一個奇跡。
這使我們有必要認真打量這本雜志的歷史。我曾有過以這本雜志為研究對象寫一本專著的願望,試圖通過《收獲》的個案,剖析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和精神史,但因時間、精力所限,始終未能如願。編選這套叢書的動議,起於2007年, 《收獲》創刊50周年的時候。對那些曾經影響過我們的作品進行分梳、整理、編選,我們看到的絕不僅僅是雜志本身,所有經歷過的歲月都會附著在紙頁上呼嘯而來,它是一部回憶之書,一部史書,它見證了文學的傳奇和我們自身的奇跡,它同時也是一部未來之書,因為它給我們希望。這喚起了我這位出版人的職業沖動,一種無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開始主持這套叢書的編選工作。我們通讀了《收獲》50余年的全部作品,盡可能選擇那些既影響過時代,又不受時代的局限,具有某種超越性的作品,這是我們權衡棄取的重要標准。當然,由於篇幅的限制,或者由於版權方面的原因,有些我們很想收選的作品,最後不得不割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無論怎樣,在歷經兩年反反復復的出版過程之後,這套叢書終於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為此,我要感謝《收獲》文學雜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與合作,當然也要感謝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經試圖去掉「50年」這一時間界定,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我已不再把它視為一個具體的數字,而是一種象征,是對中國文學半個多世紀的艱辛而漫長的旅程作出的精確概括
如果用物質主義者最擅長的比喻,我想,我是觸及了中國文學的銀行中一筆最珍貴的款項。我毫不懷疑,它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救助我們。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