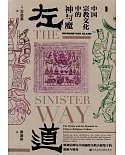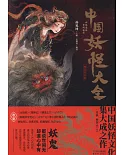本文集共收錄論文46篇,分為八個專題。論文內容廣泛,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都有新的開掘和拓展,集中反映了近些年我國伊斯蘭文化研究的前沿性成果。
在46篇論文中,西北民族大學作者論文有30篇,加上西北民族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及學術顧問的論文,則共計39篇,因此基本上比較充分地展現了西北民族大學在伊斯蘭文化研究領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及其整體水平。
作者隊伍除一些仍然耕耘在科研一線的老專家外,基本上以中青年學者為主,預示著伊斯蘭文化研究隊伍的成長和壯大。
作者單位除西北民族大學外,尚有北京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蘭州大學、寧夏大學、雲南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寧夏社會科學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來我國在伊斯蘭文化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和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錄
前言
導論 面向新世紀,創建伊斯蘭文化研究的新體系
伊斯蘭文化與文明對話
文明對話與大中東改革
伊斯蘭視閾中的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認同及其重構
“以儒詮經”活動及其對當代文明對話的啟示意義
王岱輿的“天命三品”論對當今文明對話的啟迪意義
穆斯林的人生理想
——兼與儒家文明的對話
從《據理質證》看馬德新的“回耶”對話觀
伊斯蘭哲學思想研究
伊斯蘭文明中的人文思想
當代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述評
再論伊斯蘭教的和平觀
——兼及“吉哈德”理念
伊斯蘭研究中的詞匯問題
——以“吉哈德”為例
伊斯蘭人權觀
烏瑪觀念與伊斯蘭宗教共同體的構建
納斯爾教授的“聖道伊斯蘭教”觀初探
納斯爾教授的伊斯蘭哲學史觀述評
淺談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存在神學”觀
從努爾西到努爾庫運動
——土耳其“文化伊斯蘭”概說
文化比較研究
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主權觀之比較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當代價值
伊斯蘭法文化與中國法文化的比較研究
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視閾中耶穌形象之比較研究
從“真一說”看明清之際的回儒融合
儒家“五倫”思想和劉智“五典”思想之比較
伊斯蘭文化與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符號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根本利益
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和諧理念
和諧社會中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
伊斯蘭婦女問題文化辨析
伊斯蘭生態文明初探
穆斯林生理衛生與心理衛生觀念初探
伊斯蘭文化與中國穆斯林
對王岱輿、劉智學術地位的再認識
——致杜維明先生的信
他山之石
——西方學界對中國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述評
伊斯蘭教傳入西藏考
西海固伊斯蘭教的門宦教權體制
論法門門宦兩份阿拉伯文蘇菲傳教憑證的文獻價值及信息
陝鄂交界地區回族、伊斯蘭教考述
維吾爾族jamaat群體研究
《福樂智慧》中所反映的早期蘇菲
雲南迪慶藏化回族調查報告
伊斯蘭教法研究
論教法創制與文化創新
論伊斯蘭教與“神聖律法”伊斯蘭法的辯證統一
伊斯蘭法淵源在其文化體系形成中的作用
伊斯蘭教育
歷史上的伊斯蘭教育
20世紀河州經常教育的兩次重大突破
蘭州滿拉的漢文化需求
——以城關區為例
伊斯蘭文獻研究
《古蘭經》注疏概觀
穆聖與《古蘭經》注疏
聖訓花苑中的智慧花瓣
導論 面向新世紀,創建伊斯蘭文化研究的新體系
伊斯蘭文化與文明對話
文明對話與大中東改革
伊斯蘭視閾中的文明對話與全球倫理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認同及其重構
“以儒詮經”活動及其對當代文明對話的啟示意義
王岱輿的“天命三品”論對當今文明對話的啟迪意義
穆斯林的人生理想
——兼與儒家文明的對話
從《據理質證》看馬德新的“回耶”對話觀
伊斯蘭哲學思想研究
伊斯蘭文明中的人文思想
當代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述評
再論伊斯蘭教的和平觀
——兼及“吉哈德”理念
伊斯蘭研究中的詞匯問題
——以“吉哈德”為例
伊斯蘭人權觀
烏瑪觀念與伊斯蘭宗教共同體的構建
納斯爾教授的“聖道伊斯蘭教”觀初探
納斯爾教授的伊斯蘭哲學史觀述評
淺談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存在神學”觀
從努爾西到努爾庫運動
——土耳其“文化伊斯蘭”概說
文化比較研究
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主權觀之比較
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當代價值
伊斯蘭法文化與中國法文化的比較研究
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視閾中耶穌形象之比較研究
從“真一說”看明清之際的回儒融合
儒家“五倫”思想和劉智“五典”思想之比較
伊斯蘭文化與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符號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根本利益
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和諧理念
和諧社會中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
伊斯蘭婦女問題文化辨析
伊斯蘭生態文明初探
穆斯林生理衛生與心理衛生觀念初探
伊斯蘭文化與中國穆斯林
對王岱輿、劉智學術地位的再認識
——致杜維明先生的信
他山之石
——西方學界對中國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述評
伊斯蘭教傳入西藏考
西海固伊斯蘭教的門宦教權體制
論法門門宦兩份阿拉伯文蘇菲傳教憑證的文獻價值及信息
陝鄂交界地區回族、伊斯蘭教考述
維吾爾族jamaat群體研究
《福樂智慧》中所反映的早期蘇菲
雲南迪慶藏化回族調查報告
伊斯蘭教法研究
論教法創制與文化創新
論伊斯蘭教與“神聖律法”伊斯蘭法的辯證統一
伊斯蘭法淵源在其文化體系形成中的作用
伊斯蘭教育
歷史上的伊斯蘭教育
20世紀河州經常教育的兩次重大突破
蘭州滿拉的漢文化需求
——以城關區為例
伊斯蘭文獻研究
《古蘭經》注疏概觀
穆聖與《古蘭經》注疏
聖訓花苑中的智慧花瓣
序
東方文化大師季羨林先生把伊斯蘭文化列為綿延不斷、傳承至今的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之一,指出︰“紛繁復雜的文化,根據其共同之點,共可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一直到今天歐美的文化體系。”伊斯蘭文化不僅在人類文化史上曾起到過溝通東西、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獨特作用,而且也是一種具有重大現實影響力的世界性文化。目前,全球有五十多個伊斯蘭國家,十幾億穆斯林,佔人類總人口的五分之一;特別是中東伊斯蘭國家所擁有的重要地緣戰略地位和影響世界經濟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使該地區成為舉世矚目的全球熱點地區,與此相關的伊斯蘭文化研究也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一門顯學。在國內有回、東鄉、撒拉、保安、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10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他們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區).伊斯蘭文化是這些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伊斯蘭文化研究不但具有學術價值.而且還有現實意義,這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伊斯蘭文化在人類文化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和現實影響力,因而受到國內外學界乃至政界的關注。目前,全世界伊斯蘭文化的主要研究力量大致可分為三大塊︰伊斯蘭國家本土學者、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對伊斯蘭國家本土學者而言,研究伊斯蘭文化,猶如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一樣,是其“國學”的一部分,輕車熟路,碩果累累,其特點是佔有第一手資料,原汁原味,只是對研究資料尚需分析、提煉、升華;西方學者依托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手段,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的龐大的學科體系。然而,西方伊斯蘭文化研究是其“東方學”的一部分,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論”色彩,麗且是為西方國家的全球戰略服務的;中國學者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雖說由來已久,但真正引起主流學術界的關注則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央政府對世界性宗教文化非常重視,我國高校和相關科研院所投入了相當的人力和財力實施伊斯蘭文化研究工程,取得了可貴的成果。只是這些成果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與我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國的國際地位還很不相稱,以翔實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的、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研究成果略顯不足。對此,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約旦皇家伊斯蘭思想研究院院士朱威烈教授也深有同感,他針對這種不均衡的研究狀況指出︰“客觀地看,我國對歐美的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已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但對世界文明史和當今國際舞台上佔據重要地位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卻還知之不多,研究機構和人員的數量、水平都還無法與我國對美、歐、日、俄的研究相提並論。”甚至還不如對印度文化的了解、研究程度。對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而言,印度歷史文化名人從古代的釋迦牟尼到現代的泰戈爾,耳熟能詳,能說出長長的一大串,而一提伊斯蘭世界,人們似乎只知道《天方夜譚》,只知道薩達姆、本‧拉登,而那些曾經對西方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燦若群星的學術大師(如伊本‧西納、伊本‧魯世德、安薩里、伊本‧赫爾東等等)的名字則聞所未聞。
這種嚴重失衡的研究狀況客觀上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我國有些媒體在報道中東和涉及伊斯蘭世界的新聞時,雖不乏真知灼見,但缺少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有時甚至人雲亦雲,直接照搬西方現成的術語和表述方式,無意中充當了西方媒體的傳聲筒,正中了西方有些國家和政客借全球化之名行西方化之實的下懷。一些簡單化的或帶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政治傾向的術語和表述方式充塞著人們的耳目,遮蔽著伊斯蘭世界的多樣性、伊斯蘭文化的豐富性,影響著人們對伊斯蘭文化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極不利于我國與佔聯合國成員國四分之一強的五十多個伊斯蘭國家的正常交往,不利于全面落實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不利于保持和維護我國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不利于展現大國國民的素質和氣度,不利于構築我國的軟實力。
……
由于伊斯蘭文化在人類文化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和現實影響力,因而受到國內外學界乃至政界的關注。目前,全世界伊斯蘭文化的主要研究力量大致可分為三大塊︰伊斯蘭國家本土學者、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對伊斯蘭國家本土學者而言,研究伊斯蘭文化,猶如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一樣,是其“國學”的一部分,輕車熟路,碩果累累,其特點是佔有第一手資料,原汁原味,只是對研究資料尚需分析、提煉、升華;西方學者依托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手段,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的龐大的學科體系。然而,西方伊斯蘭文化研究是其“東方學”的一部分,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論”色彩,麗且是為西方國家的全球戰略服務的;中國學者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雖說由來已久,但真正引起主流學術界的關注則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央政府對世界性宗教文化非常重視,我國高校和相關科研院所投入了相當的人力和財力實施伊斯蘭文化研究工程,取得了可貴的成果。只是這些成果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與我國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國的國際地位還很不相稱,以翔實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的、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研究成果略顯不足。對此,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約旦皇家伊斯蘭思想研究院院士朱威烈教授也深有同感,他針對這種不均衡的研究狀況指出︰“客觀地看,我國對歐美的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已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但對世界文明史和當今國際舞台上佔據重要地位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卻還知之不多,研究機構和人員的數量、水平都還無法與我國對美、歐、日、俄的研究相提並論。”甚至還不如對印度文化的了解、研究程度。對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而言,印度歷史文化名人從古代的釋迦牟尼到現代的泰戈爾,耳熟能詳,能說出長長的一大串,而一提伊斯蘭世界,人們似乎只知道《天方夜譚》,只知道薩達姆、本‧拉登,而那些曾經對西方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燦若群星的學術大師(如伊本‧西納、伊本‧魯世德、安薩里、伊本‧赫爾東等等)的名字則聞所未聞。
這種嚴重失衡的研究狀況客觀上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我國有些媒體在報道中東和涉及伊斯蘭世界的新聞時,雖不乏真知灼見,但缺少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有時甚至人雲亦雲,直接照搬西方現成的術語和表述方式,無意中充當了西方媒體的傳聲筒,正中了西方有些國家和政客借全球化之名行西方化之實的下懷。一些簡單化的或帶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政治傾向的術語和表述方式充塞著人們的耳目,遮蔽著伊斯蘭世界的多樣性、伊斯蘭文化的豐富性,影響著人們對伊斯蘭文化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極不利于我國與佔聯合國成員國四分之一強的五十多個伊斯蘭國家的正常交往,不利于全面落實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不利于保持和維護我國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不利于展現大國國民的素質和氣度,不利于構築我國的軟實力。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