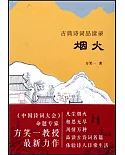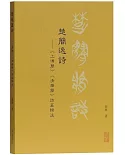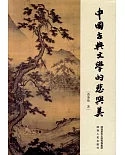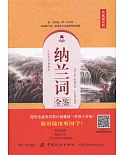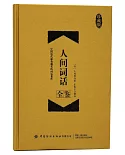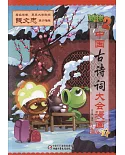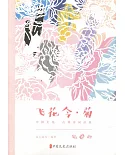作者既身在河南外省文化之中熱愛故鄉、思考故鄉,且能時時超出故鄉文化,做更有眼光的熱辣而心痛的分析。本書抓住了20世紀河南文學發展中的三個不同時期的三種文化、文學現象︰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慧星”現象,1950-1970年代河南文壇的“幾個亮點”,以及世紀末的“中原突破”,並對其背後的思想、文化、文學的底蘊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對20世紀河南文學的一種解 讀。
梁鴻,女,1973年生于河南鄧州。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文藝思潮研究。出版學術訪談著作《巫婆的紅筷子》(2002),曾在《文藝理論與批評》《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等中文核心期刊發表論文50余篇。
目錄
序 河南文化與河南文學
緒論 “外省”視角下的地域文學研究
上篇 史論
第一章 斷裂與悖離︰河南新文學的發生
一 彗星劃過天空
二 文化的斷層
三 悖離與掙扎
四 中庸與激進
第二章 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世紀~年代的河南文學
一 歷史的轉折與河南文學的“亮點”
二 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
三 文學的“虛構”與生活的“真實”
第三章 新時期的“中原突破”
一 新時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二 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
三“中原突破”的意義
四 “中原突破”的缺陷
第四章 全球化語境下的外省文化空間與河南文學
一 全球化與文學的民族性
二 “河南人”現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深層危機
第五章 “外省”的必然與無奈
下篇 作 家 論
第六章 師陀︰“果園城”文化的“變”與“不變”
一 異鄉和故鄉
二 荒原之中的詩意
三 故鄉情感和故鄉意象
第七章 劉震雲︰“平民”立場的兩難與民間生存世界
一 “故鄉”的兩極意義
二 “吵架”美學與“平民立場”的兩難
三 民間的生存特性
四 鬧劇沖動與語言的暴動
五 姥娘去了
第八章 周大新︰沖出“圓形盆地”
一 “圓”與“不圓”
二 “圍獵”與“被圍”
三 “窺視者”的身份質疑與保安之死
四 善惡辯證法
第九章 閻連科︰“耙耬山脈”的隱喻與象征
一 《日光流年》︰“鄉土中國”象征詩學的轉換與超越
二 妥協的方言與沉默的世界
三 慶典、神話、暴力及其他
第十章 李洱︰新的小說詩學的建構
一 百科全書式敘事
二 “共時性”存在結構
三 日常生活詩學空問
附錄 對話︰“中原突破”的陷阱
參考文獻
代後記 故鄉
緒論 “外省”視角下的地域文學研究
上篇 史論
第一章 斷裂與悖離︰河南新文學的發生
一 彗星劃過天空
二 文化的斷層
三 悖離與掙扎
四 中庸與激進
第二章 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世紀~年代的河南文學
一 歷史的轉折與河南文學的“亮點”
二 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
三 文學的“虛構”與生活的“真實”
第三章 新時期的“中原突破”
一 新時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二 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
三“中原突破”的意義
四 “中原突破”的缺陷
第四章 全球化語境下的外省文化空間與河南文學
一 全球化與文學的民族性
二 “河南人”現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深層危機
第五章 “外省”的必然與無奈
下篇 作 家 論
第六章 師陀︰“果園城”文化的“變”與“不變”
一 異鄉和故鄉
二 荒原之中的詩意
三 故鄉情感和故鄉意象
第七章 劉震雲︰“平民”立場的兩難與民間生存世界
一 “故鄉”的兩極意義
二 “吵架”美學與“平民立場”的兩難
三 民間的生存特性
四 鬧劇沖動與語言的暴動
五 姥娘去了
第八章 周大新︰沖出“圓形盆地”
一 “圓”與“不圓”
二 “圍獵”與“被圍”
三 “窺視者”的身份質疑與保安之死
四 善惡辯證法
第九章 閻連科︰“耙耬山脈”的隱喻與象征
一 《日光流年》︰“鄉土中國”象征詩學的轉換與超越
二 妥協的方言與沉默的世界
三 慶典、神話、暴力及其他
第十章 李洱︰新的小說詩學的建構
一 百科全書式敘事
二 “共時性”存在結構
三 日常生活詩學空問
附錄 對話︰“中原突破”的陷阱
參考文獻
代後記 故鄉
序
我原屬山東聊城地區在平縣人(1958年後我所在的琉寺區才劃歸高唐縣),在1949年以前的解放區的區域劃分中,屬于晉(山西)冀(河北)魯(山東)豫(河南)邊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初設省、市建制的時候,我們屬于平原省,是由現在的山東、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共同構成的,省會就是現在河南的新鄉市,殷都的所在地安陽地區也在平原省境內。我父親當時是一個縣級干部,曾經到新鄉開會,那時我還在小學讀書,沒有學過中國地理,所以新鄉就成了我知道的除了山東省省會濟南之外的第二個省會級大城市。但是,到我上高小的時候,平原省就撤銷了,聊城就又成了山東省的一個地區,當時我屬的茌平縣也成了山東省的一個縣。
從現在想來,河南應該是我的半拉子故鄉,就是從語言上說,我听不懂齊地的膠東方言,卻能听懂河南話,但在後來,河南卻沒有給我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對于那些與我沒有多少關系的省份,倒有更加鮮明的記憶︰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個直轄市自不必說,像西藏、新疆、內蒙古自治區,一是因其大,二是因其遠,三是因其為少數民族地區,有著與我們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風俗,你就無法將它們從我的腦海里挖出去。別人不知道,對于我,一想起“我們的祖國”,首先想起的不是我們的首都北京,也不是我的故鄉山東,倒是這三個邊疆的大省(自治區)。大概這也有它的道理︰“要不是有這三個大省(自治區),我們的祖國哪能有這麼大呀!”東北,更是我們山東人熟悉的一片荒涼但卻肥沃的土地,是我們山東人在災荒年外出逃荒的地方,我舅舅家的兩個哥哥因為家里貧窮,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下了關東”,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戶。大概也是因為他們的關系,在我兒時的印象里,哈爾濱就像一個神話里的城市,與當代青年心目中的紐約差不多。它牽動的不是我的神經,而是我的想象。一到了20世紀50年代,東北的地圖就愈加鮮活起來,鞍山的鐵,撫順的煤,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解放牌汽車,東北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勞動模範王崇倫,《把一切獻給黨》的作者吳運鐸……在我們小小的腦海里擺得滿滿當當。到了20世紀60年代,大慶的石油以及王鐵人的名字,更像一場地震一樣震動過我們的腦海。對于我們研究現代文學的,更忘不了20世紀30年代的東北作家群,蕭軍即使不是一個多麼杰出的作家,也是作家隊伍中的一個真正的男子漢,而蕭紅則是中國現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我們那里,人們一說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總是說“到了雲南、貴州嘎嘎二縣”。“嘎嘎二縣”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但雲南、貴州作為兩個省份,卻也因此而在我的腦海里扎下了根。我對于廣西的印象,並不深刻,但一旦將廣東、廣西連在一起,也就令我難以忘懷了。不知為什麼,對中國文人贊賞的自然美景,我都沒有多麼深刻的感動,倒是敦煌的鳴沙山,有著令我感動的荒涼。“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小學地理課本中就讀到過,像杭州的西湖一樣,並沒有惹起我的夢魂繚繞的向往。廣東,那可是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無時無刻都會踫到的一個省份。從林則徐的虎門禁煙,到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黃花崗七十二烈±,到了20世紀20年代,廣州又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革命策源地”,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這些文學大家也曾群集廣州,一時成為中國革命政治、文化的中心,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年之間,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大事,都與廣東人有關。到了新時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又是在廣東開始的。像深圳這樣在幾年間便拔地而起的現代城市,在世界歷史上大概也是少有的。與廣東、廣西有些相像的,則是湖北和湖南。武漢三鎮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演出過幾出大戲,聞一多、胡風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很燙手的兩個著名作家,但湖南在我的腦海里則更加鮮艷奪目。舜帝在這里長眠,屈原在這里投江,而到了當代中國,毛澤東的名字幾乎比“中國”這個名字更加響亮、更加輝煌壯麗,更莫提中國近現代史上那些琳瑯滿目的湖南籍的元帥、半軍、黨政要點、作家、文人了。江西的井岡山、貴州的遵義、陝西的延安、1949年之後的北京,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上幾顆最耀眼的明星。在《漫議》中,我曾說過陝西文化的一些壞話,說盡管說,但陝西省卻不是容易被人忘卻的省份,僅就1949年之後的文學,恐怕就沒有任何一個省份可以與衛西媲美。在河南作家群興起的前夕,還有陝西的三部長篇小說進京,轟動了當時的文壇。“十七年”的柳青,新時期的路遙、賈平凹,都不是那種可以一笑了之的文學作家。我作為一個山東人,同樣是不會忘記山西的,在改革開放的前後,我們那個地區的主要對“外”貿易恐怕就是山西的貿易了。一輛或幾輛卡車,裝著我們家鄉的糧食,到山東,再換回那里的煤來。吃的是山東糧,燒的是山西煤,我能忘掉山西這個省份嗎?“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昔陽縣的大寨和大寨的陳永貴,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山藥蛋派”和“山藥蛋派”的趙樹理,也是時時提醒我不能忘記山西這個省份的諸多因素。
……
從現在想來,河南應該是我的半拉子故鄉,就是從語言上說,我听不懂齊地的膠東方言,卻能听懂河南話,但在後來,河南卻沒有給我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對于那些與我沒有多少關系的省份,倒有更加鮮明的記憶︰北京、上海、天津這三個直轄市自不必說,像西藏、新疆、內蒙古自治區,一是因其大,二是因其遠,三是因其為少數民族地區,有著與我們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風俗,你就無法將它們從我的腦海里挖出去。別人不知道,對于我,一想起“我們的祖國”,首先想起的不是我們的首都北京,也不是我的故鄉山東,倒是這三個邊疆的大省(自治區)。大概這也有它的道理︰“要不是有這三個大省(自治區),我們的祖國哪能有這麼大呀!”東北,更是我們山東人熟悉的一片荒涼但卻肥沃的土地,是我們山東人在災荒年外出逃荒的地方,我舅舅家的兩個哥哥因為家里貧窮,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下了關東”,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戶。大概也是因為他們的關系,在我兒時的印象里,哈爾濱就像一個神話里的城市,與當代青年心目中的紐約差不多。它牽動的不是我的神經,而是我的想象。一到了20世紀50年代,東北的地圖就愈加鮮活起來,鞍山的鐵,撫順的煤,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解放牌汽車,東北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勞動模範王崇倫,《把一切獻給黨》的作者吳運鐸……在我們小小的腦海里擺得滿滿當當。到了20世紀60年代,大慶的石油以及王鐵人的名字,更像一場地震一樣震動過我們的腦海。對于我們研究現代文學的,更忘不了20世紀30年代的東北作家群,蕭軍即使不是一個多麼杰出的作家,也是作家隊伍中的一個真正的男子漢,而蕭紅則是中國現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我們那里,人們一說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總是說“到了雲南、貴州嘎嘎二縣”。“嘎嘎二縣”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但雲南、貴州作為兩個省份,卻也因此而在我的腦海里扎下了根。我對于廣西的印象,並不深刻,但一旦將廣東、廣西連在一起,也就令我難以忘懷了。不知為什麼,對中國文人贊賞的自然美景,我都沒有多麼深刻的感動,倒是敦煌的鳴沙山,有著令我感動的荒涼。“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小學地理課本中就讀到過,像杭州的西湖一樣,並沒有惹起我的夢魂繚繞的向往。廣東,那可是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無時無刻都會踫到的一個省份。從林則徐的虎門禁煙,到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黃花崗七十二烈±,到了20世紀20年代,廣州又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革命策源地”,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這些文學大家也曾群集廣州,一時成為中國革命政治、文化的中心,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年之間,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大事,都與廣東人有關。到了新時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又是在廣東開始的。像深圳這樣在幾年間便拔地而起的現代城市,在世界歷史上大概也是少有的。與廣東、廣西有些相像的,則是湖北和湖南。武漢三鎮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演出過幾出大戲,聞一多、胡風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很燙手的兩個著名作家,但湖南在我的腦海里則更加鮮艷奪目。舜帝在這里長眠,屈原在這里投江,而到了當代中國,毛澤東的名字幾乎比“中國”這個名字更加響亮、更加輝煌壯麗,更莫提中國近現代史上那些琳瑯滿目的湖南籍的元帥、半軍、黨政要點、作家、文人了。江西的井岡山、貴州的遵義、陝西的延安、1949年之後的北京,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上幾顆最耀眼的明星。在《漫議》中,我曾說過陝西文化的一些壞話,說盡管說,但陝西省卻不是容易被人忘卻的省份,僅就1949年之後的文學,恐怕就沒有任何一個省份可以與衛西媲美。在河南作家群興起的前夕,還有陝西的三部長篇小說進京,轟動了當時的文壇。“十七年”的柳青,新時期的路遙、賈平凹,都不是那種可以一笑了之的文學作家。我作為一個山東人,同樣是不會忘記山西的,在改革開放的前後,我們那個地區的主要對“外”貿易恐怕就是山西的貿易了。一輛或幾輛卡車,裝著我們家鄉的糧食,到山東,再換回那里的煤來。吃的是山東糧,燒的是山西煤,我能忘掉山西這個省份嗎?“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昔陽縣的大寨和大寨的陳永貴,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山藥蛋派”和“山藥蛋派”的趙樹理,也是時時提醒我不能忘記山西這個省份的諸多因素。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