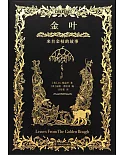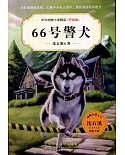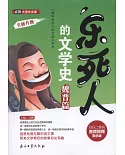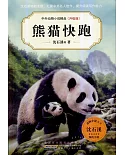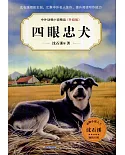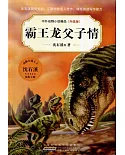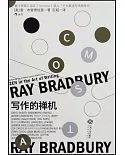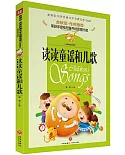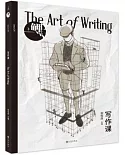全書分三輯,第一輯以憶人為主,第二輯以評作品為主,第三輯以實踐中探討問題為主,但不能載然分開,各輯內涵隨時都互有滲透處。
全書分三輯,第一輯作者述及師友,從朱光潛、聞一多、沈從文、梁宗岱、林徽因、葉公超、戴望舒、馮至、羅大岡、冼星海、周煦良、邵洵美、李健吾、吳世昌、師陀,到何其芳、方敬,以生年先後為序;第二輯論及詩文,從徐志摩、廢名、馮至、吳興華到古蒼梧、江弱水,也如此(所有在世者今只此最後二位中、青年人),第三輯各篇則以寫作先後為序。
目錄
增訂自序
第一輯
一條界線和另一方面:郭沫若詩人百年生辰紀念
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
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
還是且講一點他:追念沈從文
人事固多乖:紀念梁宗岱
窗子內外:憶林徽因
赤子心與自我戲劇化:追念葉公超
悼念戴望舒
悼馮至
又參商幾度:追念羅大岡
冼星海紀念附驥小識
人尚性靈,詩通神韻:追憶周煦良
追憶邵洵美和一場文學小論爭
追憶李健吾的“快馬”
羅音室主吳世昌謝世志哀
話舊成獨白:追念師陀
突圍小記胡喬木
淡如水中識醇味:追念王塵無
何其芳與詩派
何其芳與《工作》
何其芳晚年譯詩
脫帽志哀:追憶方敬
第二輯
徐志摩詩重讀志感
《徐志摩選集》序
《徐志摩譯詩集》序
《馮文炳選集》序
《戴望舒詩集》序
詩與小說:讀馮至創作《伍子胥》
《李廣田散文選》序
《李廣田詩選》序
《孫毓棠詩集》序
吳興華的詩與譯詩
讀宗璞《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
蓮出于火:讀古蒼梧詩集《銅蓮》
介紹江弱水的幾首詩
第三輯
開講英國詩想到的一些體驗
哼唱型節奏(吟調)和說話型節奏(誦調)
對于新詩發展問題的幾點看法
談詩歌的格律問題
《雕蟲紀歷》自序
分與合之間:關于西方現代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
與周策縱談新詩格律信
答讀者:談“新詩”形式問題的討論
今日新詩面臨的藝術問題
新詩和西方詩
譯詩藝術的成年
《英國詩選》編譯序
說“三”道“四”:讀余光中《中西文學之比較》,從西詩、舊談詩到新詩律探索
文學翻譯與語言感覺
翻譯對于中國現代詩的功過
難忘的塵緣
——序秋吉久紀夫編譯日本版《卞之琳詩集》
重探參差均衡律
——漢語古今新舊體詩的聲律通途
無意義中自有意義
——戲譯愛德華‧里亞諧趣詩隨想
重溫《講話》看現實主義問題
相干下不相干
——詩秋吉久紀夫論《尺八》詩
第一輯
一條界線和另一方面:郭沫若詩人百年生辰紀念
政治美學:追憶朱光潛生平的一小段插曲
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
還是且講一點他:追念沈從文
人事固多乖:紀念梁宗岱
窗子內外:憶林徽因
赤子心與自我戲劇化:追念葉公超
悼念戴望舒
悼馮至
又參商幾度:追念羅大岡
冼星海紀念附驥小識
人尚性靈,詩通神韻:追憶周煦良
追憶邵洵美和一場文學小論爭
追憶李健吾的“快馬”
羅音室主吳世昌謝世志哀
話舊成獨白:追念師陀
突圍小記胡喬木
淡如水中識醇味:追念王塵無
何其芳與詩派
何其芳與《工作》
何其芳晚年譯詩
脫帽志哀:追憶方敬
第二輯
徐志摩詩重讀志感
《徐志摩選集》序
《徐志摩譯詩集》序
《馮文炳選集》序
《戴望舒詩集》序
詩與小說:讀馮至創作《伍子胥》
《李廣田散文選》序
《李廣田詩選》序
《孫毓棠詩集》序
吳興華的詩與譯詩
讀宗璞《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
蓮出于火:讀古蒼梧詩集《銅蓮》
介紹江弱水的幾首詩
第三輯
開講英國詩想到的一些體驗
哼唱型節奏(吟調)和說話型節奏(誦調)
對于新詩發展問題的幾點看法
談詩歌的格律問題
《雕蟲紀歷》自序
分與合之間:關于西方現代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
與周策縱談新詩格律信
答讀者:談“新詩”形式問題的討論
今日新詩面臨的藝術問題
新詩和西方詩
譯詩藝術的成年
《英國詩選》編譯序
說“三”道“四”:讀余光中《中西文學之比較》,從西詩、舊談詩到新詩律探索
文學翻譯與語言感覺
翻譯對于中國現代詩的功過
難忘的塵緣
——序秋吉久紀夫編譯日本版《卞之琳詩集》
重探參差均衡律
——漢語古今新舊體詩的聲律通途
無意義中自有意義
——戲譯愛德華‧里亞諧趣詩隨想
重溫《講話》看現實主義問題
相干下不相干
——詩秋吉久紀夫論《尺八》詩
序
廣州《隨筆》雙月刊文藝百家圖文系列1986年第5期所刊我隨湊的一“文”,只是一句話——我寫的詩中找不到一個“詩”字。倒也不是隨便說的,說的既是事實,也驗證了我的詩觀。
我認為寫詩應似無所為而為,全身心投入似淺實深的意境,不意識到寫詩,只求盡可能恰切傳導真摯的感應,深入淺出,力求達到最科學也即最藝術的化境,有可能與正常的一般讀者或特定讀者共享其成,言志也罷,載道也罷,不流于濫調,不淪為說教,寧取“手揮五弦,目送飛鴻”式,不沾“咄咄書空”氣,杜絕現代西方所謂“自動寫作”風——那等于扶乩。另一方面我也能贊賞以詩論詩(文),例如清代趙翼或18世紀英國古典派詩人蒲伯所為、所得的一些警語,那是另一回事。
1939年後,我一度完全不寫詩,特別從50年代起,談詩就多了一點。形勢一轉,我對師友,今已大多數作古的,不論相知深淺的前輩或儕輩,著述閱讀生涯中實質上與詩有緣的,無論寫有詩篇立有詩說與否,我為文針對他們或他們的產品,都以詩論處,討論也好,追思也好,寫序也好,評論也好,推舉也好,借以自己立論也好,不注重人家的私生活(就其中個別有意義處另外為文),因為有交誼,不免涉及自己(專講到自己,則偶見他文)。 自己的作品集序則只收了一篇。除了一兩篇探討詩律文字或多或少可稱學術性文章,所收各篇都不扮起一副學術性面孔,只是都貫串了我自己既有堅持也有發展的見解。
全書分三輯,第一輯以憶人為主,第二輯以評作品為主,第三輯以實踐中探討問題為主,但不能截然分開,各輯內涵隨時都互有滲透處。
第一輯述及師友,從朱光潛、聞一多、沈從文、梁宗岱、林徽因、葉公超、戴望舒、馮至、羅大岡、冼星海、周煦良、邵洵美、李健吾、吳世昌、師陀,到何其芳、方敬,以生年先後為序;第二輯論及詩文,從徐志摩、廢名、馮至、吳興華到古蒼梧、江弱水,也如此(所有在世者今只此最後二位中、青年人),第三輯各篇則以寫作先後為序。
本書初版于、1984年,印過一萬四千冊,收文22篇,約僅十一萬多字,現在刪去了兩三篇,增入後寫的三十多篇,曾載香港《文匯報》文藝版、台北《聯合報副刊》、北京《新文學史料》、上海《文匯報‧筆會》、上海《文匯月刊》、香港《明報月刊》、北京《詩刊》等,都核改過個別時地事實細節,校訂過個別誤排,統一整飭過文詞,總篇幅也就不止倍增。越發加重了出版社主持同志、責編和監印同志的負擔,特在此也一並聲明致謝。
1994年5月25日寫
2000年5月5日改
我認為寫詩應似無所為而為,全身心投入似淺實深的意境,不意識到寫詩,只求盡可能恰切傳導真摯的感應,深入淺出,力求達到最科學也即最藝術的化境,有可能與正常的一般讀者或特定讀者共享其成,言志也罷,載道也罷,不流于濫調,不淪為說教,寧取“手揮五弦,目送飛鴻”式,不沾“咄咄書空”氣,杜絕現代西方所謂“自動寫作”風——那等于扶乩。另一方面我也能贊賞以詩論詩(文),例如清代趙翼或18世紀英國古典派詩人蒲伯所為、所得的一些警語,那是另一回事。
1939年後,我一度完全不寫詩,特別從50年代起,談詩就多了一點。形勢一轉,我對師友,今已大多數作古的,不論相知深淺的前輩或儕輩,著述閱讀生涯中實質上與詩有緣的,無論寫有詩篇立有詩說與否,我為文針對他們或他們的產品,都以詩論處,討論也好,追思也好,寫序也好,評論也好,推舉也好,借以自己立論也好,不注重人家的私生活(就其中個別有意義處另外為文),因為有交誼,不免涉及自己(專講到自己,則偶見他文)。 自己的作品集序則只收了一篇。除了一兩篇探討詩律文字或多或少可稱學術性文章,所收各篇都不扮起一副學術性面孔,只是都貫串了我自己既有堅持也有發展的見解。
全書分三輯,第一輯以憶人為主,第二輯以評作品為主,第三輯以實踐中探討問題為主,但不能截然分開,各輯內涵隨時都互有滲透處。
第一輯述及師友,從朱光潛、聞一多、沈從文、梁宗岱、林徽因、葉公超、戴望舒、馮至、羅大岡、冼星海、周煦良、邵洵美、李健吾、吳世昌、師陀,到何其芳、方敬,以生年先後為序;第二輯論及詩文,從徐志摩、廢名、馮至、吳興華到古蒼梧、江弱水,也如此(所有在世者今只此最後二位中、青年人),第三輯各篇則以寫作先後為序。
本書初版于、1984年,印過一萬四千冊,收文22篇,約僅十一萬多字,現在刪去了兩三篇,增入後寫的三十多篇,曾載香港《文匯報》文藝版、台北《聯合報副刊》、北京《新文學史料》、上海《文匯報‧筆會》、上海《文匯月刊》、香港《明報月刊》、北京《詩刊》等,都核改過個別時地事實細節,校訂過個別誤排,統一整飭過文詞,總篇幅也就不止倍增。越發加重了出版社主持同志、責編和監印同志的負擔,特在此也一並聲明致謝。
1994年5月25日寫
2000年5月5日改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