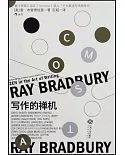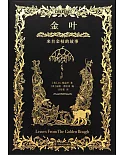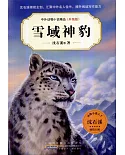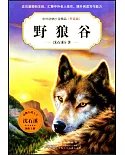本書分為上下編。
上篇「《水滸傳》的成書」將盡可能揭示它在每一個時期的大致形態,還它一個脈絡清晰的成書過程,計八章:宋代理學的發展與「說話」的興盛。宋江三十六人早期的故事形態是極其簡單的,通過對《宋江三十六贊》的分析,大致揭示了當時水滸故事的規模及其內容梗概。三十六人單個話本之後出現的是集諸多好漢故事之大成的《宋江》,這是通俗小說發展的規律決定的,郎瑛《七修類稿》的記載啟發了我們,它的最先成書應該是南宋後期,後來被收入《宣和遺事》中的「梁山泊聚義本末」即是它故事的縮寫。元代流行的《宋江》平話,比南宋後期略有改動,元代留傳至今的幾部水滸雜劇中介紹的共同背景可以作證,《瓮天脞語》中所記宋江到李師師家為謀求招安所寫的詞作也是一證;元代、明初文人參與改編了水滸雜劇,這些雜劇的淵源應是《宋江》及其他水滸故事。為《水滸傳》成書前《宋江》一書的最後形態繪出一幅完整的素描;討論了明代前期與中期之間出現的幾部水滸英雄單篇傳奇。由《宋江》和水滸英雄傳奇共同組合而成的《水滸傳》許多矛盾、不諧在所難免,本章從地理描繪的錯誤、形象塑造情節設計的矛盾、語言表述的不同、與元末明初水滸雜劇無涉四個方面予以論證。以《三國志演義》為始作俑者,《水滸傳》繼之,明代中葉高明的書商推出了一個「羅貫中編次」系列。對《水滸傳》作者問題進行了認真而深入的研究,認定它是陸續完成的,羅、施二人的姓名均是書商所署,羅僅是元末明初的戲曲家,施是「演為繁本者的托名」。
下篇為「《水滸傳》的傳播」,計五章:從明代中後期的思想解放思潮說起,引出持續到明末的「水滸熱」。從對《水滸傳》版本的梳理開始,理順了繁本、簡本、繁簡結合本先後因陳的關系。從李贄、金聖嘆對《水滸傳》的批評人手,論及《水滸傳》在晚明之後的影響;又從金批本風靡數百年的歷史事實說起,討論了歷代統治者對《水滸傳》的禁毀。《水滸傳》的續衍問題:《水滸後傳》為英雄聚義設計了理想的歸宿;《後水滸傳》對草澤聚義的形式提出了新的思考;《盪寇志》是對《水滸傳》的反動;《金瓶梅》對《水滸傳》的幾個回目進行細膩的擴充。在《水滸傳》其它藝術形式的傳播章中,分別就水滸戲、說水滸、唱水滸三個方面略作探討,揭示了水滸故事流傳的廣泛性和形式的多樣性。
序
就像西方人會將「荷馬史詩」划歸「文學」,有時也會將《伊利亞特》、《奧德賽》稱作「長篇敘事詩」一樣,我們也會比照通行的文學分類,將中國古代幾部篇幅宏大、通過長期「集體累積」而成書的敘事文學作品——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稱作「古代長篇白話小說」。
不過,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略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僅僅從「文學」的角度,或者從「敘事詩」的角度來研究和解讀「荷馬史詩」,顯然是不夠的。馬克思就將「荷馬史詩」主要作為「希臘神話」來看待,並將其視為一種「藝術形式」——即用想象和借助想象,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將自然和社會加以形象化的一種「藝術形式」。指出「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馬克思以前的黑格爾則早已指出,「荷馬史詩」描寫的雖然是神和人(英雄)的事跡,其要義卻在於表現特定歷史時期民族的生活情景、行為方式和精神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荷馬史詩」雖然有真實的歷史事件為基礎,但它並不是史學著作,其偉大意義也不主要在於對希臘古史的復述。對「荷馬史詩」而言,它既是以「敘事詩」為外在形式的「史詩」,又是以「神話傳說」為基本內容,並對后世不斷產生影響的「文化經典」。
確實,像「荷馬史詩」這樣通過「集體累積」創造的「敘事詩」,在精神蘊涵上,是不同於后世作家個人創作的「敘事詩」的——不管后世如何對它進行模仿。西方學者對「荷馬史詩」的研究和看法,對我們研究帶有「集體累積」成書特點的《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等應該是有啟發的。我曾經在一篇淪《三國志演義》的文章中談到過,正是在長達數百年的成書過程中,《三國志演義》積淀、凝聚了中古以來中國廣大民眾的歷史觀、倫理觀和道德觀,反映着社會不同階層、不同人群觀念意識的折衷,尤其是在繼承傳統「經典文化」的同時,又對其道德倫理觀念等進行了「解構」和新的闡釋,體現了時代的特征;《三國志演義》不是一般意義的古代「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史詩」性質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部代表我們民族一定歷史時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經典」;《三國志演義》的成書、傳播及其巨大的影響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精神現象」,僅僅將《三國志演義》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或僅以文學批評的方式來解讀《三國志演義》是遠遠不夠、甚至是不得要領的。對《水滸傳》,我也有一些類似的想法,雖然由於《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在成書過程、題材類型、精神意象和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並不能將兩者等同起來。
關於《水滸傳》是經過長期「集體累積」才最后成書的作品,中國現代的研究者,胡適、魯迅以來,一般是沒有疑議的。雖然有人從文學的角度更願意強調「最后寫定者」的「創造性勞動」,但也無法否認《水滸傳》有一個「集體累積」的過程。
……
不過,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略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僅僅從「文學」的角度,或者從「敘事詩」的角度來研究和解讀「荷馬史詩」,顯然是不夠的。馬克思就將「荷馬史詩」主要作為「希臘神話」來看待,並將其視為一種「藝術形式」——即用想象和借助想象,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將自然和社會加以形象化的一種「藝術形式」。指出「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馬克思以前的黑格爾則早已指出,「荷馬史詩」描寫的雖然是神和人(英雄)的事跡,其要義卻在於表現特定歷史時期民族的生活情景、行為方式和精神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荷馬史詩」雖然有真實的歷史事件為基礎,但它並不是史學著作,其偉大意義也不主要在於對希臘古史的復述。對「荷馬史詩」而言,它既是以「敘事詩」為外在形式的「史詩」,又是以「神話傳說」為基本內容,並對后世不斷產生影響的「文化經典」。
確實,像「荷馬史詩」這樣通過「集體累積」創造的「敘事詩」,在精神蘊涵上,是不同於后世作家個人創作的「敘事詩」的——不管后世如何對它進行模仿。西方學者對「荷馬史詩」的研究和看法,對我們研究帶有「集體累積」成書特點的《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等應該是有啟發的。我曾經在一篇淪《三國志演義》的文章中談到過,正是在長達數百年的成書過程中,《三國志演義》積淀、凝聚了中古以來中國廣大民眾的歷史觀、倫理觀和道德觀,反映着社會不同階層、不同人群觀念意識的折衷,尤其是在繼承傳統「經典文化」的同時,又對其道德倫理觀念等進行了「解構」和新的闡釋,體現了時代的特征;《三國志演義》不是一般意義的古代「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史詩」性質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部代表我們民族一定歷史時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經典」;《三國志演義》的成書、傳播及其巨大的影響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精神現象」,僅僅將《三國志演義》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或僅以文學批評的方式來解讀《三國志演義》是遠遠不夠、甚至是不得要領的。對《水滸傳》,我也有一些類似的想法,雖然由於《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在成書過程、題材類型、精神意象和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並不能將兩者等同起來。
關於《水滸傳》是經過長期「集體累積」才最后成書的作品,中國現代的研究者,胡適、魯迅以來,一般是沒有疑議的。雖然有人從文學的角度更願意強調「最后寫定者」的「創造性勞動」,但也無法否認《水滸傳》有一個「集體累積」的過程。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