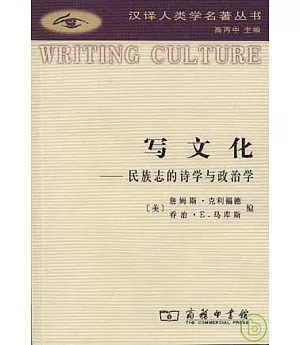在我看來,在美國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近期歷史上,即從1980年代開始,一個突出的事件就是這門學科(毋寧說普通人類學中四領域分支組織中的這個很有影響的部分)與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容納它的領地之間發生了深刻的斷裂。當然,這個學科與那些形成了社會文化人類學家的認同的制度模式的一些方面仍然保持著功能上的契合,如同一些人物,諸如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在英國和弗朗斯·博厄斯(Franz
Boas)在美國,通過他們的著作開創學科時的那樣。大多數的人類學家仍然從對美國之外的某一個地理區域的專門研究來開始其職業生涯[盡管很少有人接受過地區研究(areas
studies)的專門化教育,這種教育在美國是從1950年代到整個1970年代成為學生被鼓勵去選擇的科目。當時處於冷戰和發展研究的氛圍中,這種跨學科的項目得到巨大的投資,不過從那以後就一直在衰落。歐洲本身也已經成為了美國人類學家的具有相當高的合法性的異域,而且,一些專門領域,如科技研究,也獲得了與傳統的異域研究同等的聲望和合法性]。至少從他們最初的學位論文研究開始,大多數人類學家仍然活動在田野工作與民族志的方法所確定的范圍里,活動在由奠基人物創立的傳統所建立的群體精神與專業教學之神話的氛圍里。然而,相關職業不斷得以演進的方式以及這些職業現在衍生的方式,田野工作經驗的實際性質以及作為掌握規范途徑的田野工作經歷怎樣被講述並在專業領域內傳遞的方式,研究的對象怎樣被概念化,以及人類學首要的跨學科伙伴是誰——所有這些對於人類學專業的再生產至關重要的問題,都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當我在1970年代中期成為一名職業人類學家的時候,我在哈佛按照慣常的學徒模式進行准備。我被確定為一名大洋洲專家,並且在波利尼西亞西部從事長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在湯加群島)。我的田野工作的形成明確依據一些基本的所關心的問題,如親屬制度、儀式、政治和宗教,並通過在當地社區居住和訪談的方法進行考察。然而,在這個時候,至少在研究生當中,法國後結構主義者諸如福柯和巴爾特的影響、女性主義學者的成就、英國文化研究的實際重要性、創造一種結構主義的歷史的努力(與當時盛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相對)以及對田野工作的政治學的敏感(美國1960年代短期騷動的結果之一)全都進入了學術氛圍。可以說,在教室之外,我和我的同事仍然被認為正在從事著基礎的「民族與地方」(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民族志研究。盡管那樣,當我們早該為我們的學徒工作預見到不同的理論與主題的要點的時候,為了實現有歷史意義的、未完成的,或者有人說被中斷的,但在意識形態方面仍然具有霸權的『關於人類的一種普適科學的宏偉計划,這一工作仍然按照它的原有形式在運行:致力於為全球民族志檔案添加比較的材料或待解決的問題,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特殊任務似乎就是描寫和分析不是前現代就是非現代的生活形式。
然而,尤其在傑出的研究生項目中,盡管許多更年輕的人類學家出於信念和領悟力並不完全贊同這種規划,但是參與這一學科就意味著通過民族志的形式與心懷對田野工作的期望去循規蹈矩,而這確實常常是接受人類學學科訓練的主要吸引力。甚至在那時,更不用說直到現在,美國人類學家的研究課題就是非常多樣的。例如,特別是在二戰後的頭兩個十年,在得到西方國家大力資助的發展研究的指示下,人類學家開始關注他們曾經研究過的傳統民族所經歷的各種變遷情形,不管他們是農民、工人、城市居民還是跨國移民。但是,在所有的這種多樣性和後殖民的轉變中,作為基礎的馬林諾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據著學科的中心地位,這種實踐反過來又繼續嵌入在訓練模式中,定義著在學者們進入到人類學的學徒工作中什麽能做和什麽不能做。
今天,美國人類學仍然以同等的興趣多樣性為特征(雖然自從1980年代以來這些興趣在構成和表達上與此前功盡棄大相徑庭),地區專門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核心特征仍然得到堅持,但是范疇的設置、具體研究參與的更廣泛課題的潛在意義以及核心方法的實踐本身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我們那一代開始形成輪廓的東西如今已成為主流。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項目逐漸被一系列跨學科影響所界定,截然不同於這個學科在發展中所受到的那些跨學科的影響。規定民族志方向的主題和爭論不再起作用,而成為了學科歷史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教學中被當作了學科史)。更新的討論領域和理論關懷通過跨學科討論得到發展,這些討論以1980年代以來關於文化分析的豐富而廣泛的基本關懷為基礎,而不是產生於人類學家共同體自身圍繞人類學研究的已有成果所開展的仔細辯論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