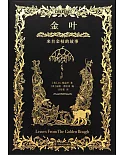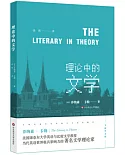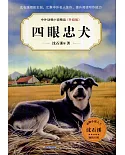從《最藍的眼楮》中一個黑人小女孩渴望得到一雙白人那樣的藍眼楮,經過日夜祈求上帝,最後居然夙願得償,真的有了一雙美麗的藍眼楮,卻終於發現自己仍然無法擺脫悲慘的命運;到《秀拉》中正是黑人女孩秀拉那種令人瞠目的要把這個世界「撕成兩半」的決心讓她成為同胞心目中傾慕的獨立、大膽和自由精神的化身,美國黑人似是已從只知祈求的兒童發展到決心反抗的青年。
托妮·莫瑞森在其處女作《最藍的眼楮》(1969)及其後的《秀拉》(1973)這兩部小說中不僅刻畫了佩克拉·勃瑞德拉渥和秀拉·匹斯這兩個有著強烈對比的形象,以她們的不同命運及書中眾多其他黑人的屈辱生活為人們昭示了作者本民族的過去和現狀,並探討了期 未來的前人管,更一舉確立了她「當代美國黑人社會文學觀察家」的地位。
托妮·莫瑞森(1931~)是當今美國最有影響的黑人女作家,《最藍的眼楮》(1970)是她發表的第一部小說。講的是一個年僅11歲的黑人少女佩克拉·布里德洛夫,因為相貌平平,不被家人、同學和鄰居喜歡,生活壓抑,於是便夢想著能有一雙像白人姑娘那樣美麗的藍眼楮,因為當時黑人女孩子普遍相信「藍眼楮的黑人是最美的」。然而美好的夢想與丑陋的現實有著太大的反差。她不僅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反而被父親強奸,懷上了身孕,墮入更加痛苦的深淵。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使佩克拉精神錯亂,心智瘋狂,她出現了幻覺,相信自己真的擁有了一雙十分美麗的最藍的眼楮。
30年前,正是這部作品確立了莫瑞森在美國黑人文壇上的地位。之後,她繼續探索黑人生活,尤其是黑人婦女的遭遇,又創作了反映黑人反抗精神的小說《秀拉》(Sula, 1973),成名作《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獲普利策小說獎的《寵兒》(Beloved, 1987),進入90年代後,她還發表了長篇小說《爵士樂》(Jazz, 1992)和《樂園》(The
Paradise,1998)。莫瑞森的作品揭示了在美國種族壓迫的大背景下,白人文明與黑人傳統之間的矛盾沖突,探討黑人獲得自由人格的出路。莫瑞森在作品中利用黑人民間文學和神話傳說來渲染氣氛,又借鑒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給環境和人物籠罩了一層詭譎的神秘色彩,把今天的現實描繪成「現代神話」,而且她的語言十分口語化,人物的對話寫得生動傳神。所有這些特點,使莫瑞森成為當代美國黑人文學的代表和領袖人物,因而,她於199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也是毫不奇怪的。
奇怪的是1970年出版的這部不足20萬字的《最藍的眼楮》,居然在30年後的今天又大受青睞,躋身新書暢銷榜的行列,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序
自從1993年托妮·莫瑞森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這位美國黑人女作家已經蜚聲全球,可是此前她所走過的二十四年文學創作歷程又是多麽堅定而執著啊!
當年的托妮在結婚生子後,曾有一段時間賦閑在家。這位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的文學碩士於孤寂中和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組織了一個「文學俱樂部」。她們定期聚首,每人都要拿出自己的作品朗誦,彼此講評。在一次這樣的活動中,托妮讀了自己寫的這樣二個童話:一個黑人小女孩渴望得到一雙白人那樣的藍眼楮,經過日夜祈求上帝,最後居然夙願得償,真的有了一雙美麗的藍眼楮。若干年後,她掘此寫成一部篇幅不長的小說,並於1969年出版發行,這就是她的處女作《最藍的眼楮》(The Bluest Eye)。
作為成書的作品,《最藍的眼楮》已經不再是一個神奇的寓言故事,而成為一部「把神話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機地結合起來」的獨特作品。就是說,她為這個故事賦予了全新的內涵,要對她的黑人同胞引起振聾發聵的作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歷經多年的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終於演變成波瀾壯闊的黑人權力運動,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但是,針對白人社會傳統的認為黑人丑陋的觀點,一些黑人簡單且得意地提出了「黑人是美的」口號。就此,托妮·莫瑞森一方面在政論文中指出: 「人類生活由於世界上最表面的東西——身體美——而遭到徹底毀滅」,「黑人是美的』這一口號」是「隨手拈來且具有反作用的神話創作的最好例證。┅┅不錯,我們是也很漂亮,但這種提法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和我們的境遇,無非是對一個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個白人概念翻轉過來仍然是白人概念。身體美的概念作為一種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壞性的觀點之一,我們應該對此不屑一顧┅┅把問題歸結於我們是否美的症結來自干衡量價值的方式,這種價值是徹頭徹尾的細微末節並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於這個問題是理智上無可救藥的奴隸制。」她的意思很明確:身體美是一種白人的價值觀,即使按照這一價值觀把「黑人丑」變成「黑人美」,依然不足取,而黑人肯干接受這種白人的價值觀,本身便是一種精神奴役制的惡果。這是多麽犀利而中肯的觀點啊,正是憑借這樣一篇宣戰書,使托妮·莫瑞森「確立了她的當代美國黑人社會文學觀察家的地位」。但她並不滿足於不斷應邀撰寫社會評論,而是操起創作之筆,寫出了這部《最藍的眼楮》。
勃瑞德拉渥(原文有「熱愛繁育」之義)一家世代受窮,相貌奇丑。小女兒佩克拉在家中處境尷尬,在外面受盡屈辱,她把這一切都歸結為自己長相丑陋,但有了大大的美麗的藍眼楮之後,反倒兩次遭其父強奸,懷了他的孩子,招致了更大的不幸。這類情節在黑人小說中均非首創,但作者卻以此形象地說明:老一代甘於沉淪而不自知,更不想自拔,已經用懵懵懂懂的死結束了其渾渾噩噩的生;年輕一代想逃避現實,但只是碰壁。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作者,懷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情,果敢地暴露出本民族的陰暗面,旨在「抹去蒙塵,還其璞玉」。她在「怎樣」上明處落墨,卻在「為什麽」上暗處著筆(參見《最藍的眼楮》第二頁:「既然『為什麽』難於應付,人們只好到『怎樣』那里去避難了。」),為我們勾勒出美國種族壓迫的大背景。綽里的墮落和變態,緣起於他十四歲那年姨婆去世後被兩個白人用槍逼著為他們「表演」,從中取樂。黑松林中手電筒亮光一閃,一下子照亮了黑人痛苦的根源。
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挖掘,就會發現更深層次的哲理,小說的開篇部分有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天真也死去了。」那麽,什麽是作者所指的「天真」呢?那就是「天然和真實」——黑人民族朴實純真的傳統本色;也正是她為美國黑人民族抵御「精神奴役制」設想的有力武器。
她的這一主題思想,實際上在《秀拉》(Sula,1973)中仍在延續,該書的結尾處有奈爾的反復訴說:「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她所感慨的,正是他們失去的童年時代的「天然和真實」。
┅┅
當年的托妮在結婚生子後,曾有一段時間賦閑在家。這位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的文學碩士於孤寂中和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組織了一個「文學俱樂部」。她們定期聚首,每人都要拿出自己的作品朗誦,彼此講評。在一次這樣的活動中,托妮讀了自己寫的這樣二個童話:一個黑人小女孩渴望得到一雙白人那樣的藍眼楮,經過日夜祈求上帝,最後居然夙願得償,真的有了一雙美麗的藍眼楮。若干年後,她掘此寫成一部篇幅不長的小說,並於1969年出版發行,這就是她的處女作《最藍的眼楮》(The Bluest Eye)。
作為成書的作品,《最藍的眼楮》已經不再是一個神奇的寓言故事,而成為一部「把神話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機地結合起來」的獨特作品。就是說,她為這個故事賦予了全新的內涵,要對她的黑人同胞引起振聾發聵的作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歷經多年的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終於演變成波瀾壯闊的黑人權力運動,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但是,針對白人社會傳統的認為黑人丑陋的觀點,一些黑人簡單且得意地提出了「黑人是美的」口號。就此,托妮·莫瑞森一方面在政論文中指出: 「人類生活由於世界上最表面的東西——身體美——而遭到徹底毀滅」,「黑人是美的』這一口號」是「隨手拈來且具有反作用的神話創作的最好例證。┅┅不錯,我們是也很漂亮,但這種提法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和我們的境遇,無非是對一個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個白人概念翻轉過來仍然是白人概念。身體美的概念作為一種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壞性的觀點之一,我們應該對此不屑一顧┅┅把問題歸結於我們是否美的症結來自干衡量價值的方式,這種價值是徹頭徹尾的細微末節並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於這個問題是理智上無可救藥的奴隸制。」她的意思很明確:身體美是一種白人的價值觀,即使按照這一價值觀把「黑人丑」變成「黑人美」,依然不足取,而黑人肯干接受這種白人的價值觀,本身便是一種精神奴役制的惡果。這是多麽犀利而中肯的觀點啊,正是憑借這樣一篇宣戰書,使托妮·莫瑞森「確立了她的當代美國黑人社會文學觀察家的地位」。但她並不滿足於不斷應邀撰寫社會評論,而是操起創作之筆,寫出了這部《最藍的眼楮》。
勃瑞德拉渥(原文有「熱愛繁育」之義)一家世代受窮,相貌奇丑。小女兒佩克拉在家中處境尷尬,在外面受盡屈辱,她把這一切都歸結為自己長相丑陋,但有了大大的美麗的藍眼楮之後,反倒兩次遭其父強奸,懷了他的孩子,招致了更大的不幸。這類情節在黑人小說中均非首創,但作者卻以此形象地說明:老一代甘於沉淪而不自知,更不想自拔,已經用懵懵懂懂的死結束了其渾渾噩噩的生;年輕一代想逃避現實,但只是碰壁。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作者,懷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情,果敢地暴露出本民族的陰暗面,旨在「抹去蒙塵,還其璞玉」。她在「怎樣」上明處落墨,卻在「為什麽」上暗處著筆(參見《最藍的眼楮》第二頁:「既然『為什麽』難於應付,人們只好到『怎樣』那里去避難了。」),為我們勾勒出美國種族壓迫的大背景。綽里的墮落和變態,緣起於他十四歲那年姨婆去世後被兩個白人用槍逼著為他們「表演」,從中取樂。黑松林中手電筒亮光一閃,一下子照亮了黑人痛苦的根源。
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挖掘,就會發現更深層次的哲理,小說的開篇部分有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天真也死去了。」那麽,什麽是作者所指的「天真」呢?那就是「天然和真實」——黑人民族朴實純真的傳統本色;也正是她為美國黑人民族抵御「精神奴役制」設想的有力武器。
她的這一主題思想,實際上在《秀拉》(Sula,1973)中仍在延續,該書的結尾處有奈爾的反復訴說:「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她所感慨的,正是他們失去的童年時代的「天然和真實」。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