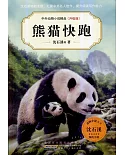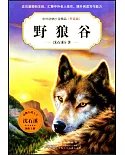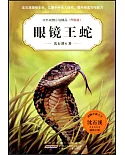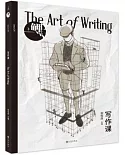圍棋是一種競技性游戲,在中國古代又被當作藝術,雖小道而通于大道。
弈何以成為藝?藝在中國古代又為何物?形而下之技與形而上之道是怎麼被打通的?中國古代棋論與文論、藝論在思維與言說方式上有何聯系與差別?弈境與藝境、游戲精神與藝術精神有何相通之處?這些正是本書想要解決的問題。
弈與天道、地道、人道溝通,從而成就了“弈”之三種境界︰天地之境、道德之境、審美之境。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弈與藝
第一節 弈之為藝
第二節 弈、藝與中國古代知識譜系
第二章 弈與道
第一節 周天畫地
第二節 制勝保德
第三節 技進乎道
第三章 弈與文
第一節 弈與文通
第二節 詩境與弈境
第三節 小說與圍棋
第四章 思與言
第一節 道與術
第二節 玄象與數理
第三節 雅俗之間
第五章 游戲精神與藝術精神
第一節 游戲與藝術
第二節 手談與對話
第三節 弈境與藝境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補記
第一章 弈與藝
第一節 弈之為藝
第二節 弈、藝與中國古代知識譜系
第二章 弈與道
第一節 周天畫地
第二節 制勝保德
第三節 技進乎道
第三章 弈與文
第一節 弈與文通
第二節 詩境與弈境
第三節 小說與圍棋
第四章 思與言
第一節 道與術
第二節 玄象與數理
第三節 雅俗之間
第五章 游戲精神與藝術精神
第一節 游戲與藝術
第二節 手談與對話
第三節 弈境與藝境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補記
序
我和雲波是1997年秋認識的,當時我們一同在蘇州大學參加一次外國文學研討會。此前,我曾讀過雲波發表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的論文,對他的學識很是佩服。那一年,雲波才34歲,剛出版了他的專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羅斯文化精神》,意氣風發。會上同事告訴我,這位年輕的湖南學者嗜愛圍棋,出差在外也不忘帶上棋具。經過《世界文學》編輯部主任李政文先生的攛掇,我和雲波擺開了棋局。從此我們結為契(棋)友,每次見面都要手談一番。
說來慚愧,我的棋齡已近40年。大概是在1966年春節,二哥湄江回杭州建德村探親時教我下棋。後來沈良齋和任旭園兩位老先生先後把他們珍藏的《圍棋》月刊和一副相當不錯的棋具送給我,進一步激發了我的興趣。“文革”“停課鬧革命”期間,我常去杭州柳浪聞鶯公園茶室觀棋,運氣好的時候能看到張禮源、董文淵等名手對弈。我感到不大習慣的是高手下棋時竟然盤外招用得很多,形勢佔優了就會盯住對手唱起京劇《沙家 》中“指導員”的台詞來︰“這時的心情不難體諒。”公園里的棋手,大都自信好強,經常出言不遜。我不敢在這樣的環境下經風雨,于是只能退回建德村,與同伴交手。
我雖然喜歡圍棋,但只是把它視為逞能爭勝的游戲,可以宣泄不良情緒。好友間偶爾失態,可以得到原諒。與陌生人斗氣,是很難為情的。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讀到一篇關于國際象棋的文章,寫得非常有趣。這位英國作者說,棋類運動是心理戰,其殘酷的程度比拳擊有過之而無不及;棋手的一招一式都以侵害、制服對手為目的,種種惡毒的辦法都想得出來,手段高明者實為“像蘇格拉底一般聰明的惡棍”。從9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圍棋刊物愛用一些贊美圍棋並把它與修身養性相聯系的文字。 出于一種自嘲的精神,我向《圍棋》月刊推薦那篇英國散文。這是敗興之舉,雜志編輯部自然不予理睬。由于對棋既愛又恨,加上天資不足,我的棋藝久不見長。每次對弈,下半盤總是松松垮垮,還要搬出唐寅的詩句做借口︰“懶算輸贏信手棋。”其實,不長棋就和蘇格蘭小說家巴里筆下的男孩彼德‧潘拒絕長大一樣,也很快活。
雲波的棋齡,恐怕不及我一半。他學棋晚,進步神速。每次與他對局,我都意識到他的棋力日強。勉強招架之余,我深知自己很快就不是他的對手。對此我倒欣然。蒼天有眼,無怨無悔的愛棋人應該得到眷顧。雲波曾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有一種為俄羅斯文學所特有的沉重、熱狂和悲愴,這個世界對他而言十分遙遠,值得敬佩而無法親近,即使陀氏遙指一個美好的天國,他也會在天國前卻步。我想,雲波這番話表明,在拯救與逍遙之間,他寧取逍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圍棋之間,他選擇圍棋。他的書房取名“瀟湘听弈廬”,這就是明證。跟了魅力無限的“木野狐”上天入地,他也認了。前幾年,我听說雲波決定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很為他高興,但當我得知他將從比較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圍棋時,我還是略感驚訝。作為我國“圍棋博士”第一人,雲波已出了《圍棋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棋行天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兩本著作,還編選了圍棋文化散文集《天圓地方》(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本書是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改就的,與《圍棋與中國文化>>一書形成一種互補的關系。雲波研究圍棋文化,成就斐然。作為比較文學專業的教授,他還在探究19世紀俄國小說中的城市形象。他的才氣和精力確實令人欽佩。
讀了雲波幾本關于圍棋的著作,我也有些感想。圍棋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這不是我的關心所在。對陰陽八卦之類的語言,我歷來敬而遠之。我們如何看待圍棋,也許更值得關注。下棋有助于思維,這應該沒有疑義。誠如範西屏在《桃花泉棋譜》的序言中所說,“心之為物也,日用則日精。”但是我不相信發明或喜愛黑白世界的民族具有特別的智慧。同時也要看到,日本進入江戶時代(1603—1868)後,對圍棋的發展和推廣貢獻最大。打本因坊道策的棋譜就會發現,我國清代國手對圍棋的認識,還稍遜一籌。.座子制加上布局時的陳陳相因大大局限了中國棋手的想像力。現在韓國執圍棋世界牛耳,個中原因是值得我國文化研究認真檢討的。
指南針可用于看風水,也能用于航海。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圍棋的意義和用途是全然相異的。上世紀80年代,我們把圍棋與國運和民族精神聯系起來,個別棋手幾乎成為中華復興的象征。這或許說明,我們當時還是有自卑情結,競技場上每一次勝利,都要做足文章。“弈”本為“小道”,哪里擔負得了政治的重任?圍棋在那時讓人變得太忙太鬧,而古人則說“棋令人閑”。 中國歷史上閑雲野鶴式的逸致經常是文人吟詠的對象,但是“閑”錯了地方也會貽誤大事。在晚清官員中,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名聲還算不錯。我們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中發現,這位大清國的外交官精通“琴棋書畫”四藝,對圍棋尤其痴迷,出任公使後依然在圍棋上耗費大量時間,有時一日下棋達五局之多。我有時覺得他體弱多病,智識活力不足。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他顯得缺乏應有的興趣與熱情,不去描述,無力描述,于是圍棋成了他尋求慰藉的避風港。 當時歐美外交官和傳教士(如已回英國的威妥瑪和還在中國的李提摩太)何等勤奮,他們了解認識異文化的熱情以及對文化交流的實際貢獻遠非圍棋愛好者曾紀澤能比。
我們還要看到,在很多民間高手中,圍棋是設賭的工具,帶來具體好處的手段,古今皆然。本書介紹的《二刻拍案驚奇》中的《小道人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生》就是一個例子。雲波在分析這故事時強調了中國文化“世俗”(他直接用了“俗”字)的一面。與“世俗”的圍棋觀對立的,是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在作品《名人》里所著意刻畫的棋道。1945年8月6日,廣島遭原子彈襲擊,然而核爆炸居然未能中斷橋本宇太郎與岩本薰正在進行中的本因坊決戰。這兩位九段視榮譽高于一切,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他們所表現的或許就是棋道的極致了。我相信,如有必要,兩位棋士還會毫不猶豫地以死來達致生命之美,圍棋之美。雲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國前卻步,棋道也是一種值得敬佩而無法親近的精神嗎?
今秋有望去長沙。我已在想像中做客“瀟湘听弈廬”,茶一杯,棋一局。“一枰坐對,萬慮俱清。”逍遙的人生觀也有可取之處,它比較寬容,頗合人道。然而,要使我們的生活張弛有度,逍遙是不能勝任的。我願意以此與棋友們共勉。
說來慚愧,我的棋齡已近40年。大概是在1966年春節,二哥湄江回杭州建德村探親時教我下棋。後來沈良齋和任旭園兩位老先生先後把他們珍藏的《圍棋》月刊和一副相當不錯的棋具送給我,進一步激發了我的興趣。“文革”“停課鬧革命”期間,我常去杭州柳浪聞鶯公園茶室觀棋,運氣好的時候能看到張禮源、董文淵等名手對弈。我感到不大習慣的是高手下棋時竟然盤外招用得很多,形勢佔優了就會盯住對手唱起京劇《沙家 》中“指導員”的台詞來︰“這時的心情不難體諒。”公園里的棋手,大都自信好強,經常出言不遜。我不敢在這樣的環境下經風雨,于是只能退回建德村,與同伴交手。
我雖然喜歡圍棋,但只是把它視為逞能爭勝的游戲,可以宣泄不良情緒。好友間偶爾失態,可以得到原諒。與陌生人斗氣,是很難為情的。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讀到一篇關于國際象棋的文章,寫得非常有趣。這位英國作者說,棋類運動是心理戰,其殘酷的程度比拳擊有過之而無不及;棋手的一招一式都以侵害、制服對手為目的,種種惡毒的辦法都想得出來,手段高明者實為“像蘇格拉底一般聰明的惡棍”。從9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圍棋刊物愛用一些贊美圍棋並把它與修身養性相聯系的文字。 出于一種自嘲的精神,我向《圍棋》月刊推薦那篇英國散文。這是敗興之舉,雜志編輯部自然不予理睬。由于對棋既愛又恨,加上天資不足,我的棋藝久不見長。每次對弈,下半盤總是松松垮垮,還要搬出唐寅的詩句做借口︰“懶算輸贏信手棋。”其實,不長棋就和蘇格蘭小說家巴里筆下的男孩彼德‧潘拒絕長大一樣,也很快活。
雲波的棋齡,恐怕不及我一半。他學棋晚,進步神速。每次與他對局,我都意識到他的棋力日強。勉強招架之余,我深知自己很快就不是他的對手。對此我倒欣然。蒼天有眼,無怨無悔的愛棋人應該得到眷顧。雲波曾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有一種為俄羅斯文學所特有的沉重、熱狂和悲愴,這個世界對他而言十分遙遠,值得敬佩而無法親近,即使陀氏遙指一個美好的天國,他也會在天國前卻步。我想,雲波這番話表明,在拯救與逍遙之間,他寧取逍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圍棋之間,他選擇圍棋。他的書房取名“瀟湘听弈廬”,這就是明證。跟了魅力無限的“木野狐”上天入地,他也認了。前幾年,我听說雲波決定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很為他高興,但當我得知他將從比較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圍棋時,我還是略感驚訝。作為我國“圍棋博士”第一人,雲波已出了《圍棋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棋行天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兩本著作,還編選了圍棋文化散文集《天圓地方》(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本書是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改就的,與《圍棋與中國文化>>一書形成一種互補的關系。雲波研究圍棋文化,成就斐然。作為比較文學專業的教授,他還在探究19世紀俄國小說中的城市形象。他的才氣和精力確實令人欽佩。
讀了雲波幾本關于圍棋的著作,我也有些感想。圍棋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這不是我的關心所在。對陰陽八卦之類的語言,我歷來敬而遠之。我們如何看待圍棋,也許更值得關注。下棋有助于思維,這應該沒有疑義。誠如範西屏在《桃花泉棋譜》的序言中所說,“心之為物也,日用則日精。”但是我不相信發明或喜愛黑白世界的民族具有特別的智慧。同時也要看到,日本進入江戶時代(1603—1868)後,對圍棋的發展和推廣貢獻最大。打本因坊道策的棋譜就會發現,我國清代國手對圍棋的認識,還稍遜一籌。.座子制加上布局時的陳陳相因大大局限了中國棋手的想像力。現在韓國執圍棋世界牛耳,個中原因是值得我國文化研究認真檢討的。
指南針可用于看風水,也能用于航海。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圍棋的意義和用途是全然相異的。上世紀80年代,我們把圍棋與國運和民族精神聯系起來,個別棋手幾乎成為中華復興的象征。這或許說明,我們當時還是有自卑情結,競技場上每一次勝利,都要做足文章。“弈”本為“小道”,哪里擔負得了政治的重任?圍棋在那時讓人變得太忙太鬧,而古人則說“棋令人閑”。 中國歷史上閑雲野鶴式的逸致經常是文人吟詠的對象,但是“閑”錯了地方也會貽誤大事。在晚清官員中,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名聲還算不錯。我們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中發現,這位大清國的外交官精通“琴棋書畫”四藝,對圍棋尤其痴迷,出任公使後依然在圍棋上耗費大量時間,有時一日下棋達五局之多。我有時覺得他體弱多病,智識活力不足。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他顯得缺乏應有的興趣與熱情,不去描述,無力描述,于是圍棋成了他尋求慰藉的避風港。 當時歐美外交官和傳教士(如已回英國的威妥瑪和還在中國的李提摩太)何等勤奮,他們了解認識異文化的熱情以及對文化交流的實際貢獻遠非圍棋愛好者曾紀澤能比。
我們還要看到,在很多民間高手中,圍棋是設賭的工具,帶來具體好處的手段,古今皆然。本書介紹的《二刻拍案驚奇》中的《小道人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生》就是一個例子。雲波在分析這故事時強調了中國文化“世俗”(他直接用了“俗”字)的一面。與“世俗”的圍棋觀對立的,是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在作品《名人》里所著意刻畫的棋道。1945年8月6日,廣島遭原子彈襲擊,然而核爆炸居然未能中斷橋本宇太郎與岩本薰正在進行中的本因坊決戰。這兩位九段視榮譽高于一切,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他們所表現的或許就是棋道的極致了。我相信,如有必要,兩位棋士還會毫不猶豫地以死來達致生命之美,圍棋之美。雲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國前卻步,棋道也是一種值得敬佩而無法親近的精神嗎?
今秋有望去長沙。我已在想像中做客“瀟湘听弈廬”,茶一杯,棋一局。“一枰坐對,萬慮俱清。”逍遙的人生觀也有可取之處,它比較寬容,頗合人道。然而,要使我們的生活張弛有度,逍遙是不能勝任的。我願意以此與棋友們共勉。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