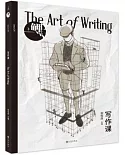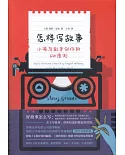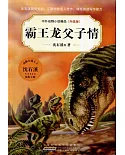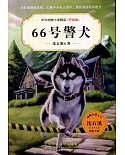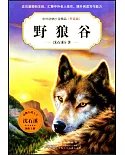首先,賦是一個大文體概念,凡籠而統之地說唐無賦或賦莫盛於唐,都不能切合律、騷、文、駢諸體在中晚唐的實際狀況。作者不憑感覺,而憑實事求是的分析,故其所作的結論,自然可免於以偏概全。其次,在斷代文學研究中最難把握的,是對研究對象的文學史評價。任何時空點上的文學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沒有對文學史的整體性觀照,不可能對斷代文學中的現象作恰如其分的評價。如果僅僅是靠作家作品的數量比較或分析幾個著名作家的作品,就可輕易地作出結論,文學史的研究則未免過於簡單。作者對此,是深有戒惕。本書兼有斷代與專題研究的性質,作者因此選擇了以分體為主的,兼及歷時性研究的方法,「以便能更集中地對某一種體工的發展進行審視。」作者認為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在於:「從歷時性的角度看,辭賦發展到中晚唐已經是各體臻備,而且各種體式的基本特征基本上已經定型」;「唐人在辭賦創作時,心目中也已經有了分體的概念」。
趙俊波,男,1973年生,山西省夏縣人。2004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獲博士學位,導師為項楚教授,專業為中國古代文學。目前專注於辭賦學的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江海學刊》、《蘭州大學學報》等重要期刊上發表《窺陳編以盜竊——論唐代律賦語言雅正特點的形成》、《論晚唐律賦的散體化傾向》、《論晚唐律賦三大家的詠史懷古之作——兼論閩地律賦創作的興盛》等多篇論文。
目錄
緒言
上篇 論中晚唐古賦
第一章 中晚唐人的古賦觀
第一節 中晚唐人對屈宋、揚雄的評價
第二節 中晚唐人古賦觀念散論
第二章 論中晚唐文賦
第一節 文賦的特點
第二節 創作思想的變遷——文賦產生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 文體之間的影響
第四節 文賦的創作歷程
第三章 論中晚唐騷體賦
第一節 論中唐騷體賦(上)
第二節 論中唐騷體賦(下)
第三節 論晚唐騷體賦
第四章 論中晚唐的大賦
第一節 都邑賦的代表作——李庚《兩都賦》
第二節 科技大賦——論盧肇《海潮賦》
第五章 論中晚唐的類賦之文
第一節 中晚唐類賦之文的內容
第二節 滑稽為文——中晚唐類賦之
第六章 論中晚唐駢賦
第一節 論中唐駢賦
第二節 論晚唐駢賦
下篇 論中晚唐律賦
第一章 論中晚唐人的律賦觀
第二章 體制與軍作技巧
第三章 論律賦的價值
第四章 論中唐律賦(上)
第五章 論中唐律賦(下)
第六章 論晚唐律賦(上)
第七章 論晚唐律賦(下)
余論
附錄一:唐賦輯補
附錄二: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上篇 論中晚唐古賦
第一章 中晚唐人的古賦觀
第一節 中晚唐人對屈宋、揚雄的評價
第二節 中晚唐人古賦觀念散論
第二章 論中晚唐文賦
第一節 文賦的特點
第二節 創作思想的變遷——文賦產生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 文體之間的影響
第四節 文賦的創作歷程
第三章 論中晚唐騷體賦
第一節 論中唐騷體賦(上)
第二節 論中唐騷體賦(下)
第三節 論晚唐騷體賦
第四章 論中晚唐的大賦
第一節 都邑賦的代表作——李庚《兩都賦》
第二節 科技大賦——論盧肇《海潮賦》
第五章 論中晚唐的類賦之文
第一節 中晚唐類賦之文的內容
第二節 滑稽為文——中晚唐類賦之
第六章 論中晚唐駢賦
第一節 論中唐駢賦
第二節 論晚唐駢賦
下篇 論中晚唐律賦
第一章 論中晚唐人的律賦觀
第二章 體制與軍作技巧
第三章 論律賦的價值
第四章 論中唐律賦(上)
第五章 論中唐律賦(下)
第六章 論晚唐律賦(上)
第七章 論晚唐律賦(下)
余論
附錄一:唐賦輯補
附錄二: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序
趙俊波的博士論文《中晚唐賦分體研究》,是賦學界期盼已久的研究成果,我為它的即將面世而深感高興。
自20世紀80年代賦學研究復興以來,為厘清賦文學的源頭,學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漢賦,而於漢以后賦的狀況則關注較少。1989年在四川江油召開的全國第二屆辭賦學研討會,會后出版的論文集有文章28篇,其中關乎漢賦的19篇,
魏晉南北朝的3篇,述評性的文章3篇,而與唐有關的研究文章僅有3篇。從90年代起,時任全國賦學會會長的馬積高先生曾經呼吁,賦學研究者在繼續加強漢賦研究而外,學術的視野應該更多的向后延伸。馬先生的呼吁,引起了全國賦學界的充分關注和響應。1998年在南京召開的第四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上,與會代表提交論文47篇,其中關乎楚辭與漢賦的1l篇,而與漢以后辭賦有關的論文已達20篇,其余為辭賦理論與綜述性質的文章。2000年,在福建漳州召開的第五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上,與會代表提交論文58篇,其中與宋玉及漢人賦有關的文章14篇,唐以后3l篇,其余為賦論、綜論及海外賦的研究文章。200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六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上,71篇與會論文中,研究唐及其以后的論文數量更遠遠超過以往。作為新時期以來賦學復興的見證人,筆者的如數家珍,旨在說明漢以后的辭賦,已經被廣泛地納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
然而賦學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態勢,既令人欣喜,也留有遺憾。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以漢以后各代辭賦為研究對象的專著或通史、通論性質的著作僅有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葉幼明《辭賦通論》、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與《辭賦散論》、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曹明綱《賦學概論》、何玉蘭的《宋人賦論及作品散論》、康金聲、李丹《金元辭賦論略》、詹杭倫《清代律賦新論》等,此外竟無一部專刀研究唐賦的著作。以此而言, 《中晚唐賦分體研究》的出版,確有填補空白之功,是我國賦學研究的一大創獲。
拜讀了俊波的大作,又深感它是一部治學態度嚴謹的著作。
在賦學的發展歷史上,歷來有「唐無賦」 (李夢陽)與「詩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王文祿)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作者對此,十分審慎。他一方面說李夢陽「對於現存兩千篇以上的唐賦,完全漠視,一棍子打死,這種態度之荒謬,自不待言」,同時也並不因為唐賦是其研究對象而任其「角色移人」或「情感移人」,對賦莫盛於唐的觀點盲目地表示贊同。作者通過冷靜、客觀地分析,在《緒論》中作出如下結論:中晚唐「律賦的創作在中唐開始走向鼎盛,其作品成為后世律賦創作的楷模」;「文體賦的創作在中晚唐也逐漸興盛起來,」「為后世文賦創作的走向高潮打下了基礎」;「唐代騷體賦的創作在這時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特別是柳宗元的騷體之作」,「堪為屈宋之后騷體文學創作的一個高峰」。仔細地推敲作者所論中晚唐的三種賦體,於律賦而言「鼎盛」,評價甚高;於騷賦則言繼屈宋之后的一個「高峰」,為后來之作的評價留下充分的余地;於文賦則雲「為后世文賦創作的走向高潮打下了基礎」,宋代的文賦因此獲得應有的地位。正因為作者有這樣的認識,他對於賦莫盛於唐的觀點也並不輕易地表態,而只是在《余論》里明白地說:「中晚唐的辭賦創作成就突出,是辭賦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
作者有這樣的態度,我以為十分可取。首先,賦是一個大文體概念,凡籠而統之地說唐無賦或賦莫盛於唐,都不能切合律、騷、文、駢諸體在中晚唐的實際狀況。作者不憑感覺,而憑實事求是的分析,故其所作的結論,自然可免於以偏概全。其次,在斷代文學研究中最難把握的,是對研究對象的文學史評價。任何時空點上的文學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沒有對文學史的整體性觀照,不可能對斷代文學中的現象作恰如其分的評價。如果僅僅是靠作家作品的數量比較或分析幾個著名作家的作品,就可輕易地作出結論,文學史的研究則未免過於簡單。作者對此,是深有戒惕的。他在《余淪》中談到中晚唐人對律賦和文賦的貢獻之后說:「議論說理手段的應用和散體句式的加強以及在這一階段得到發展的文賦、律賦等,都對宋代以后的辭賦以及四六文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值得注目的課題。學術的道路漫長、坎坷,這只能留待以后再做進一步的關注了。」既然唐以后還有許多的文學現象值得研究,作者當然不必急於在自己的階段性成果中得出毫無余地的結論。聯想到當今學術界浮躁之風未泯,以驚世駭俗之論博邀盛名者尚不在個別,如此平實的學風,顯得尤其可貴。讀完大作,作者科學嚴謹的態度,至少對我是很有教益的。
本書作者所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方法源於具體的認識對象,與對象有同一性。方法作為描述與解釋研究對象的手段,其選擇與確認,應與研究對象相適應。就辭賦而論,作為斷代的研究,應以時代為綱,就辭賦的發展演變做綜合的研究;而作為專題的研究,應就辭作分類的研究。本書兼有斷代與專題研究的性質,作者因此選擇了以分體為主的,兼及歷時性研究的方法,「以便能更集中地對某一種體式的發展進行審視。」作者認為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在於:「從歷時性的角度看,辭賦發展到中晚唐已經是各體臻備,而且各種體式的基本特征基本上已經定型」;「唐人在辭賦創作時,心目中也已經有了分體的概念」。即使在「選定了一種體式后,在具體寫作時,賦家們可能並不僅僅拘束於這一種體式的表達手法,」但「總有一種體式是主要的,其它則處於次要的地位」。當然,作者也清醒地認識到,「分類研究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使研究者更能全神貫注地注視某一種特定的對象,從而也就有可能觀察得更為仔細、深入,但同時,它也有很大的弊端。主要是任何事物都不分類則已,
一分類,再用類別去套,那麼總有一些特殊的例外的東西不好歸類」。所以,作者聲言「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有此認識,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盡力顧及全面,以避免方法所帶來的局限。我想,作者所言,也是學術界的同仁常常遇到並必須去解決的難題。20多年前我在做《漢賦通論》課題時,也有類似的困惑。比如我分賦為四言、騷體和散體,在論說各體的源流、特征及流變時,一度因賦體間文體因素的互滲而頗費躊躇。再如漢代一些肩負有其它功用的文類如頌、贊、箴、銘等,也往往采用賦的手法,從而具有了賦的文體特征。是否應該把它們納入賦的研究范疇,也是我無法回避的問題。針對后者,我在書中專設了《漢代頌贊箴銘與賦通體異用>>一章,並在《漢賦今存篇目敘錄》中把不以賦名篇而實為賦體者盡皆錄入,目的只在揭示漢賦中普
遍存在這一現象,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漢賦通論》出版后,賦學界有表贊同者,也有朋友認為我對賦的界定是否過於寬泛。后來出版的兩種全漢賦的總集,除「七體」或古人視作賦體的淮南小山《招隱土》、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解難》等人選外,凡未以賦名篇而實為賦體者如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等,均未人選。這樣的選賦標准,除有上述所說的不便外,即選家自己在論說漢賦時,也無法回避不曾人選的賦篇。所以,對作者在方法問題上的看法,我是深有同感的。
本書對中晚唐辭賦各體的研究,更是多有創獲。
茲以文賦為例。文賦盛於宋代,但它出現在中晚唐並有所發展,學術界對此已有定論。但作者更為關注的,是「文賦何以出現在中晚唐?」「它是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為回答第一個問題,作者對中晚唐的文學思想與創作風氣作了深入細致的考察。作者認為,中晚唐的古文家們「反對駢偶,提倡散化,這種理論當然也適用於作為文體之一的賦體。所以可以說,文賦的創作,正是古文運動的一部分」。同時作者又說:「古文家們有的嚴厲批評駢文,也有的對駢文並不刻意排斥,但在實際創作中,普遍的都是駢散兼行。」「具體到文賦中,便是雖然有散句,但駢對之句也不少。」作者的見解,顯然是符合實際的。文學理論的倡導,並不能完全消解因文學自身發展而形成的時代風氣。即古文健將韓愈,他的文章正是充分吸納了駢文的因素,才能有別於秦漢的古文,而具有新的時代特點。討論文賦形成的原因,是不能棄駢文影響於不顧的。
不僅如此,作者還從中唐人徐浩的《書法論》借來「破體」一說,喻指各文體之間的相互借鑒。在本書的第二章,作者以破體之說為綱,力求全面地分析文賦產生的諸種因素:「駢散不拘、破體為文創作手段的盛行,為賦以諷觀念的牢固及由此而慣用的議論手法還有對秦漢文章的推崇並借鑒,這都是文賦產生的思想基礎;而陸贄駢文、律賦以及詠史懷古詩的盛行,反映了文體之間的互相影響,也對文賦的產生有不小的影響。」顯然,作者所用的「破體說」,無論其觀察角度與研究方法,均有獨到之處;其對文賦原因的分析,也是較為深人和全面的。祝堯等嚴守文體之別,膠柱固瑟,對文賦持論苛刻。作者以破體說批評之,乃是從方法論的層面上動搖其基礎。不僅如此,作者更指出,「破體為文」的現象,古已有之,它「帶來創作觀念或創作思想的解放;它使人們突破『文各有體』的藩籬,在創作中將不同文體的創作方法打通。這種觀念一旦形成,那麼它所發揮的作用就不僅僅局限於詩歌范圍之內,而是擴展到整個文學創作的領域。」以此而論, 「破體為文」乃是推動文體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晚唐人的「以文為賦」以及宋人文賦的成就,只是「破體為文」的成功范例之一。可見作者的認識,已經從文學現象的層面,而深入到文學
的規律性存在了。
寫到這里,筆者突然想到,文賦是一個文體概念;學術界對於何謂文賦,至今還滯留於描述狀態,尚欠簡潔而准確的概念界定。近些年來, 自己對文賦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也曾就文賦的界定作過嘗試,但因對中晚唐賦的情況知之不多,結果自然不可能令人滿意。而作者對中晚唐的文賦,已有很深人的研究,倘以現有的成果為基礎,對其所論的文體性質和文體特征再作抽象、提練,其於文賦概念的界定,應有更大有收獲。
四川與辭賦有不解之緣。蜀中除西漢賦家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而外,尚有東漢李尤、唐代李白、宋代三蘇的賦作,清代李調元的賦論。賦學在蜀中倘無一席之地,的確有愧於先賢。幸而在我供職的學校,有湯炳正、屈守元、王文才等先生,他們不僅於辭賦及辭賦理論的研究頗有建樹,而且培養了一批專事辭賦研究的中青年學人。俊波獲得博士學位后,因為我們這里有幾位研究辭賦的同道,他放棄了去其它學校的打算,我才有幸與他成為同事。我與俊波,接觸不多。性格沉靜,待人謙和,是我與他交往的最初印象;讀書踏實,思維縝密,則是讀他的大作后而獲取的認識。相信作者將以此書的出版為新的起點,不斷有優秀的成果奉獻於我國的賦學界。
是為序。
萬光治
2004年10月於四川師范大學
自20世紀80年代賦學研究復興以來,為厘清賦文學的源頭,學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漢賦,而於漢以后賦的狀況則關注較少。1989年在四川江油召開的全國第二屆辭賦學研討會,會后出版的論文集有文章28篇,其中關乎漢賦的19篇,
魏晉南北朝的3篇,述評性的文章3篇,而與唐有關的研究文章僅有3篇。從90年代起,時任全國賦學會會長的馬積高先生曾經呼吁,賦學研究者在繼續加強漢賦研究而外,學術的視野應該更多的向后延伸。馬先生的呼吁,引起了全國賦學界的充分關注和響應。1998年在南京召開的第四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上,與會代表提交論文47篇,其中關乎楚辭與漢賦的1l篇,而與漢以后辭賦有關的論文已達20篇,其余為辭賦理論與綜述性質的文章。2000年,在福建漳州召開的第五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上,與會代表提交論文58篇,其中與宋玉及漢人賦有關的文章14篇,唐以后3l篇,其余為賦論、綜論及海外賦的研究文章。200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六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上,71篇與會論文中,研究唐及其以后的論文數量更遠遠超過以往。作為新時期以來賦學復興的見證人,筆者的如數家珍,旨在說明漢以后的辭賦,已經被廣泛地納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
然而賦學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態勢,既令人欣喜,也留有遺憾。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以漢以后各代辭賦為研究對象的專著或通史、通論性質的著作僅有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葉幼明《辭賦通論》、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與《辭賦散論》、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曹明綱《賦學概論》、何玉蘭的《宋人賦論及作品散論》、康金聲、李丹《金元辭賦論略》、詹杭倫《清代律賦新論》等,此外竟無一部專刀研究唐賦的著作。以此而言, 《中晚唐賦分體研究》的出版,確有填補空白之功,是我國賦學研究的一大創獲。
拜讀了俊波的大作,又深感它是一部治學態度嚴謹的著作。
在賦學的發展歷史上,歷來有「唐無賦」 (李夢陽)與「詩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王文祿)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作者對此,十分審慎。他一方面說李夢陽「對於現存兩千篇以上的唐賦,完全漠視,一棍子打死,這種態度之荒謬,自不待言」,同時也並不因為唐賦是其研究對象而任其「角色移人」或「情感移人」,對賦莫盛於唐的觀點盲目地表示贊同。作者通過冷靜、客觀地分析,在《緒論》中作出如下結論:中晚唐「律賦的創作在中唐開始走向鼎盛,其作品成為后世律賦創作的楷模」;「文體賦的創作在中晚唐也逐漸興盛起來,」「為后世文賦創作的走向高潮打下了基礎」;「唐代騷體賦的創作在這時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特別是柳宗元的騷體之作」,「堪為屈宋之后騷體文學創作的一個高峰」。仔細地推敲作者所論中晚唐的三種賦體,於律賦而言「鼎盛」,評價甚高;於騷賦則言繼屈宋之后的一個「高峰」,為后來之作的評價留下充分的余地;於文賦則雲「為后世文賦創作的走向高潮打下了基礎」,宋代的文賦因此獲得應有的地位。正因為作者有這樣的認識,他對於賦莫盛於唐的觀點也並不輕易地表態,而只是在《余論》里明白地說:「中晚唐的辭賦創作成就突出,是辭賦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
作者有這樣的態度,我以為十分可取。首先,賦是一個大文體概念,凡籠而統之地說唐無賦或賦莫盛於唐,都不能切合律、騷、文、駢諸體在中晚唐的實際狀況。作者不憑感覺,而憑實事求是的分析,故其所作的結論,自然可免於以偏概全。其次,在斷代文學研究中最難把握的,是對研究對象的文學史評價。任何時空點上的文學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沒有對文學史的整體性觀照,不可能對斷代文學中的現象作恰如其分的評價。如果僅僅是靠作家作品的數量比較或分析幾個著名作家的作品,就可輕易地作出結論,文學史的研究則未免過於簡單。作者對此,是深有戒惕的。他在《余淪》中談到中晚唐人對律賦和文賦的貢獻之后說:「議論說理手段的應用和散體句式的加強以及在這一階段得到發展的文賦、律賦等,都對宋代以后的辭賦以及四六文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也是一個值得注目的課題。學術的道路漫長、坎坷,這只能留待以后再做進一步的關注了。」既然唐以后還有許多的文學現象值得研究,作者當然不必急於在自己的階段性成果中得出毫無余地的結論。聯想到當今學術界浮躁之風未泯,以驚世駭俗之論博邀盛名者尚不在個別,如此平實的學風,顯得尤其可貴。讀完大作,作者科學嚴謹的態度,至少對我是很有教益的。
本書作者所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方法源於具體的認識對象,與對象有同一性。方法作為描述與解釋研究對象的手段,其選擇與確認,應與研究對象相適應。就辭賦而論,作為斷代的研究,應以時代為綱,就辭賦的發展演變做綜合的研究;而作為專題的研究,應就辭作分類的研究。本書兼有斷代與專題研究的性質,作者因此選擇了以分體為主的,兼及歷時性研究的方法,「以便能更集中地對某一種體式的發展進行審視。」作者認為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在於:「從歷時性的角度看,辭賦發展到中晚唐已經是各體臻備,而且各種體式的基本特征基本上已經定型」;「唐人在辭賦創作時,心目中也已經有了分體的概念」。即使在「選定了一種體式后,在具體寫作時,賦家們可能並不僅僅拘束於這一種體式的表達手法,」但「總有一種體式是主要的,其它則處於次要的地位」。當然,作者也清醒地認識到,「分類研究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使研究者更能全神貫注地注視某一種特定的對象,從而也就有可能觀察得更為仔細、深入,但同時,它也有很大的弊端。主要是任何事物都不分類則已,
一分類,再用類別去套,那麼總有一些特殊的例外的東西不好歸類」。所以,作者聲言「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有此認識,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盡力顧及全面,以避免方法所帶來的局限。我想,作者所言,也是學術界的同仁常常遇到並必須去解決的難題。20多年前我在做《漢賦通論》課題時,也有類似的困惑。比如我分賦為四言、騷體和散體,在論說各體的源流、特征及流變時,一度因賦體間文體因素的互滲而頗費躊躇。再如漢代一些肩負有其它功用的文類如頌、贊、箴、銘等,也往往采用賦的手法,從而具有了賦的文體特征。是否應該把它們納入賦的研究范疇,也是我無法回避的問題。針對后者,我在書中專設了《漢代頌贊箴銘與賦通體異用>>一章,並在《漢賦今存篇目敘錄》中把不以賦名篇而實為賦體者盡皆錄入,目的只在揭示漢賦中普
遍存在這一現象,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漢賦通論》出版后,賦學界有表贊同者,也有朋友認為我對賦的界定是否過於寬泛。后來出版的兩種全漢賦的總集,除「七體」或古人視作賦體的淮南小山《招隱土》、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解難》等人選外,凡未以賦名篇而實為賦體者如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等,均未人選。這樣的選賦標准,除有上述所說的不便外,即選家自己在論說漢賦時,也無法回避不曾人選的賦篇。所以,對作者在方法問題上的看法,我是深有同感的。
本書對中晚唐辭賦各體的研究,更是多有創獲。
茲以文賦為例。文賦盛於宋代,但它出現在中晚唐並有所發展,學術界對此已有定論。但作者更為關注的,是「文賦何以出現在中晚唐?」「它是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為回答第一個問題,作者對中晚唐的文學思想與創作風氣作了深入細致的考察。作者認為,中晚唐的古文家們「反對駢偶,提倡散化,這種理論當然也適用於作為文體之一的賦體。所以可以說,文賦的創作,正是古文運動的一部分」。同時作者又說:「古文家們有的嚴厲批評駢文,也有的對駢文並不刻意排斥,但在實際創作中,普遍的都是駢散兼行。」「具體到文賦中,便是雖然有散句,但駢對之句也不少。」作者的見解,顯然是符合實際的。文學理論的倡導,並不能完全消解因文學自身發展而形成的時代風氣。即古文健將韓愈,他的文章正是充分吸納了駢文的因素,才能有別於秦漢的古文,而具有新的時代特點。討論文賦形成的原因,是不能棄駢文影響於不顧的。
不僅如此,作者還從中唐人徐浩的《書法論》借來「破體」一說,喻指各文體之間的相互借鑒。在本書的第二章,作者以破體之說為綱,力求全面地分析文賦產生的諸種因素:「駢散不拘、破體為文創作手段的盛行,為賦以諷觀念的牢固及由此而慣用的議論手法還有對秦漢文章的推崇並借鑒,這都是文賦產生的思想基礎;而陸贄駢文、律賦以及詠史懷古詩的盛行,反映了文體之間的互相影響,也對文賦的產生有不小的影響。」顯然,作者所用的「破體說」,無論其觀察角度與研究方法,均有獨到之處;其對文賦原因的分析,也是較為深人和全面的。祝堯等嚴守文體之別,膠柱固瑟,對文賦持論苛刻。作者以破體說批評之,乃是從方法論的層面上動搖其基礎。不僅如此,作者更指出,「破體為文」的現象,古已有之,它「帶來創作觀念或創作思想的解放;它使人們突破『文各有體』的藩籬,在創作中將不同文體的創作方法打通。這種觀念一旦形成,那麼它所發揮的作用就不僅僅局限於詩歌范圍之內,而是擴展到整個文學創作的領域。」以此而論, 「破體為文」乃是推動文體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晚唐人的「以文為賦」以及宋人文賦的成就,只是「破體為文」的成功范例之一。可見作者的認識,已經從文學現象的層面,而深入到文學
的規律性存在了。
寫到這里,筆者突然想到,文賦是一個文體概念;學術界對於何謂文賦,至今還滯留於描述狀態,尚欠簡潔而准確的概念界定。近些年來, 自己對文賦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也曾就文賦的界定作過嘗試,但因對中晚唐賦的情況知之不多,結果自然不可能令人滿意。而作者對中晚唐的文賦,已有很深人的研究,倘以現有的成果為基礎,對其所論的文體性質和文體特征再作抽象、提練,其於文賦概念的界定,應有更大有收獲。
四川與辭賦有不解之緣。蜀中除西漢賦家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而外,尚有東漢李尤、唐代李白、宋代三蘇的賦作,清代李調元的賦論。賦學在蜀中倘無一席之地,的確有愧於先賢。幸而在我供職的學校,有湯炳正、屈守元、王文才等先生,他們不僅於辭賦及辭賦理論的研究頗有建樹,而且培養了一批專事辭賦研究的中青年學人。俊波獲得博士學位后,因為我們這里有幾位研究辭賦的同道,他放棄了去其它學校的打算,我才有幸與他成為同事。我與俊波,接觸不多。性格沉靜,待人謙和,是我與他交往的最初印象;讀書踏實,思維縝密,則是讀他的大作后而獲取的認識。相信作者將以此書的出版為新的起點,不斷有優秀的成果奉獻於我國的賦學界。
是為序。
萬光治
2004年10月於四川師范大學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