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把太虛的唯識學思想分為「融貫的唯識學」、「新的唯識學」和「應用的唯識學」。「融貫的唯識學」是努力融會唯識學與各派佛學思想的思想方法和致思趨向,涉及到唯識與判教、唯識與《楞嚴》、唯識與《起信》和唯識與法相等問題。太虛不但構造了一個以天台、賢首、三論、唯識、禪、凈、密、律八宗或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三宗為組織結構的大乘佛學體系,合理地安排了法相唯識宗的地位,而且以唯識學的學理詮解《楞嚴經》和《起信論》,疏解唯識理論和《楞嚴》、《起信》學理的矛盾;反對歐陽竟無划分唯識學和法相學的做法,堅持「法相以唯識為宗」的理念。
「新的唯識學」是太虛用現代語言和觀念對唯識思想的詮釋。首先,太虛提出了「新的唯識論」,在批判古今各種唯心論和唯物論哲學的基礎上,對《唯識三十淪》思想作了富有新意的解讀:其次,太虛按由淺人深的次第闡述了虛實,象質、自共、自他、心境、因果、存滅、同異、生死、空有、真幻、凡聖和修證等唯識教法的基本問題;第三,太虛試圖以唯識教理為基本資源,建立一套植根於現觀基礎上的佛陀現實主義哲學體系,從方法論和存在論上系統說明了掌握「真現實」的理論和實踐途徑。
「應用的唯識學」是唯識學思想對各種社會文化問題的回應。太虛繼承了章太炎等人的做法,把唯識學當作具有廣泛適應性的文化詮釋工具和價值判斷體系,用以解讀中國傳統典籍,論證自由與革命,為人間佛教建立心性淪基礎,充分發揮了唯識學的工具價值。
太虛的唯識學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部分,研究太虛的唯識學思想,對中國佛學的綜攝重建,對全面總結和正確認識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自我認識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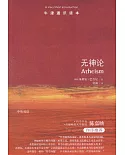
牛津通識讀本:無神論
$167 -

中國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
$407 -

體驗宗教:傳統、挑戰與嬗變
$574 -

中華創世神話六講
$355 -

佛光菜根譚
$260 -

中國神樹圖像研究
$303 -

中國人關於神與靈的觀念
$376 -

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
$345 -

中國神話學百年文論選(上下冊)
$1,556 -

靜思語(中、英、日、西對照典藏版)
$136 -

古代政治神話結構研究--聚焦中國緯書神話與日本記紀神話
$198 -

格物探原
$355 -

粵台客家民間信仰論集
$339 -

中國妖怪大全(精裝珍藏版)
$1,039 -

民間信仰與客家社會
$407 -

海南海神信仰文化研究
$308 -

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
$501 -

佛光山金玉滿堂系列:人間萬事
$292 -

弘一法師講演錄:佛法大意
$156 -

中國史前神話意象
$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