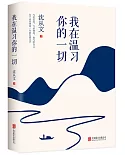此書的體例帶有濃郁的傳奇性色彩,是著者匠心獨運的一種創意,一種嶄新的換位思考模式,一種你來我往的漫談形式,視角獨特新穎,有情有趣,有滋有味。他欲通過自身與「賈寶玉」的會合溝通,試圖創造與讀者——你聊天、漫談、交流的一種氛圍,深入淺出地引導你的心理思路進入古今融會的文境、詩境、心境、意境,向你講論紅學,以達到你與他(讀者與著者)的溝通,與《對話》的溝通,與「賈寶玉」的會合溝通。
本書每一篇對話,都選擇本篇中一個有趣的問題作為題目,絕大多數是本篇的重點,但有些也不盡然。對話的內容大略分為:介紹、《紅樓夢》、人物、詩詞、探佚、曹雪芹、其他等部分,在有關詩詞部分的對話中,特將對話中所涉的相關詩詞、對聯、《紅樓夢》曲文等(均依《石頭記會真》為據)以附錄形式編在本篇對話之後,以便於讀者閱讀、理解。
序
一九五四年上元佳節,我應亡友凌道新兄之邀,訪問北碚西南師院,晤會吳雨僧(宓)先生(注),他為我題詞,並示我昔年陳寅恪先生贈他的論《紅》詩,首聯雲:「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說《夢》更酸辛┅┅」此詩永不能忘。
整整五十年往矣!凌兄、吳老以及當時所見諸賢,俱作古人。而今我卻寫出了這一冊「夢中說夢」的「夢書」,誠非無源之水,種種因緣,可以回溯。
我這「夢中說夢」,與寅恪大師七律原意又不盡同。我是夢見賈公子寶玉,夢中討論紅樓一「夢」,方才撰成此書的。然而,不同之中,也有同處。我為什麽夢見寶玉?其實夢見的人太多了,但總不曾有過這麽豐富的對話。醒後追思,略加編整,成一小帙,也不失為藝林之一枝,紅學之片段。孔子說過:「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人家聖人夢聖人;我這卻算怎麽一回事?方家大雅,哂之詬之,無詞可解。
夢是「縈思結想」的結果,夢寶玉而相談,論《紅樓》以對話,不也是一樁新文異事嗎?!正如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競有一位哥兒,餃玉而生,豈不離奇荒誕?我見一份大報上已然正式提出了荒誕也是美學的這樣一種命題,我不禁如「夢」方醒.「演說」的「演」字,耐人尋味。
夢境迷離恍惚這不一定。我有很多夢真是清清楚楚、明明
切切,連一些細節也不模糊。而且許多境況是平生絕未經過、想過的——那是怎麽出現於夢中的?我自己答不出,別人怕也不易代答。
夢已變為「文」了,以下說「文」。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詩聖老杜名言,原是自謙自檢,是以自古未見異議。但我總想:人是否都如他那麽真能有自知之明?怕是個大問題。每日寫文而不知得失何在的,大有人在。即如老杜自己,能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能知「賦料揚雄敵,詩推子建親」,卻不大見他也自批哪首、哪句寫壞了,出來敗筆了,至少詞不逮意了。所以「寸心」之知,實非輕易可到。
今年七月間,不知緣何,萌念創意要寫此書——最初的念頭,此刻已說不甚清。下筆以後,卻未有阻滯之感,倒是意趣盎然。乘勢而進,不覺積至九九八十一篇。這種選題,如此寫法,是得是失?中間各樣詞句內容,哪為得,何為失?都自思自量而模模糊糊,答不出明確的話來。這證明,我的「寸心」實在不及古賢遠甚!這就應該生愧才是。那麽,為何還要拿給讀者諸君一本連自己也尚無評議的書稿呢?
這一問,卻讓我想起了《詩經》上的兩句:「嚶其嗚矣,求其友聲」。我想與賈寶玉對話,就是為求友聲。寫了拿給諸位讀者,也還是為了一個友聲。
我寫此書,原想能與古人交流,與書中人交流,也與當前同道同好交流。交流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書簡、電話、論文、詩句┅┅都是為了同一目的交流、溝通、感召。否則的話,寸心得失「自知」,就會限於主觀而無「旁觀」之「清」了。
至於許不許與小說人物對話?好像未聞有此禁也。日可日否,正好也是共同談論的文章體例吧。幸惠友聲,恕此嚶嗚。
整整五十年往矣!凌兄、吳老以及當時所見諸賢,俱作古人。而今我卻寫出了這一冊「夢中說夢」的「夢書」,誠非無源之水,種種因緣,可以回溯。
我這「夢中說夢」,與寅恪大師七律原意又不盡同。我是夢見賈公子寶玉,夢中討論紅樓一「夢」,方才撰成此書的。然而,不同之中,也有同處。我為什麽夢見寶玉?其實夢見的人太多了,但總不曾有過這麽豐富的對話。醒後追思,略加編整,成一小帙,也不失為藝林之一枝,紅學之片段。孔子說過:「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人家聖人夢聖人;我這卻算怎麽一回事?方家大雅,哂之詬之,無詞可解。
夢是「縈思結想」的結果,夢寶玉而相談,論《紅樓》以對話,不也是一樁新文異事嗎?!正如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競有一位哥兒,餃玉而生,豈不離奇荒誕?我見一份大報上已然正式提出了荒誕也是美學的這樣一種命題,我不禁如「夢」方醒.「演說」的「演」字,耐人尋味。
夢境迷離恍惚這不一定。我有很多夢真是清清楚楚、明明
切切,連一些細節也不模糊。而且許多境況是平生絕未經過、想過的——那是怎麽出現於夢中的?我自己答不出,別人怕也不易代答。
夢已變為「文」了,以下說「文」。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詩聖老杜名言,原是自謙自檢,是以自古未見異議。但我總想:人是否都如他那麽真能有自知之明?怕是個大問題。每日寫文而不知得失何在的,大有人在。即如老杜自己,能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能知「賦料揚雄敵,詩推子建親」,卻不大見他也自批哪首、哪句寫壞了,出來敗筆了,至少詞不逮意了。所以「寸心」之知,實非輕易可到。
今年七月間,不知緣何,萌念創意要寫此書——最初的念頭,此刻已說不甚清。下筆以後,卻未有阻滯之感,倒是意趣盎然。乘勢而進,不覺積至九九八十一篇。這種選題,如此寫法,是得是失?中間各樣詞句內容,哪為得,何為失?都自思自量而模模糊糊,答不出明確的話來。這證明,我的「寸心」實在不及古賢遠甚!這就應該生愧才是。那麽,為何還要拿給讀者諸君一本連自己也尚無評議的書稿呢?
這一問,卻讓我想起了《詩經》上的兩句:「嚶其嗚矣,求其友聲」。我想與賈寶玉對話,就是為求友聲。寫了拿給諸位讀者,也還是為了一個友聲。
我寫此書,原想能與古人交流,與書中人交流,也與當前同道同好交流。交流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書簡、電話、論文、詩句┅┅都是為了同一目的交流、溝通、感召。否則的話,寸心得失「自知」,就會限於主觀而無「旁觀」之「清」了。
至於許不許與小說人物對話?好像未聞有此禁也。日可日否,正好也是共同談論的文章體例吧。幸惠友聲,恕此嚶嗚。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