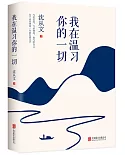內容簡介
「生活之中惟有胡思亂想才是被作者真正占有的,因為,作者可以真正自由地支配它們。作者還很願意將這些胡思亂想記錄下來,變成文字,雖然作者知道文字有著特殊的權利,但作者並不是想獲得權利而去書寫文字,其實,作者僅僅是想讓肉體在胡思亂想和轉變文字之間去體會生理性的快感。惟獨這種特殊之生理快感,才能夠使作者暫時忘卻作者還「活著」這一始終不能被作者確定的事實。由於不能確定的緣故,轉過來,又催促著作者的胡思亂想繼續繁殖而變得愈加地模糊與恍惚,轉化為文字,也就變得像酒後的腳步有些踉蹌、醉意、龐雜。文字在作者是很不重要的,僅僅是用以承載生命的方式,以便於讓文字來活受罪而讓自己從這龐雜的莫名亂想中脫身而出。但是出到哪里去,作者又是很糊塗的。於是就以為思想原本就應該是龐雜的,不雜,何以成力思想呢?做學問是否要雜,作者就不知道了,因為作者不大會做學問。舉凡做起來,頭,一定是要發昏的。做學問需要系統化,大抵如此,作者偏偏是最不善於系統與條理的。作者的昏頭之病可能就來源於此。」
序
我喝酒學哲學的小酒鋪靠近北京站,南小街口子,路西廁所斜對面,挨着一家滿姓涮羊肉飯館不遠。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辭職賦閑,每天下午來此,先買上一包花生米,再來三扎啤酒,盤腿坐在馬路邊上,一手拿着《思想錄》一手款款地商起了大酒杯。來這間小酒鋪喝酒的,盡是些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偶爾有些模樣體面的夾雜其間。酒客們養成了生物性習慣,天天廝混於此,似乎一個個人生沒有別的目的,天生為酒而來。我在這喝酒朋友中看我的書,聽着他們的語言,記不住書中講了什麼,卻不曾忘了那些臟話和葷話,我后來聊起哲學始終帶有一種暈乎乎的醉意以及販夫走卒式的俚俗與親切。我學哲學似乎也是沒有目的的,反而認定了,喝酒與哲學,左不過都是為了『昏頭』這樣一個目的。
我這種學習方式持續了好幾年,直到有一天覺得自己腦子出問題了,整日魔道着,什麼事情也不想做,專門找一些沒用的問題來折磨自己,比如人為什麼要活着、女人和男人的關系為什麼這樣復雜,等等諸如此類的不是問題的問題。
腦袋里想着老子、帕斯卡爾、叔本華的句子,手上端着大塑料桶啤酒杯,眼前晃盪着一幫子蹬三輪、賣羊肉、游手好閑人等,路邊、喧囂、打鬧,我學習哲學從一開始就串了味道,再無正而八經的可能。況且我學哲學絕無目的,不為論文、不為學位、也不為職稱,總之是什麼都不為,活着無聊,想找到一種生活方式來打發無聊。
當時有不少人皆奇怪,這家伙沒有工作,生計亦無着落,但偏偏能夠坐在馬路邊自由地喝着、玩着、讀着,就像是二流子、老混混。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混混,大抵就是吧。作為社會上無業游民,真正很地道。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家伙瞪大了眼睛驚愕地問:『聽說你什麼事情也不做?整日閑着,也不去為社會做一點貢獻什麼的?』我老老實實地說『是啊』。那人於是就為之惋惜,臨了還說些年紀輕輕之類的話。
我后來習慣了這樣的眼神與惋惜,可我確實無以為自己辯角發,因為,一個整日昏頭昏腦的家伙,怎麼可能對這些頭腦清晰的家伙來表明自己的意圖呢?況且所要表明的意圖原本是不存在的。我連自己哲學容易讓人昏頭。我發過這昏。通常是讀起哲學書來頭就發昏,頭昏之后愈發要去談,讀而更昏,可見我這發昏是昏聵到了極點。我於是就采取惡治,昏了頭而去喝酒,昏於哲學又昏於酒,於是這酒,喝起來經濟實惠,耗費不了多少酒精就能夠事半功倍地讓我的中柩神經進入了麻痹俗仙的境界。我終於把自己培養出一個良好的習慣,情不能禁地用哲學態度去品酒,然后用昏醉囈語解釋哲學,最終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小發現,發酒昏時,去看哲學,覺得世間所有哲學說的都是昏話,而酒后醉話大都充滿了哲理。舒坦於酒精也就是舒坦於哲學,反之亦然,活着沒事做去搞哲學,生要把腦袋給弄得昏昏沉沉,但在其中可以體味到了酒精作用而淡化了哲學意味。
為什麼要活着都不清楚,用我這昏沉的腦袋去為社會做貢獻,豈不將危害於社會嗎?我就想自我封閉起來,或許對於社會更為有益,酒精與哲學,可用來危害自己而不會去殃及他人。可惜我的無業游民生活,竄上了氣勢洶洶賓味道。
我經常是喝多了醉得迷里馬糊,在馬路邊看着往來人流眼花繚亂,腦細胞運動起來卻把哲學混淆於宗教,復又把宗教混淆於藝術。藝術卻是真正的游戲,我就整日在這些方面去胡思亂想了。一切思維皆了無結果,惟獨喝酒有了結果,我終於進入了酗酒狀態。身子輕飄飄的,騰雲駕霧,決然不問人間之事。記憶力大為減弱,腦袋不大好使喚了。更為麻煩的是我開始失眠,長期失眠有可能是精神系統出問題的征兆,我知道終於把自己給折騰得魔魔道道了。耗了八年時間,我得到了原先不知道會怎麼樣的結果。
哲學弄壞了我腦子,而且,我很是服輸地認識到我天生就不是學哲學的料。學習哲學應該冷漠無情,好似看待一堆抽象的數學方程式,僅僅從數字與結構上去理解,也就不會傷元動氣了。學哲學而傷了元氣,不得不依靠胡思亂想過日子。
我住在大黃庄,城市與縣城的交匯處,這里有一個標志,通縣界碑。距離界碑不遠是一座座紅色六層板磚樓房,樓房群中有一間是我的住處。我整日就在這房子里胡思亂想,然后我再把胡思亂想寫下來,以為能夠將胡思亂想寫下來就是我人生的出路。我靠着胡思亂想過日子,幾乎,我的人生專業就是胡思亂想。前一陣子我因故卧床不能起,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過日子,這下可好,除了胡思亂想別無其他能耐了,完全可以名副其實而又理直氣壯地整日價地胡思亂想了。
……
我這種學習方式持續了好幾年,直到有一天覺得自己腦子出問題了,整日魔道着,什麼事情也不想做,專門找一些沒用的問題來折磨自己,比如人為什麼要活着、女人和男人的關系為什麼這樣復雜,等等諸如此類的不是問題的問題。
腦袋里想着老子、帕斯卡爾、叔本華的句子,手上端着大塑料桶啤酒杯,眼前晃盪着一幫子蹬三輪、賣羊肉、游手好閑人等,路邊、喧囂、打鬧,我學習哲學從一開始就串了味道,再無正而八經的可能。況且我學哲學絕無目的,不為論文、不為學位、也不為職稱,總之是什麼都不為,活着無聊,想找到一種生活方式來打發無聊。
當時有不少人皆奇怪,這家伙沒有工作,生計亦無着落,但偏偏能夠坐在馬路邊自由地喝着、玩着、讀着,就像是二流子、老混混。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混混,大抵就是吧。作為社會上無業游民,真正很地道。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家伙瞪大了眼睛驚愕地問:『聽說你什麼事情也不做?整日閑着,也不去為社會做一點貢獻什麼的?』我老老實實地說『是啊』。那人於是就為之惋惜,臨了還說些年紀輕輕之類的話。
我后來習慣了這樣的眼神與惋惜,可我確實無以為自己辯角發,因為,一個整日昏頭昏腦的家伙,怎麼可能對這些頭腦清晰的家伙來表明自己的意圖呢?況且所要表明的意圖原本是不存在的。我連自己哲學容易讓人昏頭。我發過這昏。通常是讀起哲學書來頭就發昏,頭昏之后愈發要去談,讀而更昏,可見我這發昏是昏聵到了極點。我於是就采取惡治,昏了頭而去喝酒,昏於哲學又昏於酒,於是這酒,喝起來經濟實惠,耗費不了多少酒精就能夠事半功倍地讓我的中柩神經進入了麻痹俗仙的境界。我終於把自己培養出一個良好的習慣,情不能禁地用哲學態度去品酒,然后用昏醉囈語解釋哲學,最終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小發現,發酒昏時,去看哲學,覺得世間所有哲學說的都是昏話,而酒后醉話大都充滿了哲理。舒坦於酒精也就是舒坦於哲學,反之亦然,活着沒事做去搞哲學,生要把腦袋給弄得昏昏沉沉,但在其中可以體味到了酒精作用而淡化了哲學意味。
為什麼要活着都不清楚,用我這昏沉的腦袋去為社會做貢獻,豈不將危害於社會嗎?我就想自我封閉起來,或許對於社會更為有益,酒精與哲學,可用來危害自己而不會去殃及他人。可惜我的無業游民生活,竄上了氣勢洶洶賓味道。
我經常是喝多了醉得迷里馬糊,在馬路邊看着往來人流眼花繚亂,腦細胞運動起來卻把哲學混淆於宗教,復又把宗教混淆於藝術。藝術卻是真正的游戲,我就整日在這些方面去胡思亂想了。一切思維皆了無結果,惟獨喝酒有了結果,我終於進入了酗酒狀態。身子輕飄飄的,騰雲駕霧,決然不問人間之事。記憶力大為減弱,腦袋不大好使喚了。更為麻煩的是我開始失眠,長期失眠有可能是精神系統出問題的征兆,我知道終於把自己給折騰得魔魔道道了。耗了八年時間,我得到了原先不知道會怎麼樣的結果。
哲學弄壞了我腦子,而且,我很是服輸地認識到我天生就不是學哲學的料。學習哲學應該冷漠無情,好似看待一堆抽象的數學方程式,僅僅從數字與結構上去理解,也就不會傷元動氣了。學哲學而傷了元氣,不得不依靠胡思亂想過日子。
我住在大黃庄,城市與縣城的交匯處,這里有一個標志,通縣界碑。距離界碑不遠是一座座紅色六層板磚樓房,樓房群中有一間是我的住處。我整日就在這房子里胡思亂想,然后我再把胡思亂想寫下來,以為能夠將胡思亂想寫下來就是我人生的出路。我靠着胡思亂想過日子,幾乎,我的人生專業就是胡思亂想。前一陣子我因故卧床不能起,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過日子,這下可好,除了胡思亂想別無其他能耐了,完全可以名副其實而又理直氣壯地整日價地胡思亂想了。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8折$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