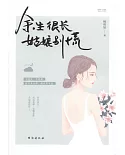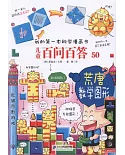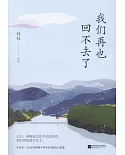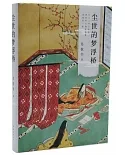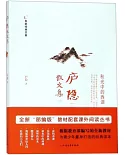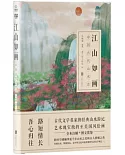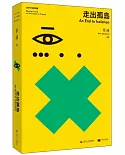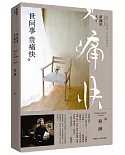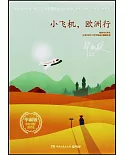本書是我社出版的中國文學鑒賞辭典系列之一。
散文是智慧的結晶,哲理是升化,歷史的記錄。它「是在一個民族擺脫了自然純朴狀態而進入更為自覺的人為的文明生活的時候」出現的,是人類進入文明期的一個顯著標志。
本書是共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八十多年來的散文14篇,其中也包括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華裔作家的作品。本書正文目次,按作者生年先後為序:同一作者的多篇作品,一般按作品寫作或發表時間先後排列。本書采用簡體字,在可能產生歧義時,酌用繁體字或異體字。
序
現代散文發軔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當時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置身於時代前列的啟蒙思想家們憂心如焚,他們翹首異域,振臂高呼:「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擴大了人們的視野。正是在反對封建道德、崇尚個性自由、追求民主科學等新思潮的推動下,現代白話散文很快脫穎而出。最早也最著名的是《新青年》雜志所開辟的「隨感錄」專欄,接連發表了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人揮灑自如、大小由之的文章,不僅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而且開日後雜文創作之先河,影響極為深遠。稍後,與重在議論的「隨感錄」不同,抒情散文作為現代散文的主干開始產生,「五四」以來第一批散文家不時有佳作問世,令人耳目一新,進一步顯示了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的實績。
萬事開頭難。現代散文的發展並非一馬平川,它既要破除封建守舊勢力的節節抵抗,又要在創作實踐中正確解決繼承古典遺產和借鑒外國經驗的問題,進而確立嶄新的散文文體觀。
封建守舊勢力為了實現文化專制主義,長期維持少數人壟斷書面語言的局面,拼命攻擊白話文「鄙俚淺陋」,是「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林紓:《致蔡鶴卿太史書》),登不了大雅之堂。對於這些歪理謬說,白話文運動倡導者自然不會輕易放過,胡適就曾巧妙而有力地申述了古今語言的巨大變化:「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嘗試集)初版自序》)可見白話代替文言,實在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誰都知道,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封建衛道士所以抱住「文言」的外殼不放,目的正在於「尊孔」、「載道」,替聖人「立言」。他們視腐朽為神奇,不敢越古人的雷池一步,只知道依樣畫葫蘆地大寫沒有靈魂、空洞無物的「仿古文」,這就不能不同樣激起啟蒙思想家和現代散文作家的強烈反對。胡適倡導「有什麽話,說什麽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劉半農堅持「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我的文學改良觀》),周作人主張寫「即興」的「言志」的散文,反對寫「賦得」的「載道」的文章(《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可以說都是有的放矢,令人信服。
這里有一個如何對待和繼承古典散文遺產的問題。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向來以詩文為正宗,視小說、戲劇為不入流。散文創作歷史悠久,佳作如雲,上溯先秦諸子,中經唐宋八大家,晚迄明清小品,無不爭奇斗艷,各擅勝場。從更加長遠和根本的觀點來分析,現代散文自然離不開對優秀古典散文的傳承、融鑄和發展,何況最早的一批散文名家又都是學貫中西、精通古今的飽學之士。問題在於:第一,必須置於當時的特殊時代背景下來看待「繼承」的問題,不能把「繼承」看作是一個靜止的孤立的過程。在「尊孔復古」甚囂塵上,八股流毒遠未肅清,人民大眾對國外情況知之甚少的大背景下,對古典散文的取舍、揚棄必然著眼於主要方面,以「民主」、「科學」的呼聲為依歸,當時不少作家推崇晚明小品便是一例。第二,必須深入理解「繼承」的多層次涵義,諸凡「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愛國情結,情景交融、物我一體的審美情趣,自然渾成、簡練含蓄的民族風格,自由靈活的漢語表達方式,等等,均是對散文發展起著長期作用的主要因素,必然會或早或遲地進入現代散文家的視野,並潛移默化地產生效果。證之以散文後來的發展,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如舍棄以上這一切,只注意章句、「義法」、典故之類,那就會僅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第三,盡管我國散文歷史悠久,但傳統所謂散文是指與韻文、駢文相對的散行體文字,范圍極廣,大量的哲學、歷史文獻在其中占據著主要的位置。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推進新文學的健康發展,必須確立新的散文文體觀。有鑒於此,劉半農首創「文學散文」之說。他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作了如下的區分:各種科學論文「系文字而非文學」;新聞通訊,如「普通紀事可用文字,描寫人情風俗當用文學」;私人之日記信札,一般實用文字,然如游歷時之日記,亦可「涉及文學」,等等。劉半農上述區分,看似縮小了「散文」的領地,其實是夯實了「文學散文」的基礎,為現代散文的發展進而超越古代散文創造了條件。稍後,周作人提倡「美文」不遺余力,極大地提高了白話抒情散文的地位,他還不顧正統古文家的反對,從古典散文遺產中挑出「獨抒性靈」的明代小品,用來和「五四」時期自由、活潑的思潮相接軌,表現了他在「繼承,,方面的創造性。
在對我國古代散文遺產作出新的審視、評價的同時,西方的文學理論和創作經驗,又不斷輸入進來。在散文方面,要算英國的Essay(現通譯為「隨筆」)對我國影響最大。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書,對Essay曾作過如下生動的介紹:「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閑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便是Essay。」不言而喻,這種散文樣式具有親切、靈活、從容等特性,切合「五四」時期崇尚平等、自由的趨勢和風尚,自然會受到散又作者的注意和歡迎。
┅┅
萬事開頭難。現代散文的發展並非一馬平川,它既要破除封建守舊勢力的節節抵抗,又要在創作實踐中正確解決繼承古典遺產和借鑒外國經驗的問題,進而確立嶄新的散文文體觀。
封建守舊勢力為了實現文化專制主義,長期維持少數人壟斷書面語言的局面,拼命攻擊白話文「鄙俚淺陋」,是「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林紓:《致蔡鶴卿太史書》),登不了大雅之堂。對於這些歪理謬說,白話文運動倡導者自然不會輕易放過,胡適就曾巧妙而有力地申述了古今語言的巨大變化:「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嘗試集)初版自序》)可見白話代替文言,實在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誰都知道,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封建衛道士所以抱住「文言」的外殼不放,目的正在於「尊孔」、「載道」,替聖人「立言」。他們視腐朽為神奇,不敢越古人的雷池一步,只知道依樣畫葫蘆地大寫沒有靈魂、空洞無物的「仿古文」,這就不能不同樣激起啟蒙思想家和現代散文作家的強烈反對。胡適倡導「有什麽話,說什麽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劉半農堅持「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我的文學改良觀》),周作人主張寫「即興」的「言志」的散文,反對寫「賦得」的「載道」的文章(《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可以說都是有的放矢,令人信服。
這里有一個如何對待和繼承古典散文遺產的問題。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向來以詩文為正宗,視小說、戲劇為不入流。散文創作歷史悠久,佳作如雲,上溯先秦諸子,中經唐宋八大家,晚迄明清小品,無不爭奇斗艷,各擅勝場。從更加長遠和根本的觀點來分析,現代散文自然離不開對優秀古典散文的傳承、融鑄和發展,何況最早的一批散文名家又都是學貫中西、精通古今的飽學之士。問題在於:第一,必須置於當時的特殊時代背景下來看待「繼承」的問題,不能把「繼承」看作是一個靜止的孤立的過程。在「尊孔復古」甚囂塵上,八股流毒遠未肅清,人民大眾對國外情況知之甚少的大背景下,對古典散文的取舍、揚棄必然著眼於主要方面,以「民主」、「科學」的呼聲為依歸,當時不少作家推崇晚明小品便是一例。第二,必須深入理解「繼承」的多層次涵義,諸凡「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愛國情結,情景交融、物我一體的審美情趣,自然渾成、簡練含蓄的民族風格,自由靈活的漢語表達方式,等等,均是對散文發展起著長期作用的主要因素,必然會或早或遲地進入現代散文家的視野,並潛移默化地產生效果。證之以散文後來的發展,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如舍棄以上這一切,只注意章句、「義法」、典故之類,那就會僅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第三,盡管我國散文歷史悠久,但傳統所謂散文是指與韻文、駢文相對的散行體文字,范圍極廣,大量的哲學、歷史文獻在其中占據著主要的位置。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推進新文學的健康發展,必須確立新的散文文體觀。有鑒於此,劉半農首創「文學散文」之說。他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作了如下的區分:各種科學論文「系文字而非文學」;新聞通訊,如「普通紀事可用文字,描寫人情風俗當用文學」;私人之日記信札,一般實用文字,然如游歷時之日記,亦可「涉及文學」,等等。劉半農上述區分,看似縮小了「散文」的領地,其實是夯實了「文學散文」的基礎,為現代散文的發展進而超越古代散文創造了條件。稍後,周作人提倡「美文」不遺余力,極大地提高了白話抒情散文的地位,他還不顧正統古文家的反對,從古典散文遺產中挑出「獨抒性靈」的明代小品,用來和「五四」時期自由、活潑的思潮相接軌,表現了他在「繼承,,方面的創造性。
在對我國古代散文遺產作出新的審視、評價的同時,西方的文學理論和創作經驗,又不斷輸入進來。在散文方面,要算英國的Essay(現通譯為「隨筆」)對我國影響最大。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書,對Essay曾作過如下生動的介紹:「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閑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便是Essay。」不言而喻,這種散文樣式具有親切、靈活、從容等特性,切合「五四」時期崇尚平等、自由的趨勢和風尚,自然會受到散又作者的注意和歡迎。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