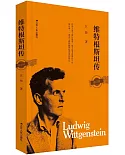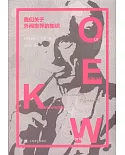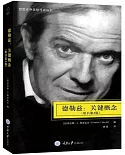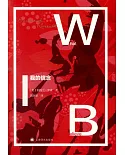自先秦至晚明,漢語思想有過兩次與異域思想的歷史性相遇(佛學和秦西實學及天主實學)。清末以來,學界孜孜以求認識西方思想,乃漢語思想與異域思想歷史性相遇的第三波。
僅僅百余年的西方學典漢譯歷史,可以說已經歷了三個階段。以嚴復譯秦西政法諸書至本世紀四十年代,為第一階段。尤其二十年代以來,眾多現代知識人憑着自己的興趣翻譯西方學典,出現了不少出色的翻譯大家。但西洋思想圖景仍然顯得零碎,學界尚缺乏對西方思想傳統的整體性認識,一些譯家的熱情奉獻給了不那麼經典的西方作品。
第二階段,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新中國政府規范翻譯西典事業,整編四十年代遺稿,制訂新的選題,幾十年來寸累銖積,形成了振裘挈領的「漢譯學術名著」體系。然而,這西典體系的設計受當時學界眼光限制,亦為思想史界的教條主義所扼,雖開牖后學之功萬不容沒,仍然不能說反映了西方思想大傳統。「思想不外義理和制度兩端(康有為語)」。涉及義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大家的基本著作,未有譯成漢語者,豈止在少數?問題仍然在於,學界對西方思想傳統的整體性認識,迄今讓人感到不踏實。比較而言,國人認識近、現代思想的熱情遠大於認識西方古典思想。原因似乎不難理解:國人認識西方思想的熱情,主要是現代強國夢推動的。如此認識心態,本來就是問題。所謂「西方名著」的清單難道不需要通盤重擬?
八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學人創設「現代西方學術文庫」,致力晚近幾十年歐美學界整理學故的學術成果,企求以西方現代經典入手重建西方思想漢譯學典體系,反映了學界通盤重新認識西方思想傳統的渴求。遺憾的是,這一漢語學界的重大學術戰略因時光流變而中斷。
九十年代以來,西學翻譯蔚成風氣,各種翻譯「叢書」迭出,熱情引進種種人文一社會科學新知。可是,正如科學不等於技術,思想也不等於科學。無論學界引進了多少「前沿」的社會學、政治學、法學之類的社會科學,仍與歐洲思想大傳統了不相干。如果選題設計隨事補苴、以求適時,只能徒令學界轟拾西學唾余,以支庶續大統。緊跟當下「主義」流變,務競新奇、不成條貫,重新認識西方思想大傳統的未盡之業難以庚續,仍有賴悉心疏理傳統源流。
西方思想傳統的要典即便譯成了漢語,對西方思想傳統的整體性認識問題並不等於就解決了。就已經有的經典翻譯而言,學界的讀解經常吃夾生飯——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原因之一是,學界缺乏對西方思想典籍具有深度解釋的翻譯積累。僅僅翻譯原典,顯然不夠,也需要精當挑選、翻譯對原典的解釋性要籍。
晚近十年,不能說譯界不熱心翻譯思想研究論著,甚至不乏龐大譯叢之舉。問題是,如果對西方思想大傳統的理解尚有問題,如何可能恰切選擇研究論著?再有,業界對西方思想史的關注,基本上還停留在通史一類或對思想大家的通論介紹性評估,缺乏有深度解釋的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一般認識水平,對西方思想傳統的整體性認識就不可能長進。
設計這套「西方思想家研究系列」,旨在推進學界對西方思想大傳統的理解。首先,注重選擇思想大家或有影響的思想史家的研究,力求形成名家解釋名家的研究系統。形式上以個人和專著為主,也兼及思想史上的小傳統和文集,希望在認識西方思想傳統的路上留下堅實的足印。編譯者念漢譯西典前業未畢,亦知譯業安有不百年積之而可一朝有成者耶。
劉小楓1999年10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