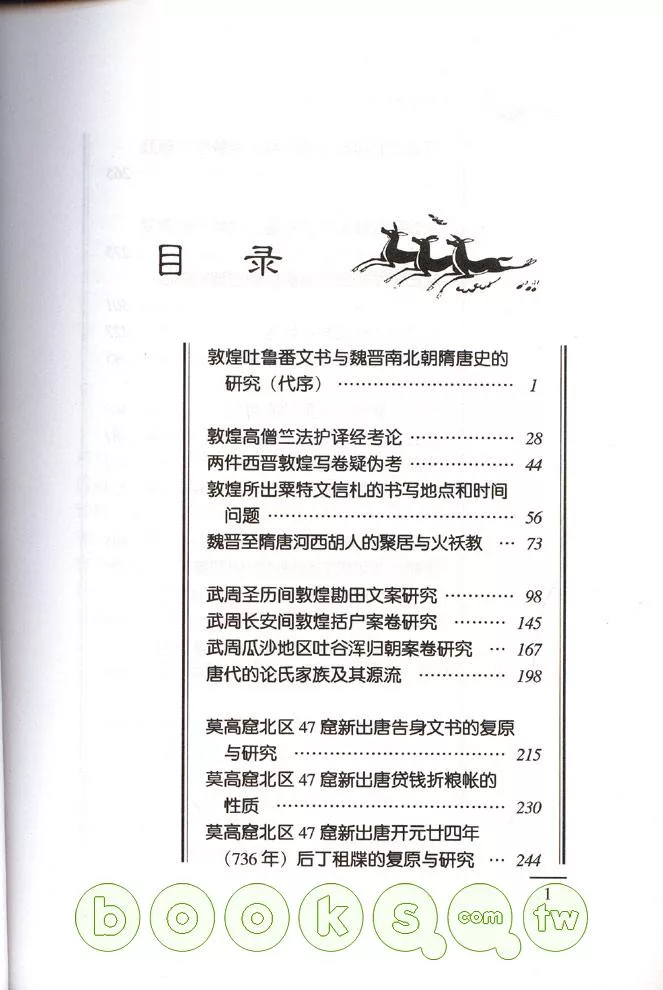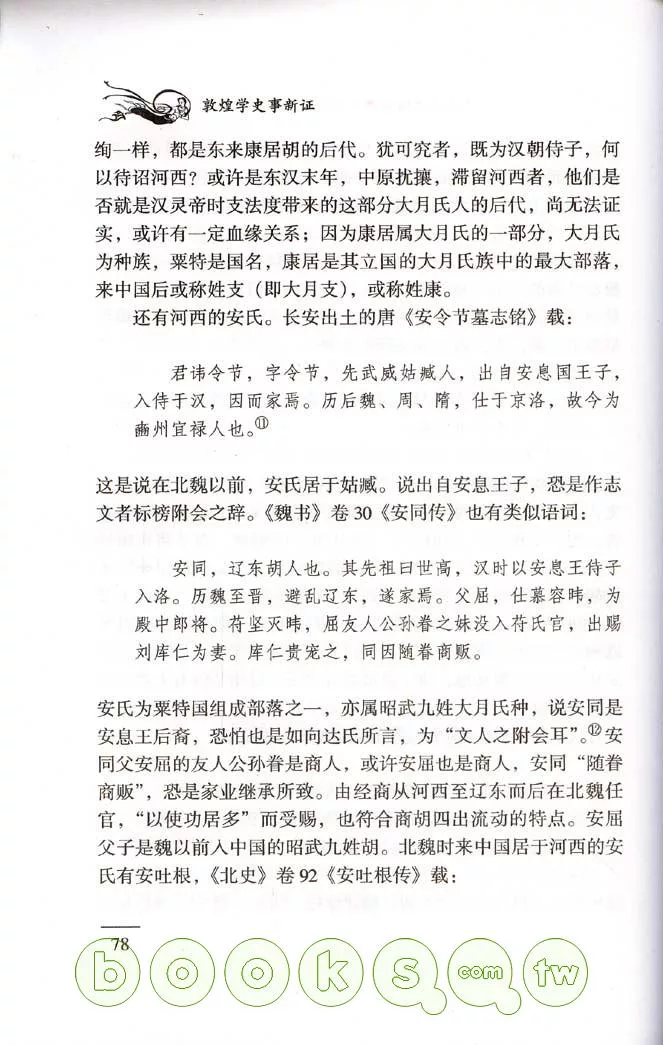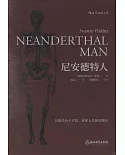本書收入25篇論文,作者利用敦煌文書對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歷史進行了探索。
該書是作者多年在敦煌史學方面研究的一本論文集,全書收集了作者的25篇文章,涉及敦煌學中有關魏晉的一些史實問題,吐魯番所出敦煌案卷對唐代武周時期歷史的反映,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新發現的一些唐代社會文書殘片所做的綴合、復原和研究,唐五代敦煌鄉里、軍鎮、交通等歷史地理問題所做的論證等。
作者簡介︰
陳國燦,武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參與編纂《吐魯番出土文書》,著有《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唐代的經濟社會》。主編《全唐文職官從考》、《民族融合‧締造中華》等。在海內外學術期刊或論集中發表《唐乾陵石人餃名研究》、《從吐魯番出土的質庫帳看唐代的質庫制度》、《烏海市所初西夏某參合政事碑考釋》等學術論文九十余篇。
目錄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代序)
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論
兩件西晉敦煌寫卷疑偽考
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書寫地點和時間問題
魏晉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與火教
武周聖歷歷間敦煌勘田文案研究
武周長安間敦煌括戶案卷研究
武周瓜沙地區吐谷渾歸朝案卷研究
唐代的論氏家族及其源流
英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告身文書的復原與研究
英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貸錢折糧賬的性質
莫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開元廿四年(736年)後丁租牒的復原與研究
英高窟北窟新發現的兩年唐煌戶籍殘片
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五代地子的演變
從歸義軍受田簿看唐後期的請田制度
敦煌所出諸借契年代考
西夏天慶間典當殘契的復原
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
唐五代瓜沙歸義軍軍鎮的演變
唐瓜沙途程與懸泉鎮
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
安史亂後的唐二庭四鎮
唐朝呈蕃陷落沙州城的時間問題
八、九世紀間唐朝西州統治權的轉移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
後記
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論
兩件西晉敦煌寫卷疑偽考
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書寫地點和時間問題
魏晉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與火教
武周聖歷歷間敦煌勘田文案研究
武周長安間敦煌括戶案卷研究
武周瓜沙地區吐谷渾歸朝案卷研究
唐代的論氏家族及其源流
英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告身文書的復原與研究
英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貸錢折糧賬的性質
莫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開元廿四年(736年)後丁租牒的復原與研究
英高窟北窟新發現的兩年唐煌戶籍殘片
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五代地子的演變
從歸義軍受田簿看唐後期的請田制度
敦煌所出諸借契年代考
西夏天慶間典當殘契的復原
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
唐五代瓜沙歸義軍軍鎮的演變
唐瓜沙途程與懸泉鎮
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
安史亂後的唐二庭四鎮
唐朝呈蕃陷落沙州城的時間問題
八、九世紀間唐朝西州統治權的轉移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
後記
序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社會狀況,在史籍上固然記述不少,可是,在對一些問題進行具體認識時,又常有情況不明之感。或因隱諱不載,或因語焉不詳,妨礙了對當時社會的深入認識。這種情形,促使著學者們對當時人留下來的地上地下遺物進行搜集和發掘,除了大批魏晉至隋唐的實物和碑刻外,還有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的當時人留下的大批紙質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資料,今天統稱為敦煌、吐魯番文書,而對這些文書內容的探索,直接關系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
一、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特點及作用
我國甘肅省的敦煌和新疆的吐魯番,在魏晉時期,分別設置為敦煌郡和高昌郡,在唐代又分屬于沙州和西州,是當時中國通向西域的門戶。因而在它的地上地下,也留存有許多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物、遺書。加之西北地區氣候干燥,水分稀少,使得這些遺物、遺書,常保存逾千年而不腐,它們或長眠于眾多的墓葬中;或被當做神明供奉在寺廟里;或密封在石窟藏經洞內。長帝國主義的探險家們便將這些珍貴的遺物、遺書一批一批地劫往世界各地。
1895年,當俄國探險隊羅波洛夫斯基在吐魯番古寺廟遺址里,褻瀆神靈,劫走古寫本經卷後,俄、德、英、日等國的探險家們陸續來到盆地,掠走了大批漢文和民族文字的寫本文書。自1912年起,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英國的斯坦因又連續對吐魯番阿斯塔那的古墓群進行了盜掘,劫走大批十六國至唐代的墓葬紙質文書。在敦煌的莫高窟,自1900年道士王圓策發現藏經洞內四萬多卷古寫本文書後,立即引起帝國主義的垂涎,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等又相繼從這里劫走了三萬余卷。我國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就這樣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如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藏的“斯坦因文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伯希和文書”、俄羅斯聖彼得堡(前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的“敦煌特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吐魯番文書”、日本京都龍谷大學藏的“大谷文書”等,都是來自我國敦煌、吐魯番的古文書。
這些古文書雖然大部分是西晉到唐宋時的寫經,但也有一小部分屬于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始文獻,學術價值極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出土有紀年的最早社會文書是《西涼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現藏倫敦,編號為S.113),最晚的是寫有“宋咸平五年壬寅歲(1002年)五月十五日記”的寫經(現藏俄羅斯,編號為IX1696),就整個敦煌所出社會生活文書而言,還是以晚唐五代宋初文書居多。在吐魯番文書中,最早者有吐峪溝寺廟遺址所出寫有“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殘卷(現藏日本),最晚者有元代的文書,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善斌賣身契》三種。整個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國至高昌國和唐前期的文書為大宗。除此以外,在敦煌和吐魯番出的文書中,還有一些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和回鶻文的文書。由于這眾多的文書在本世紀初就被劫往國外,以致在舊中國的國內學術界欲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也無從大力進行,相反,在有些國家里,一些漢學家們結合中國的歷史,卻發表了不少對文書的研究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的直接關注下,一些流往國外的文書相繼被攝制回來,學術界對敦煌文書也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編目,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魯番阿斯塔那村和哈拉和卓古墓地,進行了十余次的發掘,出土了幾近萬片的漢文文書,經新疆考古工作者和“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同志們多年努力,已拼合成1800余件文書,並陸續分冊出版,其中有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文書;也有高昌王國時期的文書;數量最多的還是唐代的文書,基本上都是當時官私的文案和各種事務交往的記錄。所有這些,都為大力開展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
一、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特點及作用
我國甘肅省的敦煌和新疆的吐魯番,在魏晉時期,分別設置為敦煌郡和高昌郡,在唐代又分屬于沙州和西州,是當時中國通向西域的門戶。因而在它的地上地下,也留存有許多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物、遺書。加之西北地區氣候干燥,水分稀少,使得這些遺物、遺書,常保存逾千年而不腐,它們或長眠于眾多的墓葬中;或被當做神明供奉在寺廟里;或密封在石窟藏經洞內。長帝國主義的探險家們便將這些珍貴的遺物、遺書一批一批地劫往世界各地。
1895年,當俄國探險隊羅波洛夫斯基在吐魯番古寺廟遺址里,褻瀆神靈,劫走古寫本經卷後,俄、德、英、日等國的探險家們陸續來到盆地,掠走了大批漢文和民族文字的寫本文書。自1912年起,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英國的斯坦因又連續對吐魯番阿斯塔那的古墓群進行了盜掘,劫走大批十六國至唐代的墓葬紙質文書。在敦煌的莫高窟,自1900年道士王圓策發現藏經洞內四萬多卷古寫本文書後,立即引起帝國主義的垂涎,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等又相繼從這里劫走了三萬余卷。我國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就這樣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如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藏的“斯坦因文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伯希和文書”、俄羅斯聖彼得堡(前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的“敦煌特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吐魯番文書”、日本京都龍谷大學藏的“大谷文書”等,都是來自我國敦煌、吐魯番的古文書。
這些古文書雖然大部分是西晉到唐宋時的寫經,但也有一小部分屬于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始文獻,學術價值極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出土有紀年的最早社會文書是《西涼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現藏倫敦,編號為S.113),最晚的是寫有“宋咸平五年壬寅歲(1002年)五月十五日記”的寫經(現藏俄羅斯,編號為IX1696),就整個敦煌所出社會生活文書而言,還是以晚唐五代宋初文書居多。在吐魯番文書中,最早者有吐峪溝寺廟遺址所出寫有“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殘卷(現藏日本),最晚者有元代的文書,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善斌賣身契》三種。整個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國至高昌國和唐前期的文書為大宗。除此以外,在敦煌和吐魯番出的文書中,還有一些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和回鶻文的文書。由于這眾多的文書在本世紀初就被劫往國外,以致在舊中國的國內學術界欲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也無從大力進行,相反,在有些國家里,一些漢學家們結合中國的歷史,卻發表了不少對文書的研究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的直接關注下,一些流往國外的文書相繼被攝制回來,學術界對敦煌文書也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編目,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魯番阿斯塔那村和哈拉和卓古墓地,進行了十余次的發掘,出土了幾近萬片的漢文文書,經新疆考古工作者和“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同志們多年努力,已拼合成1800余件文書,並陸續分冊出版,其中有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文書;也有高昌王國時期的文書;數量最多的還是唐代的文書,基本上都是當時官私的文案和各種事務交往的記錄。所有這些,都為大力開展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