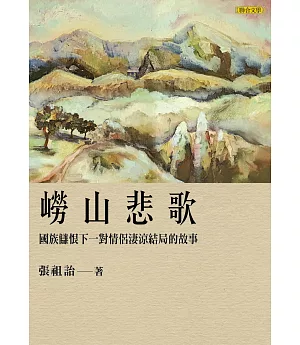推薦序
結於情者深
張祖詒先生這部小說以「嶗山」命名,我一下子便想起蒲松齡和他的《聊齋志異》。蒲是淄博人,距青島之嶗山二百餘公里,他曾於康熙十一年(1672)與高珩、唐夢賚、張紱等八友暢遊嶗山,有七古〈嶗山觀海市作歌〉傳世;其著名小說《聊齋志異》有〈嶗山道士〉、〈香玉〉以嶗山為場景,今太清宮逢仙橋之右下方立有蒲松齡石雕像。
〈嶗山道士〉(台灣的高中國文課本有收,作〈勞山道士〉),嘲諷慕道者不願吃苦,求術不求道,貪圖近功,注定失敗;留下「穿牆術」的故事,對於道教名山之於「道」,有正本清源的警世作用。而〈香玉〉為淒美的愛情故事,實乃「悲歌」,我直覺可以拿來和《嶗山悲歌》類比。
〈香玉〉以嶗山白牡丹和耐冬(山茶)的傳說為題材,寫黃生與白牡丹花妖香玉的婚戀故事,後白牡丹被人偷掘,香玉失蹤,書生終日傷痛,憑弔時遇山茶花所化的紅衣女絳雪,一同哭悼香玉,花神被感動,使香玉復生。黃生死後化成牡丹花下的赤芽怒生,終長成高大之樹,卻被不知愛惜之道士斫去。白牡丹和山茶花於是也相繼死去。
《嶗山悲歌》寫民初趙孫二官宦之家兒(趙厚仁)女(孫用和)的情愛受挫重創故事,大背景是從民國建立到八年抗戰(二戰)結束,場景從中國(北京、上海、青島、鄭州等)到美國(紐約、綺色佳、緬因州)、北歐的瑞典等地。
〈香玉〉是人妖戀,《嶗山悲歌》是正常男女情愛,都愛到入骨,都深嘗愛的滋味,也備嘗相思之苦。他們的愛情都受到摧折,〈香玉〉先是香玉原型白牡丹被偷掘,後是黃生精靈所化之樹被砍;《嶗山悲歌》先是用和在紐約為日籍街頭賣藝青年強暴,自戕未成,遁至瑞典為修女,最後竟得子宮頸癌,後是厚仁在嶗山與該日人相遇鬥毆,擊斃之,卻遭日軍嚴刑拷打幾至五臟俱裂。
二部作品的主場景都在嶗山,一是下清宮,一是嶗山小築;前者為道教,後者為天主教,其誠則一。兩情相悅中,前者有詩為媒,當然是舊體,後者為中文新詩與創作歌曲;前者有香玉義姊「絳雪」,後者有用和同父異母之小哥「用濟」,於雙方情愛皆為正向濟助之力量,相對於男女主角之熾烈,則顯理性沉著。
黃生死後魂寄卿側,而厚仁與用和「生不同衾,但死可同塋」。〈香玉〉篇末有「結於情者深」的評論,又說「人不能貞,亦其情之不篤耳」。我想,這應該就是二者共同的主題吧,《嶗山悲歌》另有「國族讎恨」,對於祖詒先生那一代人,當是刻骨銘心之記憶。
李瑞騰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序
這本書是作者一生中所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大概也是最後一本。距我第一次嘗試寫了一本《寶枝》出版(三民書局)已有六年。當時年已九十七歲,並未期望再作一次嘗試。
可是近數年中,又連續寫了二本散文集,都承聯合文學社先後贊助出版,其中《不亦快哉集》是於二○一九年八月問世,那時我的年齡,實已超過一百零一歲,乃蒙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女士積極鼓勵,力促本人如果能於二○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之後,再交一本作品給聯合文學出版,將可打破世界最年長作者的紀錄。
老邁如作者,豈敢妄作追求這項冠冕的奢望。因為作品的良窳,不在作者的年齡,而在作品的實質。但感謝張發行人和聯合文學的編輯同仁一再給我打氣,盼我再作一次嘗試。於是我不能不開始為本書作了規劃,勉力進行撰寫。其間因作者心臟病發,動了手術,三進三出醫院,以致遲延寫作,直到今天全稿完成。
中國小說的淵源,起始甚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莊子的〈外物篇〉中,首先就有「小說」二字的出現。其後經過歷代文化的演變,今日的小說已是現代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類。
姑且不論小說的孕育過程,但小說的胎源,早先大多出於稗官,也就是把街談巷議、道聽途說都可作為小說取材的來源。而且後來許多小說作家,慣用繪聲繪影或戲謔嘲諷的筆調敘事,以吸引讀者的興趣。因之故事的真實性和正確性自難與正史相比,但小說作品,足以反映社會風氣及人文素養,則猶過之而無不及。
筆者並非擅長創作小說的文學家,只能以百年所見所聞作為寫作背景。雖然書中的人和事,皆屬虛擬,但所採題材,必能符合時代現象的真實;人情義理的表達,也能力求無違邏輯的原則,這也是本書作者一貫寫作不尚浮誇而重樸實的基本態度。
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曾說:「真實世界遠比小說荒謬,因為小說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誠哉斯言,不僅小說作家應可奉為圭臬,舉世政治人物,亦應引為警惕,不亦然乎?
本書敘述的故事,發生於晚清末代、民國初立、以至中日戰爭的結束,時隔久遠。但願讀者閱後不致產生今昔扞格之感,不勝幸甚。又本書抱病完成,咎誤難免,敬請讀者朋友不吝指正。
張祖詒
二○二一、五、二一